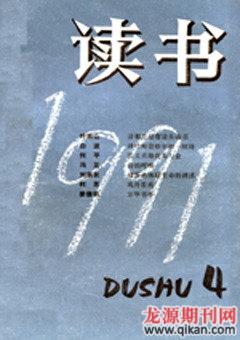新書錄
《詞學》第八輯(華東師大出版社,3.75元)令人佇望已久,看到《編輯后記》中言,多少了解一些編輯與出版的艱難,則它終于問世,已使人欣慰了。本集所收馬興榮《張炎的北行及其他》、謝桃坊《姜夔事跡考辨》等論文,仍是用考證、校勘、比較、歸納等傳統的方法,探索作家作品在其特定時期的真實情況或意義。而《詞的接受美學》(趙山林)、《<人間詞話>境界說給詞學批評的啟示》(鄧喬彬)則是嘗試運用西方現代美學理論,展開的對文學創作的評論。關于詞的音律問題,有馮統、何令龍兩家的研究文章。文獻部分,收錄了納蘭容若的手簡三十四通。啟功先生曾在《成容若手札卷跋》中寫道:“先生高才早世,遺墨流傳,稀如星鳳。每思披尋尺素,以寄仰止之思,而不可得。今見此卷,摩挲展讀,其欣幸真有譬喻所不能盡者。”仰止之思,人所同慨。只是書簡此番刊出,未能將《啟功叢稿》中對手札進行大略考訂的內容一并收入,未免稍覺遺憾。
見到新出的《基督教文化評論》第二輯(貴州人民出版社,3.10元),不由記起泰戈爾的一首小詩:“我能熱愛我的上帝,/因為上帝給我以否認上帝的自由。”正是由于上帝的這種寬容,方使人們在與上帝的一次又一次沖突之后,又一次一次取得和解吧。“生活的意義,亦即世界的意義,我們可以稱之為上帝。作為一位父的上帝之符號與此意義相聯。”“相信上帝即意味著看到,對世界的事實還不能漠然置之,相信上帝即意味著,生活有意義。”——對維特根斯坦的這些表述,當作何理解?漢斯·昆的《維特根斯坦與上帝問題》對此進行了闡發。“對于不可說的東西必須沉默。”但不可說的東西卻是“人在他的真實、他的存在的深層里所遭遇的那種真實”,對之怎能保持沉默呢?H.奧特在《對不可說的東西的言說》一文中所作的討論,很有深意。除六篇譯文外,集中尚收有韓彼得的《論先知》、唐逸的《安瑟倫的真理論》、何光滬的《上帝死了,只剩道德嗎?》等論文七篇。
《新價值觀——人能實現自我嗎?》(〔美〕丹尼爾·揚克洛維奇著,東方出版社,14.90元)向讀者展示了美國人追求自我實現的歷史背景,分析了它對美國的社會生活和美國文化產生的影響和自我實現不可逾越的障礙。本書對于近幾十年來發生在美國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經濟狀況、文化變遷,以及美國民眾家庭、婚姻、性生活等倫理道德上發生的變化多有涉及,因此讀者可以從書中比較全面地了解美國社會。同時,本書所列舉的事例和觀點,有許多在我國也為人們的親身感受、思考和討論過。而此書會對人們的思考以新的啟迪。
《天空中的現代神話》(東方出版社,3,50元)。是榮格晚年的一部著作,作者應用他所建立起來的心理學體系來分析飛碟現象。榮格認為,此起彼伏的飛碟現象是一種集休無意識心理投射。“令人感到非常絕妙的是,在榮格所分析的并沒有聽說過飛碟傳說的人的夢境中,竟然出現了與那些自稱目睹過飛碟的人所描述的形象相同的飛碟形象……”這些聽起來似乎荒謬,榮格也似乎意識到人們的這一分析的必然反應,表示“我必須冒險,哪怕這意味著將我求實可信以及科學判斷能力等等來之不易的聲譽毀于一旦。”
不管是研究近代史,還是研究中國共產黨史或者國民黨史都不能“不研究蔣介石,甚至研究近代政治經濟等等都離不開蔣介石這個人物,一七二七年的“四·一二”事件后,中國大地上發生的每一政治、經濟事件都也蔣介石有關。在中國老百姓的心目中,蔣介石就是罪惡的代名詞。給這樣的一個人物寫傳記,我想無非也是蔣介石=罪惡。這是我看完《蔣介石傳》(楊樹標著,團結出版社,9.00元(精))之前所想的。《蔣介石傳》記錄了蔣介石撤離大陸前的前半生。并不是如我想象的,作者在罪惡和蔣介石中間劃一等號,作者認為,蔣介石在大陸上的幾十年有一個歷史發展的階段性過程。蔣介石在大陸上的活動就是循著這樣一個過程走過來的。作者對蔣介石的描寫也是這樣一步步展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