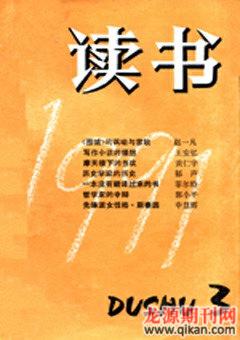欠賬
吳祖光
新鳳霞的又一本散文集將要出版,收記事文一百一十一篇,約五十余萬字。估計一下,包括幾種不同的版本及外文譯本在內,這本書是她的第十三本文集了。她著手大量寫作,從一九七七年開始,至今約為十三個年頭,幾乎每天都在不斷地寫,于是就寫了這么多。
出身天津南市貧民窟,到二十多歲在舞臺上早已成名卻還是文盲。進入新中國,煩重的演出之余,擠時間上了短期的業余掃盲班。盡管在舞臺上紅極一時,然而偏偏橫遭不幸,最終迫害成病,落得半身殘疾。這就是新鳳霞的命運。
然而奇跡也由此而生。從一九五七年春天她在掃盲班的兩篇作文在《人民日報》八版副刊上發表之后,直到一九七五年病倒之前再也沒有寫過什么。但是在病成殘疾、被迫離開舞臺、失去用武之地后,卻以筆作為她宣泄情懷的武器——幸而致殘的是左手——不停地寫了起來。寫得這么多,這么快,也可以說又是這么樣的引人注目。依我看來,一個自幼與文字絕緣、民間藝人出身的戲曲演員,有這樣表現的,實在是前所未見。不僅空前,而且絕后;因為今后將不會再有這種類型的民間藝人了。
她是我的妻子,我曾鼓勵過她識字、讀書,但是在短短的十幾年取得這樣的成果實在是我始料不及的,深深感到這真是個“異數”,她大可列入異行傳。
為她叫屈的是,至今還有人懷疑她的作品是由我代筆的,盡管仔細審閱便知那絕對不是我的文章。她的風格我代替不了,寫不出來。雖然有過不少同行朋友為她、也為我解釋;可就是不能消除這樣的懷疑,那也就沒辦法了。
正是因此我就需要在這里說說她何以能寫出自己的風格,而且又寫得這么多的原因。第一,她沒有上過正規的學校,所以很少受到新文學以及舊文學的影響,作文章只能用自己熟悉的生活語言;一般人稱此種語言為大白話,因之便較少新的名詞、語匯和術語,這反而是一般作家所難以做到的。這樣也從而形成了她獨特的風格。第二,她有驚人的記憶力。譬如,她記電話號碼的能力簡直可以和電腦比美。很多人的電話號碼只要她撥過一次便牢牢記住,可謂過腦不忘。在這方面,我的記憶力太差勁了,連弟弟、妹妹、甚至兒子的電話都記不住,然而很多電話,那怕十分疏遠,只通過一兩次的很久遠的電話,她常常是應答如流而且毫厘不爽。因為,錯了一個號也是叫不通的。這一樁,家里人已經習以為常,記不起的電話碼一問她便知道了,而外人碰到便往往大為吃驚。這種記憶力是她能大量寫作的主要原因。她的作品無論是記人、記事、談藝、論藝都是她大半生記憶的結晶。譬如在那天昏地黑的十年文革時代,其中有不足一年的時間在她工作的中國評劇院,由于鄰近全國政協所在地,所以極其偶然地在兩個單位臨時組織起一個老弱病人的勞改隊,其中唯一的女性就是新鳳霞,其它成員則大都是所謂“戰犯”的老先生們,其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是遜清的傀儡皇帝溥儀。事情已經過去約二十年了,但鳳霞寫的關于與溥儀在這段短短的幾個月里共同勞動中發生的一些佚聞趣事竟達六十余篇,已經單獨編輯成書,行將出版。這一切都是她記憶力過人的表現,是她的寫作大量產生的主要原因。當然,更主要的因素是她的勤奮,幾乎每天在凌晨六時左右她便起床,洗漱之后,立即在晨窗下寫作起來。寫得這么多即是這種持之以恒的寫作習慣所致,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她的記憶的寶庫似乎永不衰竭。
相形之下,我這個健康人的記憶力便與她相差太遠了,過去的事大都忘卻,尤其是近事健忘更甚。新朋友在一起過了一段共同生活常常有之,但事隔不過幾個月再見時,卻只覺面熟,名字就想不起了。甚至老朋友亦經常叫不出名字來,別人跑過來熱烈握手,歡然道故,我卻常是張口結舌,在苦苦思索著人家的尊姓大名,真乃苦不堪言。近年以來,有幾個雜志,幾個出版社向我約稿,要我寫自己的回憶錄;確實我也覺得該寫,然而怎么寫呢?往事一片模糊,從何寫起?
鳳霞一生的道路,崎嶇坎坷,一言難盡;小時貧苦,為生活掙扎,為學藝奮斗,這都是正常的。而成名之后,趕上新時代,天日重新,本應前途似錦,卻是大難臨頭,九死一生,而帶來偌大不幸主要竟是由于作丈夫的我的原因。假如她當時聽從“領導”的指示和我“劃清界限”,甩掉我這個“包袱”,她仍將十分幸福,順水行舟,如座春風。但她卻偏偏不這樣做,硬自吞下苦果,承受災難,弄到被趕下舞臺,重病致殘而堅持到底終生不悔。
半生匆匆過去了。昔日舞臺上的輝煌已化為輕煙消逝,而鳳霞的回憶錄卻似永無止境地仍在一篇篇的寫出來。她半身不遂,行動很不方便,我們自從把五十年代自費購置的四合院平房捐給國家之后,一直住在城東的四層樓上,偶爾應邀出門作客或看戲開會之時,常是由兒子或是年輕朋友來背她上樓下樓;當然天暖時她自己扶著欄桿或是拄著手杖亦能一步一挨地艱苦上下,我看著這種情景總是感覺無限歉疚。總想到她年輕時行走如風,自然不需人背;如今需要人背時我這堂堂男子漢卻背不動她了。但我卻是不甘心的,總想試一背之,卻又總被她厲聲喝退,看來這亦將是終身遺憾了。
晨起聽北京新聞廣播,介紹曾經默默無聲地編過一千幾百種書的資深老編輯常君實先生的事跡,譽之為《中國的脊梁》。我非常高興鳳霞這本新書的編輯又是常君實先生,因為她的頭兩本書亦都是君實先生編輯的。這次又不辭辛苦地來編鳳霞這本大書,可以想像,編她的書十分吃力,起碼要改多少錯別字啊!這一回又是君實兄要我寫篇文,給我一個機會談談鳳霞的情況,也說說自己的歉悵。歉悵亦就是“欠帳”吧?鳳霞受的苦是我害她的——誰害的我我可說不上來——而患難余生我竟連一背之勞亦無能盡力,真是好不慚愧。
鳳霞的勤奮和記憶力都還在興旺之際,看來她的文章還要無盡無休地寫下去的。
一九九○年十二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