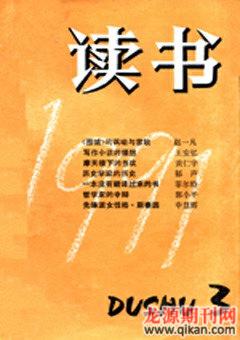摩天樓下的芻議
黃仁宇
衛方在波士頓遇見了他的朋友。晚餐之后聚談到十點半,他辭別了出來。朋友原來邀他在旅館里住夜,他辭謝了。在夏天像奧頓這樣的旅舍,單人房間起碼就是一百美金一夜。而且衛方每一旅行就失眠。與其輾轉反側地糾纏著枕頭和床單,還不如星夜回家,說不定在巴士上還可以若斷若續地坐著打盹。
在車站里,他發現洗手間在地下室。但樓梯口有一位穿制服的服務員把守,來人非持有車票,不得下梯。
上下樓梯之后,衛方還想到當晚他和朋友在奧頓的餐室里的晚餐。他叫的是小鱈魚,朋友要的是海味特品(seafoodspecial)。他們的侍者名叫沾米。
“一切如何?”沾米每幾分鐘就走來問。
朋友告訴沾米,海味煎烹得過度。“抱歉,”沾米說著。衛方在旁邊沒有明講的則是鱈魚昧同嚼蠟。付賬時,朋友在帳單上簽了字,另給小帳三元。沾米取過去,初時并沒說什么,過了三、四分鐘他又回來了,手中仍拿著內有賬單與小賬的膠型碟子。“先生,”他告訴朋友,“你的簽字沒有注明房間號碼。”這位朋友照著侍者的指示,將房間號碼加寫簽名之下。這時候,三塊錢小帳仍在碟里,沾米就趁著這機會做文章:“先生”,他說“難道這里的服務這么壞?”
“什么?”東道主已經把筆放在口袋里,很驚訝地瞧著沾米。
對方仍然站在桌子旁邊。很理直氣壯地陳述:“你給的小帳不到十分之一,所以我要知道服務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當面被抗議小帳給得不夠,這是第一次的經驗。可是,這是沾米的世界,小賬已是份內應有而不是額外施恩。他又不能原恕這兩位資深公民之年老無知,重復地說:“這小賬不及十分之一……”
衛方不能猜想四十年前,當他的東道主胸前掛著飛行員和降落傘的徽章時,對這種質問的反應,現在到底是經過圣命的牧師(ordainedminister),此一時彼一時也,態度自然不同,他從皮包里找出一張五元鈔票放在碟子里,才把三張一元鈔票收回。沾米算是對他的抗議得到圓滿的解決,低聲哼著道謝退場。
波士頓到紐約的巴士擠滿了旅客,有些人在車門口站隊達一兩小時,就是想要占得座位。衛方上車時已經找不到座位,后面還有三十個人,照例公司要加派一輛車,但是這時候司機用擴音器叫乘客將行囊放在座下,小孩放在大人的懷抱中,“如果一個人占著兩個座位,就要加買一張票。”這樣的呼喚之后,衛方得坐在一位太太的旁邊,她被迫將一個約三四歲,正在酣睡的孩子貼著自己抱起。
最后還有一位太太讓一個五六歲的孩子占著一個座位。司機走上前要她買票。
“照規定他不需要票。”她辯著。
“他不需要票,那也就不能占座位。”司機緊迫著,還站在旁邊不去,這位太太意態快快地也把小孩貼身抱著。司機算是替走廊上最后一個旅客找到了座位,于是再度清檢人數,又向傳音器里說了些話,巴士才離站,至此已近半夜時分。巴士脫離了波士頓市區,進入跨省公路。
不知什么時候,他真的打了一陣盹,醒來只聽著司機大叫。“哈特福!”此時只有一位乘客下車,座席也給一位新來的乘客接替。衛方又在
巴士在清晨四時半到紐約汽車總站(Port Authority Termi-nal)。下車之后,他才知道一切不如想像。借大的紐約總站,只有灰狗經營的地下室一部分開放,有警衛守門,只讓有票的人進來。候車室已經坐滿了人,還有人在地上躺著睡覺,也有人靠在樓梯旁邊看報紙。
提著行李信步走到四十二街,他已經問明白了:第一班去紐普茲的車在清晨七點出發,車站在六點半才開門售票。離現在至少還有一個半鐘頭。這時候街上雖有車輛行人來往,但所有的店鋪全都關著,即使咖啡店也是門扉深鎖。他抬頭望著很多的摩天樓,又興起今昔之感。衛方第一次到紐約時,全部的建筑都是鋼骨水泥,現在卻有很多的用有色玻璃做建筑的外表了。
沿著第九大道走去,他不敢太靠著建筑物走。因為有些無家可歸(homeless)的人正傍著墻壁睡覺;有燈光的一片地方,則有不少街頭的叫化子。
他不能過度的發牢騷,訴不平。紐約是世界上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各種時裝美術藝術表演展覽之中心,有天才的人起先或者有些困難,只要在這幾平方英里的面積內打開門徑,無一不獲得生活之滿足,物質上的報酬也很實際,十萬百萬隨手而來,也不分人種國籍的畛域。他也不能過度的代街頭搭地鋪討飯吃的人伸冤。美國現在可算“全部就業”(full employment)。到處都是事求人(Help Wanted)的廣告。不然像沾米那樣的侍者,要是記掛著飯碗之安全,又何敢在資深公民的顧客面前講小帳不能少過十分之一的大道理?至于報紙雜志上有時還提到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的失業人數,則有專家分析其咎在這些人自己身上,其中大多數則是無可雇用(unemployable)。再說得不好一點,在這個時間、在這樣的一個地方仍舊躑躅于街頭的人,也就是沒有出息。在重視成功的社會里,他們只能被稱為失敗(failure)。
衛方也索性承認自己是一個失敗,不然何以天尚未亮,仍躑躅于紐約的第九大道與四十二街之間?又何以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尚在侃侃而談,閑坐著吃龍蝦,今日則自己扛著行李袋付不慷慨之小帳?
雖說閑常他有這樣的想頭,可是又不愿如此衷心的糟塌他自己。
他也不愿爭辯在經濟景氣的年份仍然找不到事做,其咎在社會還是在各人本身。他認為兩種情形都能存在,彼此都有理由。要是加入此中爭論,他就會被卷入現實政治的漩渦中去了。他學的是歷史,這時候他希望以一個學者的身份,對現實政治保持距離,可是歷史承先啟后,又不能和今日不關痛癢。同時他看到很多人沒有看到的一個大問題:刻下美國和很多亞洲國家打交道,政治思想的沖突已屬次要。這些國家以廉價勞工制成品侵入西方市場,使美國對外貿易產生收支上絕大的不平衡,也仍可以平心靜氣地根據數目字談判。唯獨兩方之不同,可能因宗教思想之不同而產生更大的差異,至為可慮。
比如說:日本和美國同時提倡資本主義,日本人卻將神道的宗旨摻進了他們的生意經里面去了。又如新加坡也和美國一樣的在實行資本主義,可是這個城市國家針對內外情勢嚴格地主張由政客作主,采取儒家“自謙”和“一國興仁”的辦法,就和美國的新聞界造成一個勢不兩立的情勢。
衛方之所謂宗教,有一種廣大的含義,包括出世入世的思想,有形與無形的成份,大凡一提及人生之“最高的”目的和“最后的”宗旨,又牽涉很多人眾,即不妨以宗教視之。這樣看來,神道也并不神秘,甚至可以用“清明在躬”的四個字籠罩之。即是穿鮮明潔凈的衣服,反映著山川自然之靈氣,甚至保持著原始社會的恩義觀念,只要在這種美術化原始型的條件之下,做人做事表現著既簡單又真切有力的風格,即可以算得符合神道之旨趣。所以美國人做生意以賺錢為目的。日本人之做生意除了賺錢之外,還要各人在其行動之中,反映著他們國家的原始性格,就不期然而然地在世俗之成功的局面里,產生了一種精神上的力量和集體的效果。有些日本人還意不在此,索性借此鼓吹日本人種優秀,甚至有修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論之趨勢。
新加坡的華裔公民占百分之七十。如果他們都以短視界的立場,堅持狹義的本身利益,也真可以暫時頤指氣使,把華人的地位捧上云霄。只是處在一個億萬的印度人馬來人伊斯蘭教徒之人海中,短視界的作法,很難有成果,而且貽害子孫。好在儒家思想“柔遠人,來百士”,向來一視同仁,也是中國人的歷史性格。現在新加坡決定用這種態度當作立國精神,甚至將南洋大學原來專用以保持傳統的中國文化之教育場所一并封閉,要他們和新加坡大學合并,如果將一個行政上的大前提,處之如憲法精義,也不容爭辯,看來就有宗教上的硬性了。
很多美國人沒有想起的他們所表彰的“自由”也是一種歷史產物,也有北美合眾國的特殊性格。英文里面有兩個字可以視作自由,一為freedom,一為liberty,前者帶有濃厚的宗教意義。十七世紀的清教徒,在其旗幟之下,深信他們個人接受了神之啟示(calling),遠渡重洋,來北美洲披荊斬棘,把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發揮到極端。后者追溯其根源于歐洲中世紀,起先封建領主將城市特權(municipal franchise)授與市民(burghers),等到經濟發展成熟才普及于全民。美國得天獨厚,也可以說是將一個已經試驗有效的組織與系統,施行于一個空曠的地區。可是也還要經過無數的奮斗,最顯然的則是四年的內戰,當時雙方都認為為自由而戰,北方固然認為解放奴隸是一種解放運動,而南方也認為抵抗強迫就范的威脅是他們作人的第一要義。所以至今內戰的歷史仍為美國人百讀不厭的題材。至于美國人在海外為自由而犧牲,已經用不著說了,旅游者只要看到各處的美國人公墓,就可以想的起。
衛方已經走過十一大道,他才折回東行,這時天已微明。他知道本身自己決定為美國公民,不可能與自由的宗旨作對。可是他覺得不顧其他國家的歷史與社會背景的推行自由為不合實際。自由是一個極為廣泛而抽象的名詞,在古今中外一向就被人濫用。今日亞洲諸國除舊布新,只能根據自由平等的大原則之下,讓他們各自發展他們的國家性格,不能由外界干涉,使他們的群眾運動,變成一個四不像的改革(unstructured reform)。次之則以美國的尺度衡量亞洲,往往做得文不對題。今日美國公民享有之自由乃是社會分工合作進展到某種程度,法律賦予各人權利與義務之一種保障,包括各種特殊情形,并且仍在流動狀態之中,也仍在不斷地修正。要是其他國家的經濟條件尚未發展到這種程度,就要實行同樣的自由,首先就費力而不討好,萬一僥
等到車站將各種鏈條撤除,各處門窗店鋪大開的時候,他到阿莊力克公司的柜臺上買了票,順便又去隔壁不遠一家點心店,買了一塊黑草莓蛋糕,他的早餐。這店里卻無去咖啡因之咖啡,于是他又從自動樓梯上了一層樓,那里有一處小食店,在那里購得他要的飲料。掌柜的女店員是亞洲人,看樣子也是華裔。
“六毛五分錢”,她說。突然,她看到衛方手里的紙袋,內盛黑草莓蛋糕,乃樓底下店內之物。“喂”,她指著這袋向衛方警告,“你不能在我們店里吃這些食物!”
原來這店里也有它自己的點心,也有空桌子讓顧客憑站著吃早點。當然它有權力拒絕來客用他們的家具,去幫助樓底下的競爭者賺錢。衛方很誠懇地解釋,咖啡與點心都準備在巴士上用。
他又買了一份《紐約時報》,才匆忙地奔去樓下的候車室。他左手抓著兩個紙袋并報紙,右手拇指穩定著掛在肩上的行李袋,夾在食指與中指之間的乃是阿莊力克的汽車票。如此他可以及時站入乘客的行列中去,用不著掏腰包。
他已經站在波士頓和紐普茲的乘客陣容里了,可是他還是想著東方與西方,美國和亞洲。
這中間之不同已經展開成為一種宗教問題。清教徒在麻省登陸已經快四百年,今日很多的美國人,已不常到教堂去做禮拜了,可是“我的良心只有神知”的觀念卻已經透過三百年來無數的歷史事跡轉化而成一種社會力量,把持這種觀念的人,當然要盡力保衛各人的獨立人格,因之將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發展到最高峰,這也是使衛方在年輕時代醉心于美國之一大主因,可是這種想頭也容易使各個人所想象的宇宙限于自身的人身經驗。在今日一種帶收縮性的世界里,這樣的宇宙觀是否合適,甚成疑問。
當司機開始收票,乘客每六、七秒鐘向前走一步時,他更猛省地記起,他想發表的意見不易被人接受。“什么”,他可以預算到對方反應,“你打算傳播東方及集體性的哲學(philosophy ofcollectivism)?”
衛方無意傳播東方之集體性的哲學,他只希望這樣一個世界能夠依然存在。這也沒有超人的見解,他想今日之資深公民必有很多與他有同樣的想頭。他為人父已二十多年,曾看到不少的美國父母帶著他們的子女,去參加小狐童子軍(Cub Scouts)、芭蕾舞、幼年棒球隊、軟式棒球隊。縱使他們都是個人主義者,又縱是他們都不明言,總也不能離開一個心有同感。
現代的中國人,很少會以贖身超度(redemption)的觀念,或因個人與神之特殊關系之下祈求永生。可是據他所知,一種父以子繼兄以弟繼的傳統卻仍然壯盛。換句話說,他們都在血緣關系中祈求永生。如此則必須現有的一個世界依然存在,于是也必須延長擴大個人的宇宙觀。這種想法是否可以與西方的個人自由主義并存?他希望如此。
他衷心地希望如此。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兜了一個大圈子,走了五百多英里路,看到了數十年沒見面的老朋友,當然內中仍有不少個人的想法,只是始終沒有忘懷這樣的一個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