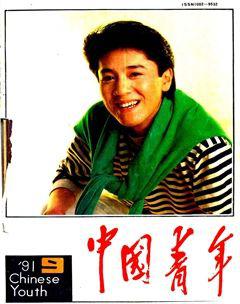需要自覺
周良洛
如果后人要寫20世紀80年代、直至90年代的青年學生運動史,大學生的社會實踐活動恐怕當屬濃重之筆,甚至可稱為主流。我想這絕非夸大其辭,10年中我親身目睹、參與了這項“運動”經久不衰的歷程。
耐人尋味的是,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的發生、發展伴隨著三個歷史現象,一是改革開放的全面推開并帶來我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深刻變化;二是大學校園里基本上是清一色的“三門學生”;三是10年中發生過幾次大的學潮,而每次學潮后又都會出現一次社會實踐熱和學理論熱。這是否向我們說明,不論學生的行為、行為效果怎樣,在那些表象背后,總深藏著一個思考——社會、人生以及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該怎樣才更接近真理。也許,這種思考正是學生們走向社會、走向實踐真正的內在動力。
當大學生的社會實踐經過幾個循環以后,越來越多的人發現了上一代人已經證明了的原理:只有把理論和實踐,外部“灌輸”和自身體驗結合起來,才能使書本知識得以消化和吸收,轉化為學生的自覺。參加到人民的實踐中去,這是青年知識分子成長的必由之路。52年前,毛澤東講得更徹底,“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這是一條并未過時的真理。
當我們帶著這樣的認識反思幾年來社會實踐活動的時候,是否會發現,我們還沒有完全地將這個內在動力運用于社會實踐活動中,社會實踐活動還帶有很大的自發性。淺嘗輒止,挖掘不深,滿足于轟轟烈烈,滿足于學生歸來后的即興觀感之談。我們很深地體會到,僅僅把學生放進社會,很難自然而然地形成真理性認識,活動需要我們引導,需要我們增加更為豐富的思想內涵。我覺得,我們的社會實踐活動已經到了一個階段的關節點,也就是從自發走向自覺的關節點,從感情體驗到理性認識的關節點,這是否向我們展示了深化社會實踐活動的一個新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