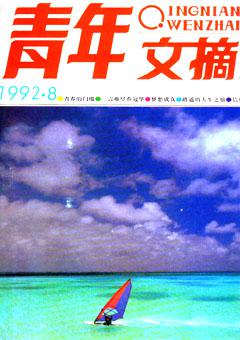峭壁下的奇跡
(美)李沙·何斯·約翰遜 葉碧霞
1989年5月27日,星期六。美國科羅拉多州西南部的古老礦城特魯萊德城外洛基山上空是一片蔚藍的晴天,西部各地的巖壁攀登者都被吸引到這兒,來到13,000英尺的山峰上磨礪他們的登山技能。
34歲的凱蒂婭也來了,她曾開辦過一所登山學校,現在是位急救護士。與她同來的是里克·哈奇。里克34歲,是位推銷員,也是登山愛好者。
奧斐峭壁的難以攀登是出了名的。它的正面是花崗巖,向前突出有幾百英尺高,其上只有一些可以支撐得住一個攀登者體重的手坑。
到下午二時半,凱蒂婭已攀登完畢。里克在爬著最后一段距離,她則把他的繩子系牢在地面上。但她并沒有覺察到一陣狂風正以每秒50米的速度掃過崖頂。
“石頭!”里克突然發出急促的警告,她一下子警覺起來。里克已經平伏著身體緊貼在花崗巖上,以避過那驟然而降的石崩。垃圾筒大小的巨礫正在峭壁上轟然坍下,在凱蒂婭身前身后紛紛炸裂。
凱蒂婭跳起來疾速跑到左邊。說時遲那時快,隨著劈啪一聲巨響,一塊巨石從奧斐山崖的正面崩彈開來,猛砸在凱蒂婭的左腿后部。那沖擊的力量一下子把她拋到離地五英尺的空中,像車輪般翻滾著,鮮血噴濺而出,在她身體周圍飛散。
凱蒂婭墜落在一塊鋸齒形的山嘴上,感到左腿像火燒般疼痛。她向身下望去,一下子瞥見兩根斷了的骨頭從膝蓋下伸出來,她的半條腿沒有了。
里克迅速爬過來,這時凱蒂婭四處張望尋找她的斷腿。她發現斷腿就近在她身體左側,與膝蓋之間仍然有一塊一英寸寬的皮條和肌肉條相連。
凱蒂婭猛然間意識到:我可能因此而死掉。作為護士,她知道一旦腿動脈開了口,流血致死那是只消數分鐘的事。她驅散這些念頭,集中精神考慮如何活下去的問題。
凱蒂婭強忍著劇痛,小心翼翼地將那截幾乎與軀體完全分離的下肢捧起來,清理著。它摸上去很古怪——軟軟的,暖暖的,感覺不到那是屬于自己身上的東西。
里克此刻正在她身旁,眼睛里充滿了恐懼。
“我們需要用止血帶把腿綁住。”她叫喊著。
里克爬過碎石堆,取來一些他曾用來爬山用的尼龍帶子。
“等一等,”凱蒂婭說,檢查著傷口。“這僅僅是靜脈沁出的血。”希望從她心中涌起:我的動脈一定是被扯出來挾在大腿里面掐斷了,她想,我得要讓膝蓋保持有血流通。
體重160磅的里克長得瘦長結實,體質強壯,他把凱蒂婭抱了起來。
“別擔心,”他說,“我不會離開你,我會自始至終幫你渡過這個難關。”
里克一邊掙扎著走下山間小徑,一邊強制著自己不去注意凱蒂婭那可怕的斷腿。那斷腿緊抓在凱蒂婭手中,離他的臉只有八英寸遠。
凱蒂婭看見他臉上掠過害怕的神色,就說:“里克,如果我休克或昏倒了,你需要做這些事……”她向他作了詳細的說明,希望能分散他心中那種認為她將死在他懷里的念頭。
他們走到一個四分之一英里長,布滿石礫的陡峭山坡,即使沒有什么累贅,這樣的地形也是很難越過的。里克把約15英尺左右該走的每一步都預先在腦海中排練一次。
他終于精疲力盡了。汗水濕透了他的襯衣,與凱蒂婭的血混合在一起。他的心跳加速,又因為地勢的高度而氣喘吁吁。這是他體力耗費最大、最為艱難的一次經歷。然而只要他一想到懷中這位女性的堅忍剛毅,他就能夠鼓起更大的勇氣驅策自己向前邁進。
到三時半左右,里克走出了山間小徑。另一位目擊那場石崩的登山者正在那兒,身邊有輛卡車。里克把凱蒂婭舉上了車子后部。卡車飛速駛過公路,每一下顛簸都使凱蒂婭遭受像電擊般傳遍全身的痛苦。里克竭力寬慰她,同時讓她的腿保持成一直線,好讓那還連在一起的肌肉不被撕斷。
20分鐘后,在特魯萊德醫藥中心,值班護士幫著里克把凱蒂婭放置在急救臺上。
一些剛剛才接受培訓的護士,從未見過這么嚴重的傷勢。當凱蒂婭看到他們嚇得臉色灰白,就擔當起指揮員。“我是急救護士。現在你們即將要著手給我進行靜脈注射。”她伸出雙手,緊握拳頭以便使血管暴露。用“16號針頭,在肘彎前注射。注入摻有乳酸鹽的林格溶液,越快越好。每隔五分鐘你們得要給我量一次血壓。”
凱蒂婭需要先進的醫藥治療,醫生決定把她送到格蘭莊遜的圣瑪麗醫院——凱蒂婭工作過的一間醫院。此時醫生所能做的工作,就只是在她的大腿上加個套箍,因為一旦那里的動脈松弛下來敞開了斷口,凱蒂婭幾分鐘后就會送命。
這一個小時之內凱蒂婭的情況穩定。隨著最初的震擾漸漸消失,神經末梢變得較為敏感、疼痛更為加劇了。“喊叫一下吧,沒關系的,凱蒂婭。”周圍的人鼓勵她說。但是她仍是不哼一聲。
大約下午五時,她被小心地安置上了空中救生直升飛機。在飛往圣瑪麗途中,凱蒂婭一直在考慮下一步該采取的措施。看到里克和自己在一起,她很高興。
飛機到達目的地,急救室工作人員作好了外科手術準備。當戴維·費希爾大夫趕來時,凱蒂婭看著他的眼睛問道:“你能保全我的腿嗎?”
“不,”他說。
“那么截肢位置取到膝蓋以下。”
費希爾大夫沒有問答,但是在手術中他意外地發現那截下肢是溫暖的,腿的兩部份都有可修復的動脈。“這一位年輕女士很幸遠,”他對同事們說,“她還有機會再用自己的腿走路。”
幾個小時以后,里克又坐在凱蒂婭手術后住的特別病房中。又過了幾小時,當凱蒂婭蘇醒過來時,她一時間竟想不起身在何處,所為何事。當疼痛襲來時,那可怕的回憶復活了。一陣不祥的預感使她打了個寒噤,低頭向腳下望去,腳趾頭是整整十個!“看哪!”她歡快地說,知道自己又有了一個拼搏的機會。
凱蒂婭每天得有兩次泡在旋渦浴中清洗傷口。接下來的幾個月期間,先是在圣瑪麗,后來是在丹佛,經受了半打手術,修復那失掉的肌肉和皮膚。醫生還從她的右腿取了一段血管來造她左腿的動脈。這期間,里克每天晝夜24個小時都和她在一起。
凱蒂婭裝上了一個類似腿支架那樣的金屬框架。每天她都得強行把支架延伸一毫米,讓柔軟的肌肉組織、神經、動脈、靜脈和皮膚在骨頭生長的同時得到伸展拉緊。
所有這一切努力都不能說必定保證生效,然而她的腿和腳已經有了感覺,也就是說,有了希望。
在整個階段中,里克,一個她幾乎不了解的人,一直伴隨在她的身旁。她留醫的頭四個星期內,他就在她床邊的一張椅子上過夜。在她床頭幾的花瓶上,總會有一株白玫瑰。這一切令她想起他在山間小徑上說過的話:“我會自始至終幫你渡過這個難關。”
(王萍摘自《體育博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