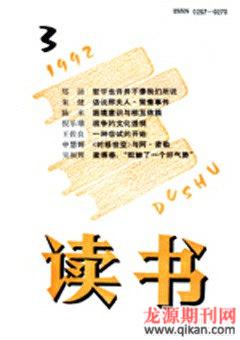社會與國家的文化詮釋
葛佳淵 羅厚立
以往治史,多以人物或事件為軸心來把握歷史演進的經絡,而對人物事件后的社會文化自身嬗變,關注不夠。今日海外漢學中的社會史取向,則恰好反之,是力圖將對歷史過程的探究,根植于對地方文化社會變遷的了解之上,以期對來龍去脈(context)有一更深刻的把握。這一取向篳路藍樓者,為倫敦大學傅立曼(MauriceFreedman)的宗族說(lineageorganizationtheory),斯坦福大學施堅雅(WilliamSkinner)的市集體系說(marketSys-temstheory),以及蕭公權等的縉紳社會(gentry society)研究。而近年對這一取向做出新的拓展的,是近日付梓的《文化、權力、與國家:一九○○——一九四二年的華北鄉村》一書(以下簡作《文化》)。
《文化》一書為杜甫生(PraenjitDuara)所作。杜氏為印度人,留學哈佛,師從清代社會史名家庫恩(PhilipKuhn),專事清末民初史研究。該書瘁其十年之心血而成。杜氏雄心勃勃,欲于書中構筑一龐大體系,兼容并蓄傅、施、蕭三家,以廓清此時期華北鄉村社會文化變遷的脈絡。杜氏并引入歐洲史研究中的“國家”概念,以考釋中國近代國家與社會的互動消長,為檢討近代中國歷史提供了一個新的參照空間,頗值得注意。
《文化》一書旨在闡釋近代中國的一大悖謬性歷史現象,即以清末“新政”為發端的一系列“富國強兵”之舉,其結果均適得其反。盡管這些以國家對社會滲透為主要手段的措施與近代歐日的“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過程極其類似,效果卻大相徑庭,貌似而神離。作者認為,原因在于華北政權向鄉村社會的擴張滲透,實質上摧毀了地方社會的既有秩序,而同時又無法找出一套相應的整合手段,結果就使華北農村陷入一種所謂“國家滯變”(stateinvolution)的窘境之中,導致這些政權賴以生存的農村社會組織解體。雖然國家政權從農村攫取財源的能力與日俱增,但控制農村社會穩定的能力則大大減弱,終致一發不可收拾。因此權力更迭頻仍,直至國民黨政府崩潰。
證明這一命題的關鍵,在確立華北鄉村在“新政”之前已有一套可自身完善的既有秩序。杜氏于此處著墨甚多,他將這個既有秩序稱為“權力之文化綜”(culturalnexusofpower),意即一組反映在價值觀念、宗教信仰、地方組織上的行為規范。由于各種組織在這種格局之下相互作用,這種規范及組織格局便為地方政治的參與者們提供了實施權力的空間,同時也界定了行動的范圍。在這一參照空間下,地方政治的參與者們——無論是祠廟、宗族、水利管理組織,抑或是國家政權的地方代理者——都共同分享著這些規范和價值觀念。正是這一參照空間,即所謂的“權力文化綜”,賦予了參與者們,包括國家政權在內,在地方政治上的合法性。
西方漢學對傳統中國鄉村社會結構的研究,受施堅雅“市集體系說”影響頗深。這一學說強調鄉村集市在鄉民社會生活中的功能。施氏根據他早年在川西平原的考察,以為界定傳統鄉村社會的基本單位,非市集莫屬。他以空間觀念為出發點,將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勾勒為六角狀的層級秩序,并以此衍申他對中國社會結構的理論。雖然“集市”的概念曾為研究華北農村的黃宗智所批評,但黃氏的自然村概念依然是以空間為出發點的。
杜氏對“市集體系說”提出新的挑戰。他認為界定這一既有秩序的基本單位應是一文化現象而非空間現象。鄉民的社會互動,農村的社會組織、宗教活動乃至婚喪嫁娶,其地理范圍雖相互重疊,但絕非完全一致。如華北地區嫁娶的地理范圍,常常超越集市界限;而水利組織輒橫跨數鄉。因此,杜氏認為:只有鄉民共同分享的價值觀念,共同參與的社會組織,以及共同遵循的行為規范,才能作為界定地方政治社會結構的基本單位。這樣一來,其“權力之文化綜”就顯得比施氏的“市集體系”來得貼切了。
杜氏在論述“權力之文化綜”的概念時,對宗教和宗族組織有值得注意的新見。一般研究宗族的傳統,以傅立曼的社會人類學為發端。傅氏取東南沿海地區宗族資料為證,強調宗族組織在地方村社政治中的作用。而東南沿海的宗族組織,多為大族,以其族產、宗祠及血緣網絡為支點,非但決定地方社會升遷的渠道,提供社會保障的功能,且成為地方政治的認同對象,雄踞村社政治舞臺。而傳統的看法認為:與南方這種支配性宗族(dominantlineage)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宗族在華北的微弱功能,有人甚至認為宗族組織在華北鄉村中的角色微不足道。杜氏根據對南滿鐵路在直隸、山東的調查資料的分析,指出宗族在華北鄉村中依然舉足輕重。宗族、宗教組織與水利管理組織并駕齊驅,成為地方政治最為活躍和最為直接的體現。他說:“在那些宗族同村社管理相互吻合的村子里,村社之政治和權力完全操于以各宗族之代表組成的理事會之手,而宗祠則為地方精英們表現其領袖欲望和履行社會職責提供了一方天地。”
《文化》一書中最具洞見之處,在于討論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部分。此前凡論及國家與社會的消長,論者均庇蔭于“縉紳論”的大樹之下。“縉紳論”主張突出“縉紳”(gentry)在國家與社會間的中介或價值傳遞作用。由于縉紳在地方政治中的顯赫地位,其上傳與下達實質上保證了國家政權在鄉民眼中的合法性。但《文化》一書對此論不以為然。杜氏覺得該論不能自圓其說的關鍵,在于它奠基于一個不甚牢實的假說之上,即縉紳本身是一個完整的,同時又與其他階層涇渭分明的團體。
與縉紳論者不同,杜氏將自己對國家與社會的分析著眼于兩者間實質的聯系,即國家政權如何從地方攫取財源之上。從有限的南滿資料中,他辨識出兩種不同形式的中介:豪奪型掮客(en-trepreneuralbrokerage)和保護型掮客(protectivebrokerage),前者包括衙門跑腿、“社書”、“里書”、“保正”和“地方”,以包攬稅收為生。由于他們沒有正式的薪資,其收入多基于“陋規(cus-tomaryfees),因此上下其手,魚肉鄉民。而后者多為地方自行舉薦,如“協圖”、“義圖”、“豐脾”,實為對抗豪奪型掮客所設,以冀保護本鄉本地之利益,防止豪奪型掮客從中漁利。
“新政”以來的所謂“現代化”舉措,以國家向地方社會滲透為手段,以達成穩定財源的目的。但是地方政府機構的設立,如鄉區政府、國民黨政府時期的鄉鎮閭鄰制,乃至日據時代的大鄉制,無不增大地方政府對財源的依賴,而導致對豪奪型掮客的倚重。與此同時,如設置警察、保甲等官僚體制化(bureauratiza-tion)又大大削弱了民間團體的功能。興辦實業和教育又多以毀祠堂建學校為捷徑,也使民間宗教組織的功能喪失殆盡。
杜氏對新政以來的“攤款”詳加剖析,突出它對地方文化社會組織解體所起的催化作用。新政以來的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或可以說是一個現代化的過程,歐日諸國于此受益良多。但在近代中國,這一過程所聯帶的官僚體制化過程,卻與地方政府支出膨脹互為表里。因此,“攤款”這一不定期且非正式的稅收,逐漸演變為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這種變相的稅收使得保護性掮客力不能支而豪奪型掮客乘虛而入。由于保護性掮客原為“文化綜”重要的有機部分,它的崩潰就導致了整個文化綜的瓦解。杜氏稱這一悖謬性發展為“國家滯變”(stateinvolution),即一個社會遲遲不能轉型的過程。
《文化》一書有幾個特點,第一,該書大量使用社會學、政治學和人類學的理論。杜氏對于這些相關學科的新近發展,均能把握與消化,運用得體,有時且有獨到之處。第二,杜氏能從一個斑駁陸離的鄉村社會中,梳理出幾條重要的線索,自如地游刃于朝廷國家與野鄙村社之間,上下求索,使國家與社會的主題突顯而不覺牽強。第三,杜氏《文化》一書的理論建樹,雖奠基于前人的學術發現之上,卻并不拘泥于前人的理論,而且將理論與過去的發現溝通并詳加比較,有承上啟下的功效。第四,杜氏取材很有特色。他主要運用南滿鐵路的調查資料,但也親訪了一些村寨,更與當時參與調查整理“滿鐵”資料的日本學者詳加討論,并多方參考了其他中文資料。滿鐵資料曾為馬若孟(RamonMyers)和黃宗智(PhilipHuang)采用,均有成效。而杜氏以新的角度重新審視這些資料,能從“冷飯”中炒出一盤全新的佳肴,其功底可見一斑。
杜甫生本是一個歷史學者,由于大量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其書的史學方面反覺薄弱。杜氏對歷史時期的編年順序處理較為模糊,對時代變遷也甚少觸及。似乎筆下的四十三年的事件并無時間上的序列。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清廷,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及日偽政權雖均可裝入“政權”這一個概念;從歷史學的角度看,其間的變化卻不可略而不提。另外,,他全書所基的材料,僅僅是直隸、山東的六個村莊,以此而推出華北鄉村的全貌,無怪乎勞逸(LloydEastman)戲稱其“理論之探險叫人膽戰心驚”。
杜氏的書從一新的角度觀察近代華北農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科學地”研究社會和文化現象的一次新努力。但是社會和文化的結構和功能是那樣復雜,實際上甚難進行“科學的”總結歸納。西方學術界對于歷史學到底屬于社會科學還是屬于人文科學這一根本問題至今爭論不休。多學科研究恰能有補于兩者間的分歧。杜氏此書的貢獻與不足似都宜在這一大框架中去認識。
Prasenjit Duara,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North China,1990—194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