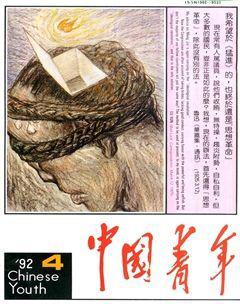理性的認同
段躍
對待社會文化規則,跨世紀人需做理性的認同。
要維持一種特定秩序,單純指望個人善心是不夠的。
如果社會喪失了肅然起敬地對待文化規則的能力,現代化便難以實現。
蔑視規則行為的奏效等于從事實角度鼓勵對現代化經濟秩序的曲解。
無視社會文化規則,成為普遍的社會病;規則,只因它是規則就已置于尷尬的境地。
程農,1964年出生于安徽蕪湖市,1990年畢業于安徽師范大學歷史系,1987年獲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中外政治思想”專業碩士學位。現從事中國人民大學近現代中國思想史教學工作。
記者:近幾年,有一種風氣頗為流行,率性妄為能博喝彩;違反交通規則、無視規章制度等犯規之舉備受同情……以往的正統與神圣在種種反其道而行的喝彩與同情中正漸漸消解著。有人說這是當今世界特別是青年人中的社會通病,即無視社會文化規則病。
程農:耐人尋味的是這種病在個人素質較高的社會群體、特別是高等學府尤為突出,而且得到了一種自覺的欣賞和辯護。其最充分的理由就是反對不合理的傳統文化規則。而事實上許多青年反傳統的行為已變成反對所有社會文化規則,反對規則本身。
記者:總的說,反對不合理的傳統文化規則并沒什么錯,但在實踐中為什么卻導致了這樣的結果,在反對不合理的同時,將合理的反掉;在反對傳統的同時將現代的也反掉呢?
程農:這里涉及的問題很復雜,我只能從思想史專業的角度做些分析。以反傳統為旗號反對所有規則并非今天才有,而是近代以來長時間過程在當代的延續和激化。本世紀初,反傳統思想趨向已在我國達到了白熱化,由于傳統中國與現代化的價值取向不直接吻合,因而拋棄傳統代之以現代化的價值取向總體上合乎中國發展趨勢,確有必要。然而正是在對這種必要性的普遍認同中,反傳統被全面化、絕對化了。
反傳統者自認為站在西方現代化立場反對傳統,而他們所接觸的大多是西方的若干理念。其中最重要的有兩個方面,一是關于個人自由、個性解放與自強進取;二是強調科學、高揚理性,要求以理性尺度審視一切。
就第一點而言,自由原本是普遍法律與規則下的狀態,本身就意味著一種特定的秩序。但反傳統的絕對化立場卻僅僅以個性舒展、沒有限制來理解自由,強調沒有束縛、無拘無束的人性自由。任何規則都意味著某種束縛與限制,要求無拘無束只能意味著反對規則本身。正如一位學者所言,全盤反傳統不是要自由,而是要解放。不是要以一套規則向另一套規則轉換,而是要徹底擺脫一切規則。
就第二點而言,正如對待其他事物一樣,對待科學與理性也應采取辯證態度,不僅了解其長,也要了解其局限。然而反傳統的絕對化立場卻一味強調科學與理性的力量,以致一切都受到理性的審查,唯有理性自身不受審查。于是近代中國社會出現了這樣思潮:沒有節制的理性將科學實證原則無節制地運用于文化規則領域,文化規則因不能科學實證而受到蔑視,認為是“非理性”的貨色。反過來這種“理性”又虛懸一套完美標準如個性解放、真正自我實現等進一步貶斥文化規則,視之為“壓抑自我”“壓抑人性”。這種立場的反傳統顯然正與否定規則本身渾然一體。
記者:的確,反傳統的這些特定立場今天依然存在,80年代后期的文化熱盡管內涵復雜,卻也包括了對這些立場的復興與強化。除了這些歷史的因素外,當代的一系列新因素是否也為無視社會文化規則現象提供了新刺激呢?
程農:這是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有兩點很重要。
其一是中國社會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大變動。改革的深化確實加速了中國社會結構的新舊轉化。但由于改革自身的規律與艱巨性,舊規則的解體與新規則的確立并不同步,致使社會、文化規則方面不確定因素增多。典型的是經濟領域投機可能性增加,機會主義行為流行,蔑視規則、無拘束行事常能奏效……這等于從事實角度鼓勵了對現代化經濟秩序的曲解,這種事實上的規則失調應是當代否定規則的心態比近代更為強烈的重大原因。
其二便是現代西方文化批判思潮的刺激。這些文化批判思潮就其批判資本主義體制而言固然有可取之處,但無限制指責機器文明壓抑人性又顯然有無節制反抗文化規則束縛的特征。同時,所謂“后工業社會”的消費崇拜、享樂主義與強調本能刺激的觀念也已成為西方大眾文化的時髦傾向。這些思潮和觀念自然與中國反傳統立場一拍即合,推波助瀾。
在種種因素的互相作用中,一切規則都從整體上喪失了權威性與感召力。無論是事實存在的,還是觀念形態的;無論是傳統的,還是真正現代化的。規則,只因為它是規則就已置于尷尬的境地。由于任何形式的自我約束與節制在“理性”審查下卻顯得缺乏道理,傳統規則“克己復禮”式的限制固然遭到唾棄,現代化所需要的節欲苦行、追求成就的“企業家精神”也一樣得不到信奉。“事業心”在相當一部分青年心中越來越成為笑柄,取而代之的是享樂主義。這種當代享樂主義絕然不會滿足于恬然自得的意境而是以釋放本能和感性崇拜為特征,尋求無止境的刺激。
記者:值得討論的是,蔑視規則、崇拜感性的時尚是把“個性張揚”作為正面旗幟的,按照許多青年的理解,個性張揚相對于傳統的個性壓抑是否具有進步意義?
程農:這依然要從反傳統者對個性張揚的特定理解中尋找答案。我認為當一種個性主義只是以千篇一律的蔑視規則、崇拜感性為內容時,當這種千篇一律的個性主義又成為大眾的共同時尚時,它就幾乎注定只是一種偽個性主義了。這樣的個性主義者也許比公眾更敢犯規,更敢宣泄本能,更敢尋求刺激,但再清楚不過的是自己的行為必會博得公眾的欣賞。其實“個性”在此只是一種外部裝飾,骨子里不過媚俗而已。也許這種媚俗給人以快感,但那絕不是個性,除非我們說:快活即個性,難受即無個性。
我想,真正的個性決不表現為奇裝異服、違反交通規則,而是由于內在的思想資源與信仰依托能對事物保持獨立判斷。唯有那些除去人人都有的本能與感性之外內心空蕩的人,才會急于佩戴個性標簽。真正的個性總是稀缺的,當“個性張揚”滿街都是時,必是贗品。
記者:看來這里既不是真的反傳統,也沒有真的個性主義,充其量是“返回原始”的世界性時髦在中國的特定表現。然而,這一切之所以在中國循環往復了半個多世紀,是否與人的內心活動有不謀而合之處?
程農:必須承認,這種反文化的浪漫態度自有其哲學魅力,少數心靈敏感的人可以從中開掘出撼人心魄的體驗與理念。同時這種浪漫態度在當代青年群體中大眾化、庸俗化之后,與理性相比更能提供“痛快”與“舒坦”的感覺,令人難以抵御。然而,當我們將其作為社會性問題討論時,任何人都能看出,如果一個社會已經喪失了肅然起敬地對待文化規則的能力,如果“認認真真”作為一種社會態度已經消失,那么,不僅現代化的新規則體系難以確立,而且現有的社會秩序也不會順暢運轉。規則喪失權威性的現象妨礙著中國向現代化的轉化。
記者:許多人認為這種蔑視規則現象是由當代人的善惡標準不清、道德淪喪所致,而要樹立規則的權威性則必須從確立新的道德觀念開始,你怎樣看?
程農:這里必須解釋的是,文化規則與善惡道德并非一回事,蔑視規則也并不是直接的道德淪喪。這問題比較復雜,如果允許簡單化的描述,可以認為,文化規則是指特定文化經長期演化而成的一整套規范,文化秩序由此形成,置身其間的人都清楚該如何與人交往,如何行為。而善惡道德則主要是指人內在的抽象道德素質,既在文化之中,又超越文化,與特定文化規則并不直接聯系。當代小說家王朔在試圖將自己的“現代派”主人公描寫得可愛時,便觸及了這種區分。這些主人公往往對公共規則視若無物,但卻可以偶爾表現一點惻隱之心與正義感。
要維持一種特定秩序,單純指望個人善心是不夠的,而應主要依靠客觀文化規則的制約。當文化規則喪失權威時,一方面原有為文化規則所制約的邪惡因素得以膨脹,刺激了道德淪喪的加劇;另一方面人們不得不乞靈于道德以求維護秩序。殊不知純粹的道德振興是難以駕馭復雜的文化規范的。
顯然,建立文化規則的權威性只能作為社會文化問題予以解決,根本的努力在于社會、經濟方面。正如民族自信不能靠愛國表態,只能由民族不斷進步才能增強,蔑視規則的現象也只能在新規則體系的確立過程中逐步沖淡。
作一個樂觀的估計,對于社會文化規則我們這代人很難再如前輩一般敬畏,但社會文明的進程會引導著我們用理性去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