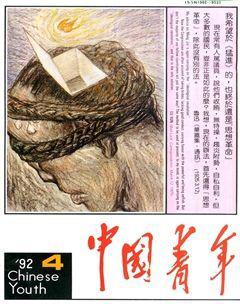哭悼相聲
楠客
相聲,你死得好慘!雖說這幾年你一直病病殃殃的,大家知道你命在旦夕,但畢竟現在藥多,你還沒試過幾味藥呢,就這么走了?
我知道你命苦,兒時就是討飯的營生。窮哥兒們愛你但接濟不了多少,達官貴人拿你消閑,你要想得到那一點點賞賜,就必須“關公戰秦瓊”地討他們的喜歡。但是自從人民當家作主,你的日子就好起來了。五彩斑斕的現實生活為你注入了豐富的營養,侯寶林、馬三立、郭啟儒等藝術大師的創造提高了你的地位,《醉酒》、《夜行記》、《秘訣》等大批佳作使人民喜愛得至今仍有很多人可以倒背如流。這些藝術家們也得到了人民真誠的喜愛和崇高的敬意,侯寶林先生成了北京大學的教授。
相聲,我和你相識也晚。但我大概在搖籃里的時候就喜歡你了,算得上接觸最早的文藝樣式,你是我文字和文學上的啟蒙老師、恩師。自從知道了侯寶林、馬三立、馬季,我敢夸口,數得上的相聲段子我幾乎全聽過,那里面的智慧、學識、真理,令我陶醉,促我上進。
但自從數年前有一些個年輕的、好像還冠之以“星”的相聲演員在臺上互相謾罵,甚至拿對方的姐姐取便宜;《釣魚》說得那么好的一個演員自扇嘴巴;大禿瓢成了營造氛圍的“殺手锏”;大舌頭、聾啞人、五花八門的方言土語、拿腔捏調的“引吭高歌”成了永恒的題材——我就知道你病了。前些時候有個大鼻子朋友進入相聲界,本來是件新鮮事,滿不錯的,但是他說“北京的姑娘都愛我”;說相聲的還有了女的,依我看,相聲一有女的就別扭,果不其然:上乘的不過是能唱,中間的是僅僅能拉得下臉,下作的便令人作嘔了。比如,有個女演員問她的男搭檔:“你媽沒教過你?”“沒有。”“那我跟你說,”——一個大姑娘當眾蹦出這么句臺詞,且自我感覺極為良好,真令人目瞪口呆。還有兩位女軍人說相聲,拿彼此的著裝作笑料,弄模弄樣,還以為得意,殊不知惡心死人……至此,我知道你病入膏盲了。
元旦晚會上,中央電視臺是花了大功夫的,總的來說編排精巧,五彩紛呈,蠻好的。但馮鞏、牛群說《91熱門話題》,互相損。馮鞏說牛群捐獻給災區的棉襖穿了30多年,最后千里迢迢用新的去換,蓋因為棉襖里有5000元存款單;牛群說馮鞏一年級上了二年,二年級上了四年,是個大笨伯……一會兒說植樹造林的一干人吃喝好了爬起來就跑,因為忘了帶鐵鍬;一會兒說有個小孩子和謝軍弈棋下成平手——原來是馮鞏的兒子。無聊之極不說,還煞有介事地向軍人、教師送禮品,弄得敦厚之輩不知所措。整臺晚會,那段相聲就像是一杯美酒里的一只死蒼蠅。
相聲,你死就死了吧,但是總要讓人知道病因。據我對你的了解,你恐怕一是長期缺鐵,貧血。侯寶林先生把相聲藝術推向高峰,除了他對人民深切的愛和至微的理解,還有鉆研學問一條。你且看他讀了多少書?古今中外,簡直無所不通。你看他會多少本事?吹拉彈唱之外,還有石粉灑字那一手絕活。胸中的墨水就是你的血,生拉活扯地瞎白呼,與販夫走卒的插科打諢比起來,還要等而下之得遠呢!二是四體不勤,養尊處優慣了,當然要半身不遂。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生活多么豐富,他們有多少妙趣橫生的語言,有多少對現實陰暗面辛辣的諷刺,又有多么深刻的理解。最近我下鄉采訪,就聽到某地的群眾說腐敗了的干部,說他們非常廉潔,“兩袖清風,一肚酒精”,“大吃不大喝,跳舞不亂摸,打牌不賭博,受賄不勒索”。這不比在對方姐姐身上找便宜之類生動精彩?姜昆、李文華的《如此照相》,侯躍文、石富寬的《救火》,馬季的《誣告》,與生活那么貼近,所以才膾炙人口。現在趙本山的小品比相聲不知要貴多少倍,其實訣竅正在于貼近生活。
相聲,你不同于人,死了還能復生的。只要你深入生活并且勤奮地學文化、學科學、學藝術,你會活過來的。不過,我不希望你只是簡單地復活,而希望是一次涅□,像經過烈火洗禮的鳳凰,更加英俊,更加燦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