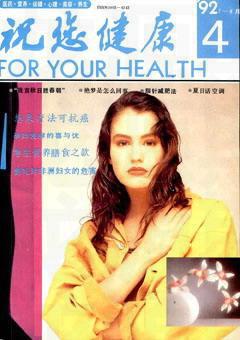精神療效
人有了病,十有八九都去求醫,吃藥,打針,不惜一切代價。也有提倡精神療法的,諸如“清心”、“舒懷”,凡事想開些,聽天由命,往往也能驅逐病魔。
精神和肉體,原是一個統一的東西,一榮俱榮,一枯俱枯。生理上患了病,精神上便爽快不了,精神不振,病毒更容易乘虛而入。
這是常識。人患了絕癥,決不會去找哲學家治療。
但是我卻發現一種“秘方”——編輯也能治病,而且治的是絕癥。
我在青海人民出版社任編輯期間,遇見兩個這樣的病例。一位是《馬步芳統治青海四十年》的作者陳秉淵。陳先生把他的書稿交到出版社的時候已經年近古稀。書稿尚在排印中,他忽然患了重病,這部書是曹玉禎編的,他得知陳先生病危通知下來了,非常著急,便趕緊催促印刷廠盡快裝訂兩冊,希望陳先生能在生前看一眼他的著作,書到醫院病床邊,陳先生恍惚中認出自己心血的結晶,精神一振,不久就病愈了。我又見他到省政協上班,數年后才壽歸天年。
另一位是西北師范學院的教授常校珍,他寫了一部《勸學新篇》,我是這部書的責任編輯,可是我還未見過這位先生,他從事教育研究,他的著述引經據典學富五車,據我猜測,他總有六七十歲了。我接到書稿不得不查經覓典,生怕發生錯誤有損教授尊嚴。不料,編輯的中途接到著者惡訊:他患了癌癥,他說醫生只給他不到半年的時間,如果書在半年以后出版。他就見不到了,信寫得凄凄慘慘,我含淚卒讀。于是,我只好草草收兵,二審、三審也以十分同情的心境盡速審畢付梓。我雖然知道印刷周期一般都在三個月以上,但我卻寫信告訴他近在目前,此書也是提前印制的。我一接到樣書就寄出了,書上了路,我才作最后一次的校閱。
1981年冬,我到蘭州參加西北寫作學會首次年會。在蘭州飯店一住下就趕緊給常先生打電話,我真怕沒人接。兩個小時后,他就趕到飯店來了,見了面我才知道,他不過是個五十來歲的中年人,他把他住院時的醫生也約來了,讓醫生親自證明他的患者是出版社洽好的。據醫生說,常先生患了胃癌,而且到了后期,術后至多能活半年,醫生還描述了患者看到《勸學新篇》樣書時一躍而起的情景,不論醫生怎樣勸阻,患者仍是坐在病床上一氣把十幾萬字的書讀完了。現在一年過去了,醫生再作檢查,患者身上的癌細胞不僅沒有擴散,而且徹底消失了。常先生神采奕奕,說他正在寫另一部有關教育學的書。
我沒有讀過《吉尼斯大全》,不知道它是否收集過這類事情。我講的兩個故事既真實又平凡,乍聽起來也許覺得既荒誕又奇妙,而其中的奧秘,卻值得研究。
十年前,在一個縣醫院里,一個更奇妙的現象在我熟識的一位青年身上發生了。他不過三十來歲,身體壯實如牛。他因咽部不適住進醫院,幾經檢查沒能確診病情。有的醫生說,他患了慢性咽炎。他從重重疑慮中解放出來,每應付完查床之后就到球場參加業余籃球賽。不久,又有一位醫生否認了咽炎的診斷。禁止他再作激烈的運動,他復人疑團,連起床的勁頭也沒有了。后來確診為食道癌。兩位醫生一致宣布是咽炎,他又參加了一場球賽,并且要求出院。不料確診癌癥的消息走漏了,這青年的精神一夜之間垮了下來,不到一個月就一命嗚呼。
由此看來,醫生和神父各有妙用。白求恩的手術刀可以切除千百人的痛苦,有時,連神父娓娓動聽的說教也能消除不少人的煩惱,異途同歸,人類的健康要靠各種方法維持,疾病不可能一刀切除,心理療法往往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不同的是,醫療多借助于外力,精神治療主要靠自己。
(王立道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小說家兼散文家,曾長期從事新聞出版工作,現任青海作家協會副主席,出版有長篇小說《沙沱情暖》《南園風情錄》和散文集《霜后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