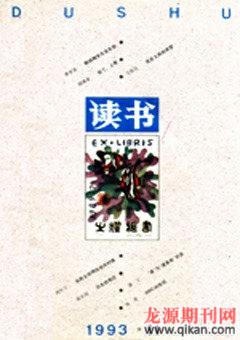六十年前“出來事”
王妙發(fā)
“出來事”是一句日文,意為“發(fā)生的事”,中國人可以望文生義,在這里或沒有大錯。說的是距今整整六十年前,一般被認(rèn)為是日本現(xiàn)代史上最黑暗年代的“出來事”。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當(dāng)時的文部大臣(教育部長)鳩山一郎下令,免除京都帝國大學(xué)(今京都大學(xué))法學(xué)部瀧川幸辰的教授職務(wù),用現(xiàn)在的話說叫剝奪公職,因為京都大學(xué)是國立大學(xué)。理由是瀧川幸辰是赤化教授,他的刑法學(xué)說是“馬克思主義的”。這即是日本一般現(xiàn)代史教科書上都要提到的代表性地反映了那個思想統(tǒng)制時代的所謂“京大事件”,也叫“瀧川事件”的引發(fā)點。
上面說的只是這件事情的起點,接下來當(dāng)然還有種種場面、情節(jié)要“出來”。筆者在這里想先羅嗦幾句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并且好像有必要從比較遠(yuǎn)的地方開始羅嗦起。
早在大正三年(一九一四),當(dāng)時的京都大學(xué)校長澤柳政太郎,新官上任伊始,就要罷免七個教授,理由是學(xué)問和人格皆不適宜為帝國大學(xué)的教授。當(dāng)時日本有大學(xué)的歷史還不久,這事情是沒有先例的。所有教授們自我感覺都特好,憑什么隨便就要敲飯碗?更何況大正初年“德先生”在日本也正大領(lǐng)風(fēng)騷的時候,校長的獨(dú)斷專行成了眾矢之的。并且確實還有一個“學(xué)問和人格”標(biāo)準(zhǔn)的問題,校長一個人又有什么資格可以隨意對此作判斷?如何容得這種專斷?!于是軒然大波而起。教授們的抗議以法科大學(xué)(法學(xué)部的前身)為最激烈。校長堅持認(rèn)為自己有完全的任免權(quán),而法科大學(xué)的教授們則堅持認(rèn)為校長的任免必須先獲得教授大會的同意。雙方對立嚴(yán)重,相持不下,一直發(fā)展到法科大學(xué)全體教授集體提出辭呈。有必要一提的是,說是仗義執(zhí)言或者說是惺惺惜惺惺都可以,總之當(dāng)時東京大學(xué)法科的教授們是以各種方式全力支持了京都大學(xué)的教授們的(后來的瀧川事件時這份仗義或同情則沒有再現(xiàn))。此事之所以有必要一提的是,東京大學(xué)和京都大學(xué)是日本東、西兩座舉足輕重的學(xué)府重鎮(zhèn),此“二發(fā)同舉”,可以說日本學(xué)術(shù)界大體就全動了。
澤柳校長的罷免令最終未能生效,文部省承認(rèn)了教授的任免需經(jīng)教授大會的同意。澤柳政太郎本人,則是在任校長一年以后即去職了。頗有點灰頭土臉。
這是先已有過一次了的因人事權(quán)而引起教授抗?fàn)幍乃^“澤柳事件”。
此事件以京大教授們的大勝為終。以此為契機(jī),一個本已在形成中的制度先是在京都大學(xué)、繼而在全日本的大學(xué)中被確立,即所謂大學(xué)自治,并且一直具體到各學(xué)部(系)。形式是各學(xué)部(系)從人事到教學(xué)計劃的幾乎所有的決定權(quán),全部歸各學(xué)部(系)的教授大會。校長僅以名義對人事“執(zhí)行任免”,文部省則只是備案而已。實際真實到何種程度且不說,起碼形式上這以后文部省以及大學(xué)校長本人都已無權(quán)直接任免各系(學(xué)部)的教職人員了。
因為曾經(jīng)有過這樣一個“澤柳事件”,到了將近二十年后的“瀧川事件”時,應(yīng)當(dāng)算是第二次因人事權(quán)而起,實質(zhì)是教授要求學(xué)術(shù)自由、大學(xué)自治與官方無視或者準(zhǔn)備剝奪這種自由、自治的交鋒了。說起來當(dāng)然是文部省嚴(yán)重違反已有的游戲規(guī)則,教授們是二十年前嘗過甜頭了的,或許還在以為天下既然已經(jīng)打了下來,這倒毛豈是隨便捋得的?
只是時代不同了。
本世紀(jì)三十年代,正是軍國主義熱度最高,對外大舉擴(kuò)張、對內(nèi)嚴(yán)厲思想統(tǒng)制的時代。或許多少還存有一份崇儒傳統(tǒng)的緣故,當(dāng)局在要對知識界開刀時相對而言還算比較謹(jǐn)慎,或者應(yīng)該說更多的還是狡詐和陰險,然而已經(jīng)絕不缺乏堅決了。
“瀧川事件”的開始是在當(dāng)年二月。眾議院預(yù)算委員會上,當(dāng)時政友會的宮澤裕(前首相宮澤喜一的父親)已經(jīng)提出要開除東京大學(xué)和京都大學(xué)的幾個“赤化教授”(東大三人,京大一人)。——至于后來為什么只拿京大開刀后面要說到——以后,四月份,瀧川幸辰的《刑法讀本》一書被禁。同時,文部省對瀧川幸辰本人發(fā)出“自行辭職勸告”,若不接受則將強(qiáng)行開除。當(dāng)時的京大校長小西重直站在校長的立場上對文部省的舉措表示不能接受,認(rèn)為不能僅以學(xué)術(shù)觀點為理由而動搖教授的地位,如果強(qiáng)行開除的話則更將引起其他糾紛,希望文部省方面改弦更張。只是“上面”的態(tài)度非常堅決,沒有商量余地,對校長的意見未予理會,還是強(qiáng)行發(fā)出了開除瀧川幸辰教職的命令。
且看當(dāng)時京大方面的反應(yīng)——
不用說從四月份《刑法讀本》被禁開始已經(jīng)群情激憤。文部大臣命令5月26日下午五點生效,法學(xué)部全部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副手(這個職名現(xiàn)在已無)即全部教員三十九人“立刻”舊技再演:同時辭職,包括學(xué)部長(系主任)宮本英雄在內(nèi)。法學(xué)部先已在開學(xué)生大會討論這件事。隨即學(xué)部長就在學(xué)生大會上宣讀了全體教員的辭職聲明。抗議(聲明)文字雖然還是文謅謅的,但對當(dāng)時法西斯主義的猖獗已深含危機(jī)感:“在以追求真理為使命的大學(xué),研究的自由是不可或缺的。(這種)研究的自由不用說包括思索的自由和教學(xué)的自由,(政府既然)承認(rèn)研究的自由而又不允許教學(xué)的自由,可知是對這種(自由)本義的無知”。
學(xué)生大會當(dāng)即通過決議向文部大臣抗議,其他各學(xué)部的學(xué)生也有集會、罷課等抗議活動。以此為始,學(xué)生和知識界的抗議運(yùn)動波及全國,并且是旗幟鮮明地反法西斯的。
當(dāng)時的齋藤內(nèi)閣相當(dāng)蠻橫,非但無視全國知識界的抗議,而且照樣再次發(fā)令,把提出辭呈的教授中的十五人,毫不客氣的罷免了六個。其他九個則予以駁回。
需要補(bǔ)充一句的是,被駁回的九個教授中的七個,倒也有趣(知趣),開起新的教授會,決定撤回辭呈,并發(fā)表聲明,稱鳩山文部大臣既然已經(jīng)明確表明,瀧川幸辰的免職是屬“非常特別的場合”,并不否認(rèn)大學(xué)自治這一“多年的先例”,因而法學(xué)部(大家抗議)的目的已經(jīng)達(dá)到云云。——這種時候會有這樣的事,也就不算意外吧。
對此,副教授以下十八人中的十三人不予理睬,最終辭職他去。
小西重直校長見自己全然無能為力,也在瀧川幸辰離校不久的當(dāng)年六月,辭去了校長職務(wù),在職僅三個月。
教授們在“澤柳事件”時是大獲全勝了的,這一次可是確確實實輪到了他們鼻青臉腫了。事后鳩山一郎文部大臣在眾議院不無得意地說,文部省“看來已經(jīng)可以”自由地更換被認(rèn)定為不合格的教授了。政府方面全勝凱旋。
與澤柳事件當(dāng)初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東京大學(xué)方面的態(tài)度,瀧川事件事發(fā)后,除了有個別教授以個人名義表示支持以外,東大方面,特別是東大法學(xué)部,一直保持了沉默。這和東大沒有被開刀一事是否相關(guān)?后面還要談到,是一個歷史之謎。
當(dāng)時的學(xué)生運(yùn)動用這里報紙的話說,是最終被鎮(zhèn)壓。筆者查閱過當(dāng)時內(nèi)務(wù)部警保局保安課的有關(guān)文件,有大量的電話電報記錄,包括各種學(xué)生集會的地點、時間、出席者名單、所作決議等等,不厭其詳,地域遍布日本各地,可見內(nèi)控是相當(dāng)?shù)闹苊堋.?dāng)然并沒有到此為止,各地都有學(xué)生被捕,據(jù)報道被捕學(xué)生中卻是以東京大學(xué)為最多。不過,稍感意外的是,或許尊儒重道的傳統(tǒng)在政府那兒還沒有徹底失墜,而讀書人也還勉強(qiáng)支撐著搖搖欲墜的使命感、尊嚴(yán)感,知識界好像還一直存有著一小份言論自由的特權(quán)。當(dāng)時知識界、新聞界不少討論京大事件的文章,大多數(shù)程度不同地批評政府的舉措,認(rèn)為是粗暴壓制學(xué)術(shù)自由和無理干涉大學(xué)自治。而政府方面好像也頗容忍了知識界的這種自由化,沒有看到有關(guān)當(dāng)時在知識界大規(guī)模清洗和鎮(zhèn)壓的材料,或許尚未公開,起碼筆者沒有翻閱到。
補(bǔ)充一句或許毫無必要的廢話:在那個時代,公開支持政府作法的報系自是也有,如每日新聞報系和時事新聞報系。只是不多。
瀧川幸辰教授自身,去職后先是開業(yè)當(dāng)了專打刑事官司的律師。戰(zhàn)后不用說是“徹底平反”,恢復(fù)京大教職。先為法學(xué)部長,后來并當(dāng)過四年京都大學(xué)校長。更有兩件必得一提的:一是校長任期中,曾被左派學(xué)生“長時間監(jiān)禁”(瀧川自語),事在一九五五年,是左派學(xué)生運(yùn)動頗成氣候的年代;另一是京大校長任滿退休后,一九六○年起,每年新年去皇宮為天皇“進(jìn)講”,事屬殊榮,年譜上特別要大書一筆的。須知這是當(dāng)年被指稱為“赤化教授”的先生。不管在哪里,有權(quán)者一旦蠻橫無理和荒唐起來,也真是叫人哭笑不能!
筆者頗多事,在圖書館找出了當(dāng)年被禁的瀧川幸辰的《刑法讀本》來翻了一下。在作為主要被禁理由之一的通奸罪的解說中,只是很客觀的引述了對此全然不罰的蘇聯(lián)刑法,并有女性的經(jīng)濟(jì)獨(dú)立是男女平等的前提(這大概可以算是馬克思主義觀點了)的說法而已。被批評的除了當(dāng)時的日本刑法,還包括了中華民國刑法等只罰女性不罰男性的亞洲系法律。可以說通篇看不出我們看慣了的包括那個年代出版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dǎo)”的寫作風(fēng)格。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的,不如說主要還是自由主義的吧,看來這或許可以算得是一個真正的冤案了。
事情過去六十年了,完整的一個花甲。只是這段歷史還沒有“完整”,或者應(yīng)該說歷史本來不可能完整。有一部分當(dāng)時的公文資料至今尚未公開,前面其實已經(jīng)提到過,起碼至今還有兩個謎尚待解開:
1 最早被指稱為“赤化教授”并要求制裁的另有東京大學(xué)三個教授共四人,為什么當(dāng)局先開京都大學(xué)的刀?
2 東大的三個教授為什么最后竟能免此一難?以及東大方面集團(tuán)性的支持為什么沒有?
據(jù)京都橘女子大學(xué)松尾尊兗教授的“推定”,這兩個謎底應(yīng)該是:
1 鑒于此前曾發(fā)生過的“澤柳事件”,京大是自由化的重災(zāi)區(qū),政府方面認(rèn)為拿京大開刀最為有效,可起殺一儆百的作用,而且有可能從根本上摧殘已成制度的所謂大學(xué)自治化。后來的事實也證明政府方面的目的是達(dá)到了的。前面已經(jīng)引過鳩山一郎的話,政府方面大體已經(jīng)對大學(xué)掌握自如了;
2 至于東京大學(xué)為什么沒有被開刀?有一種說法,是因為當(dāng)時的文部省和東京大學(xué)校長之間有密約。即我不開你的刀,你也不能拆我的臺。瀧川事件事發(fā)后,東大的個別教授以個人名義表示過支持,東大方面,尤其是東大法學(xué)部,一直沒有集團(tuán)性的表態(tài),與澤柳事件當(dāng)初判若兩者。這應(yīng)該算是東大歷史上的一個污點了。此事雖說還缺少完整的資料證實,但有兩個事實已可作為旁證無疑了。一是鳩山一郎自己在戰(zhàn)后曾承認(rèn)有過密約一事(見《サレテ一每日》一九五一年六月三日);另一是戰(zhàn)后當(dāng)過東大校長的當(dāng)年法學(xué)部教授之一的南原繁,曾對當(dāng)時沒有表態(tài)一事表示過終身遺憾。
事情過去六十年了。在一般日本人眼里這已經(jīng)是非常遙遠(yuǎn)的歷史了。日本的非這門專業(yè)的學(xué)人好像也已經(jīng)完全不關(guān)心這類看來毫無現(xiàn)實意義的歷史了,在歷史已經(jīng)被宣布為結(jié)束的今天。文化界小有一些紀(jì)念活動。當(dāng)年的當(dāng)事人,先生輩的多已作古,學(xué)生輩的也垂垂老矣。五月二十六日東京學(xué)士會館的六十周年紀(jì)念集會,大家心照不宣,怕是最后一次了。留下來一點是否算謎的謎,剩給歷史學(xué)家去吧。
筆者讀這段歷史,再一次從心里涌出一種無能感,甚至是自卑感。筆者不專門搞日本現(xiàn)代史,不過說起來總也是在歷史學(xué)這塊園田里磨蹭著。然而腦子里卻不時冒出來一個物理學(xué)家的話:“在歷史這門學(xué)科里我不能獲得真理。”當(dāng)然可以問真理是什么?這會越扯越遠(yuǎn),只說真實吧,歷史學(xué)家能夠獲得真實么?這本來是歷史學(xué)的上帝。
當(dāng)事人還沒有死絕,“真實”的載體還生存著的時候,歷史學(xué)家對著他的工作目標(biāo)反而是無能的。當(dāng)然他可以先“考證”起來,條陳辨析一些目標(biāo)周圍的雞毛蒜皮,其實是被先天地規(guī)定為暫時失業(yè)!將來史料全部公開了,真實(不是真理)是不是就全盤獲得了呢?如果在大學(xué)一年級的時候,我會回答說當(dāng)然。現(xiàn)在,恐怕只好說,有點兒自卑。
這篇小文寫完了,我問自己,為什么我要關(guān)心這件六十年前的“出來事”?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五日寫完,日本“終戰(zhàn)”四十八周年紀(jì)念日,于大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