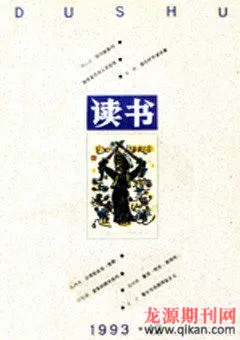《陰翳禮贊》
1993-07-15 05:30:02于飛
讀書 1993年12期
于 飛
這書名的朦朦朧朧,先就教人產生一分驚訝。大約是怕這種朦朧會使人產生誤解吧,中譯本(三聯書店一九九二年版)為之加上一個副標題,叫作“日本和西洋文化隨筆”。自然這里面娓娓縷陳的瑣瑣細細,皆可歸類于文化,但它一下子把那一種令人玩味的意趣,醒豁得不留余地,倒真像是作者所不喜歡的那個現代化的電燈了。
所謂陰翳,大抵是一種境界罷,朦朧的,幽迷的,彌漫著低回不已的情與思。芭蕉徘句有“炭火埋灰里,客影壁上游”,或可作為陰翳的注解之一。
“女人就隱藏在這種永遠幽暗的黑夜深處,白天絕不拋頭露面,只是像幻影一般出現在‘夜短夢苦多的世界里。”“古代男人所愛慕的并非女人的個性,亦非看中了某個特定女人的艷麗容貌或豐滿肉體。對他們來說,正如月亮總是同一個月亮,‘女人也永遠是一個‘女人而已。大概他們認為在黑暗中微聞其聲,微覺衣香,觸其鬢發,摸其肌膚,想象其嬌媚之態,一旦天亮,便消失得無影無蹤,這一切才是他們心目中的‘女人吧。”漢代李夫人的故事,正好可以做個印證——夫人死后,武帝思念不已,于是有方士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日:‘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這“是邪非邪”,便是陰翳所營造出來的情境了。女人是可以用來象征美的極致的,那么,應該可由此而推及其他。
黑夜與白天交替,是自然之和諧。然而現代社會中的人類卻無視造物的錫予,偏用技術的手段在黑夜中復制白天,這是聰明還是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