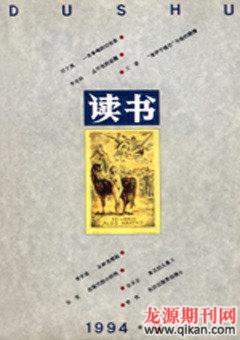欲知生 先知死
陳東有
《中國死亡智慧》認同海德格爾“向死而在”的觀念,但其智慧的基礎還是建筑在本土文化之上。作者把儒、道、佛、墨、法五家散于各類典籍中有關死亡觀念的論述搜集起來,作為自己闡發觀點的起點和借鑒。
儒家從死亡本體論出發,得出的對死亡必至的理性主義態度,使人們可以避免通過信仰或道術尋求靈魂永生、肉身成仙的宗教迷誤,但儒者并非因此而放棄使“生命”趨于永恒的努力,恰恰相反,儒家學者對超越“死亡”的問題有著極為濃厚的興趣。所以,儒家重視生命的全過程中道德價值的實現,以個體之人向整體之德靠攏,以生命的有限進至道德的無限,從而在精神上超越死亡;在實踐中,儒家把自己認定的道義和道德價值置于“生死”之上,生為道義而奮斗,死為道義而獻身,死亡就不是痛苦的個體毀滅,而是道義的最終實現,是一種內心感到欣慰的行為。
道家“生死齊一”的觀念,把生與死都看作是自然大變化演變的一種形式,“生”是自然而然,“死”也是自然而然,所以不必因生而喜,不必因死而悲;“生”為暫來,“死”為暫往,不必執著于“生”,也不要迫切地求“死”。老子的“死而不亡”和莊子的“逍遙游”更是超越生死、追求個人精神世界的大自由,從透悟大道到合于大道,物我兩忘,與天地共存以致“不朽”。道家死亡觀雖然比儒家更為玄虛,然而作為哲學智慧,更為深切透徹。
佛家把“死”看作為一種中介,因為人不僅有一“生”,而且有無數循環之“生”,而“死”不過是這種輪迥不已之“生”的中介和橋梁。人生通過“死”的環節循環無窮,生而死,死而又生,生是苦難,死也是苦難,世俗人便要承受這生生死死的命運痛苦。而只有一心向佛,從體認現象界的一切皆由“因緣”和合而成,到看破宇宙萬物盡是虛空,然后悟解“真如”的永恒,便可超脫生死輪迥,進入佛界。佛家這種宗教死亡智慧,奧秘無窮,但在現實生活中往往是難以仿學與付諸實踐的。
代表下層民眾思想的墨家在死亡觀念上,反對儒家的命定觀,本諸“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救世精神,更多的是采取一種實用的經驗主義方法,重在對死進行效用性的實利考察,對“死”取一種純理智的態度,推崇一種積極有為的生死觀。這種生死觀不同于儒家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殺身成仁”,而是以對天下蒼生奉獻實際利益的“義”作為價值取向,義貴于身,為義可以慷慨赴死。墨家這種極強的功利死亡觀對下層農商賈民眾的影響極大,今天看來,摒棄天命,努力有為,慷慨赴死,英勇就義仍不失為一種積極的態度。
法家的死亡觀主要表現在韓非子的論述中,他從“定理有存亡”的角度觀照死亡的本質,又借助于老子的“道”來打通本體界與現象界,從而提供給人們一種理智的死亡觀。但是,法家強調生死有定理,加上“性惡”觀,便認定人們在利己之心的驅策下,可以赴死不懼,君主們則可以利用這一點來治國安邦;且政治的價值高于一切,國家的穩定重于民眾的生死,甚至以民眾的死亡來換取國家的穩定。所以法家的死亡觀更多的是冷酷,在以人為本位的現代社會,這種死亡觀是不可取的。
很明顯,《中國死亡智慧》在論述五家死亡觀的同時,已表明了自己的抉擇。歸納起來,即是作者闡發的現代死亡觀:無疑,在科學已經十分發達的現代社會,以現代科學為基礎,建構正確合理的死亡觀是十分必要的,這不僅有助于解決目前醫學界、法學界已提出來的諸如“安樂死”“臨終關懷”等問題,更重要的還在于它的人文精神,在于人自身終極價值的實現。死亡觀應該真正地成為人生觀的組成部分,并介入醫學、法學和倫理學領域,成為人類更客觀地認識自己、安排自己并進而認識世界、促進人類進化的重要途徑。人類首先應客觀地對待生理死亡,即個體的毀滅。只有最充分地認識人的自然屬性,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地認識人的社會屬性。超越死亡,就是使有限的個體與無限的整體相結合,使有限的生命進至無限的精神境界。肉體不可能永存,具有社會意義的個體精神卻可以永恒。當一個人意識到這種關系,并付諸實踐,那么他就可以直面死亡而摒棄任何恐懼心理,死亡就不再是可怕的終結或無可奈何,而是一種現代意義上的涅
欲知生,先知死,應該是一種更具智慧的認識邏輯和思維邏輯。
(《中國死亡智慧》,鄭曉江著,臺灣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四年四月版)
——由刖者三逃季羔論儒家的仁與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