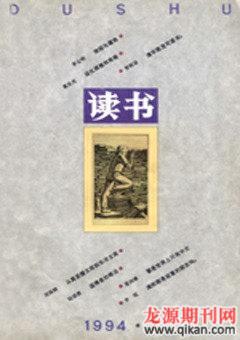夢為蝴蝶亦還鄉
于 飛
林清玄寫了一組菩提系列:《紫色菩提》、《鳳眼菩提》、《星月菩提》、《如意菩提》、《拈花菩提》和《清涼菩提》。我只讀到了第一種和最后一種。都是很美麗、很清澈的文字,有著明心見性的智慧。他把佛理、佛的境界,引入世俗的社會,在碌碌紅塵中,懸一面清明之鏡——照見世俗的種種無謂和佛界的萬法清涼。
最喜歡一篇題為《娑婆世界》的文字。因為我也久欲以此為題,寫幾行文字,但終于沒有寫——總以為自己是“一闡提”,既不研習佛典,更不解佛典的精義,不過妄念、妄見而已。現在有了一個發言的機會,我便以自己的感悟,體證自身的佛性——不是“一闡提也能成佛”么?
布頓大師在《佛教史大寶藏論》中說:此世界名娑婆,意為忍。是說不為煩惱三毒所劫奪,而且樂意忍受,以能堅忍,故名堪忍。此說本諸《大悲妙法蓮花經》,三毒,謂貪欲、嗔恨、愚癡。佛之教化眾生,便是從這娑婆世界講起,便是這世間法。佛法便如蓮花,出于污泥,而灼灼其華,不為污泥所染。但倘若只是虛空,只是清水,蓮花將所由生呢?就佛祖的一生來看,出生、覺悟、涅
所謂空、無,是說世間沒有永恒的東西;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
《百喻經》中有一個故事,說從前有一位國王,喜得一女,因喚來醫生,吩咐道:給我找一種藥,讓我的女兒立刻長大。醫生答道:藥自然是有的,但是倉促之間卻無法找到。給我時間,好嗎?只是在此期間,請國王不要去看她。醫生便往遠方求藥。一去十二年,取得藥來,侍侯公主服下,然后出見國王。王大喜,以為良醫,即命左右以珍寶相賜。左右便笑國王之愚——不解自然規律,而迷信藥力。
人是自然之子,本該依賴自然,護持自然;依賴自己,護持自己,果能如此,便是無上覺悟了。佛所施為,若視作是藥力的話,便是不斷向人顯示自然的規律,不斷喚起天性所存有的免疫力,使有情識、有愛欲的眾生,在有缺憾的婆婆世界中,不迷失本性。“佛教所說的出世間,就是要經過修學止觀,認清因果的規律和無我的真理,在一切時、一切處、一切事業中,斷煩惱、破無明,而盡一切力量作利益眾生的事。”這原是世間智慧,又何曾離了世間呢。
作為“有情”——佛典釋“有情”為“有情識、有愛情之動物”,雖然明知升沉榮辱不過一枕黃粱輕夢,漫漫人生不過彈指一揮間;也明知浮華是空,功名是幻;“好”即“了”,“了”即“好”,卻依然要認認真真走完這屬于自己的從生到死的每一步;由“好”至“了”的過程,仍然不能少。雖然抱怨“活得很累!”但生命中更無法承受的,是“輕”。“空”和“無”是一眼可以看破的,但無限的“空”,無限的“無”,卻撐不滿一個血肉的七尺之軀。佛只是用“空”與“無”的澄明,鑒照塵世的“實”與“有”;用對真諦的知覺,點醒沉淪中的迷惘。此所謂事為俗諦,理為真諦。一切有情須由俗諦證得真諦。苦集是俗諦(世間),滅道是真諦(出世間)。不周遍世間,怎能找到出世間的路?自相為俗諦,實相為真諦。不深入自相,怎么識得實相?解決人生之法,仍在人生之中。宋人詞云“夢為蝴蝶亦還鄉”,即使夢入“極樂”,夢回,仍在“娑婆”。
因此,如果人的本性是善良,又何妨去愛、去恨,領受自然之所予,而完滿自己的一生。癡情的寶玉不是早已參得“無可云證,是立足境”么;比他更癡的黛玉不是猶進一境,曰“無立足境,方是干凈”么。人生處處皆有大撒手處——此等已見得是撒手處,但未愛、未恨、未證得完滿具足的人生之前,何嘗撒得手呢?
浩如煙海的佛經,匯聚了古往今來無數的人生經驗、覺悟與智慧。究竟哪一種經義是真理?不妨說,你所信的,便是真理了!能夠解脫你的煩惱的,便是真理了!哪一時解脫了你的煩惱,哪一時它就成為真理了!佛可以不是宗教,而只是一種精神。它可以只是為娑婆世界的有情提供一個心的處所,給予他一種自我拯救的力量。在古老的語言符號中,加入屬于自己的人生體驗,便是覺悟與智慧了。
“從前有一位大官問馬祖道一禪師是否可以飲酒吃肉?馬祖說:飲酒吃肉是你的祿分,不飲酒吃肉是你的福氣!——這確實是生活里的偉大教化,我們在生活中的或悲或喜都是我們的祿分,只是我們應在這樣的祿分里創造一些福氣罷了。信仰,就是如實地接受生活本身,隨緣消舊業,任運著衣裳,如是如是。”(《清涼菩提》序)——這樣的體認,正是覺悟、正是智慧。林清玄是上根之人,修的是度一切眾生的菩薩乘。他說:“我的星星,或者說我的文學,希望給這熱鬧的人間帶來一絲清涼。”但聞法的眾生所以能感到說法者所在清涼,正因為這一絲風的吹拂來去,原不曾離開“堪忍”的熱鬧人間呀。
(《紫色菩提》、《清涼菩提》,林清玄著,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九月版,5.00元;3.6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