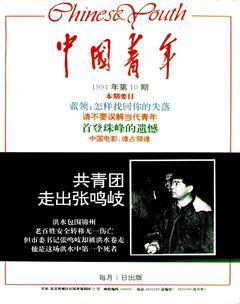指縫里相望
劉曉平
上高中時曾有個女孩子很讓我崇拜,她叫燕子,是班里的學習委員。盡管她出身不好,受著在當時看來最為殘酷的政治壓力,可她說起話來仍然是輕聲細語。她不像有些女孩,要么驕氣太重,要么旁若無人。她黑黑的頭發,亮亮的眼睛,紅撲撲的圓臉,讓人難忘。她有些抑郁孤獨的深情,樸素文靜的氣質給人很美的感覺。遠遠地偷看她高瘦的身材,使人覺得舒服。那時,我還不懂得談戀愛,只覺得她好,我愿意每天都看到她。
畢業后,她下放農村當知青,因一次渡船失事而淹死。知道消息的同學都去了,大家為她掩面而哭,哭得最厲害的是男同學。現在想來這大概就是我的初戀。后來我寫過一首小詩《指縫間望你》:你在指縫間望我/我在指縫間望你/老師在講臺上望我們……我想初戀留給人的美好印象一定就在這指縫間的相望之中。
成年之后,我體驗到了真正難舍難分的愛情。那一年,未婚妻去了南方。作為生命中摯愛的一部分,突然不在身邊了,彼此有種悵惘若失的感覺,有種苦不堪言孤苦伶仃的情緒。因此,特別珍惜每周特定的那次通話時間。每到那個時候,總是匆匆吃過飯,早早地守候在電話機旁,等待那驚心動聽的電話鈴聲。電話里,我們有說不完的愛戀,嘮叨不完的囑咐;既是親又是吻,又是哭,又是笑。除了吃飯,工資幾乎全用在打電話上了。
我們的年紀都不小了,相愛的過程已成歷史。因為害怕愛情的“墳墓”埋葬了愛情,我們沒有急于結婚。未婚妻無奈等待,也為了出去闖闖,才把自己放逐南方,置身于霓虹鬧市中承受無依無靠,無處訴說的等待,做一個漂泊不定,沒有港灣停靠的打工妹。有一次她終于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緒,在一聲急促的電話鈴響之后,我拿起了話筒,她沒有對我說話,卻是撕心地唱起來,我驚呆了,一邊全身心地顫抖,一邊聽——
千年等一回等一回呀,千年等一回,我無悔呀。是誰在耳邊說愛我永不變,只為這一句啊斷腸也無怨。
……
任何一首歌,沒有如此感人肺腑;任何一首歌,沒有如此動人心魄。唱著唱著,她在那邊哭;聽著聽著,我在這邊哭。哭聲變成了一聲呼喊:“來看我吧!”哭聲變成一聲呼喊:“我去看你!”
于是,我們走到了一起;于是,我們結了婚。婚后的耳鬢斯磨甜蜜而美滿。但生活到了彼此分毫相識那一刻,卻多了幾分祥和,少了一些激情,彼此互愛的舉動激不起對方那種強烈的心靈感應。生活中便有憂怨,便有拌嘴;因無厚實的家底,又要追些時尚,故而時常為缺一(衣)少十(食)遺憾;因想有番事業,又要為工作忙碌,故而為缺三(談)少五(我)而煩惱。我跟愛人談及這些時,她跟我一樣地無奈。
我說:“你再打電話給我唱一次歌吧!”她說:“你再千年等一回吧。”
指縫里羞澀地相望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