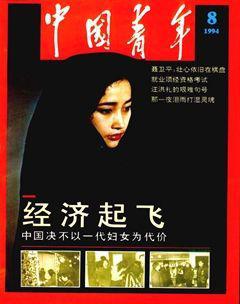橙紅色的太陽
梁粱
卞超凡青年詞作家,29歲,家住沈陽市東陵區祝家鎮卞麥玉村,迄今已在報刊上發表作品百余篇。現為中國音樂文學會會員,沈陽市音樂家協會會員。
初中三年級時,我傷了一只腳,在家養了很長時間的傷,就耽誤了這一年的考高中。我那時候一心要考大學,便決定第二年再考。但不幸的是我被分到了慢班。慢班都是一些被認為根本考不上大學的學生,學校抓得很松,各科老師也都不太在意。我父親找了學校領導,強烈要求將我調到快班,這其實是我的意思。但學校拒絕了。父親和校領導大吵了一架,回家后就令我退學,讓我到建筑隊做工。父親是個既精明又固執的農民,他知道進了慢班就考不了學,既然這樣,還不如省下復讀的費用,早點做工掙錢來得實惠。
一旦聽說自己將從此離開學校,立刻就有一種酸楚籠罩全身,我不知道該怎樣才能讓父親了解我彼時彼刻的心境。“就這么著9巴!”父親好像知道我將說些什么,便再次強調了一句,出去了。
我只能服從。
我進了鄉建筑隊。活很重,也很累。我那時個子挺高,但身板極瘦弱,搬石頭、搬磚、推車,對于我就成了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偏偏建筑隊還定了一個口號,叫做:早晨5點半,晚上看不見。這下我就更慘了,經常因為極度的疲憊和困倦,在工地上搖搖晃晃,好幾次都差點出事故。
有一天,隊長對我說:“孩子,你還是回家吧!要是真出個什么事,我們也不好向你父母交待。”我就回去了。父親一見我就罵了一句:“沒出息的東西。”我低頭無語。說真的,我實在是很慚愧。
就呆在家里,可總這么無所事事,心里也挺不是滋味。就找來原來的課本讀。讀著讀著,便感到不滿足,又出去找各式各樣的書刊。漸漸地,連自己都覺得“檔次”高了起來,因為除了名著,我已不再讀其他書了。
一次,我偶然看見一本歌曲雜志上登有征稿啟事,就很不在意地寫了一首歌詞寄去。誰知這竟成了決定我一生命運的大事。那首好像是抒寫青春美好的歌詞,雜志社并未采用,但卻將稿子轉給了著名詞作家、沈陽軍區政治部的鄔大為老師。大為老師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有激情、有才氣,還說目前我們國家的歌詞創作急需一大批新人,讓我堅持下去。當時接到這封信,我的激動可想而知。也就是從那天開始,我產生了要作一個詞作家的強烈愿望。我拼命地讀書,又不斷地將我的思想和情感變成一首首歌詞。一本稿紙寫完了,我就騎一輛嘎嘎直響的破自行車,往返70多公里趕到沈陽市內,將稿子呈給鄔大為老師審閱……慢慢地,村里人看我的目光就有點怪:挺大個小伙子不去賺錢,整天折騰寫什么歌詞,吃飽撐的。父親也大光其火:“你就寫這些沒用的東西吧!我看你到頭來能寫出什么日五大六。”
1984年,我創作的一首歌詞由著名作曲家生茂譜曲,發表在《天津歌聲》雜志上。以后的幾年時間里,我的名字開始頻繁地出現于各類報刊上。生活對我這個初中都未畢業的農村青年,綻開了她明媚的微笑。
1991年“八一”前夕,沈陽軍區戰士文工團的一位同志邀我為即將舉行的“八一”大型晚會寫一首《關東情》主題歌詞。這首歌作為晚會的壓軸節目,無疑將晚會推向了高潮,當時,整個會場掌聲雷動,氣氛極為火暴。我知道歌的成功,非我一人之力,但對于那首歌詞,我確實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寫成后也頗為自得。同年,我帶著這首《關東情》和另一首歌詞參加首屆全國工人歌曲征歌大賽,竟出我意外地雙獲金獎。1992年,第二屆全國工人歌曲征歌大賽又在南京拉開了帷幕。為參加這次大賽,我深入到鐵嶺清河區的場礦企業,走訪了許多生產第一線的工人和技術人員,并查閱了大量的有關清河的歷史資料,創作了《清河魂》《清河之夜》《清河的傳說》《請到遼北清河來》等4首歌詞,寄往大賽組委會,最后,在數萬份應征稿件中,分獲一個一等獎和三個三等獎。這幾首歌詞由著名作曲家龍飛、陶思耀、朱南溪作曲,唱遍了石頭城,并由江蘇省音像出版社灌成磁帶,公開發行……
1993年底,我意外地接到了山東某縣一位少女的來信,她在信中寫道:“今年我高考落榜,父母和親友都用冷漠的目光看著我,我覺著活得很壓抑,幾次都想尋短見,以免受人白眼。前幾天,我偶爾看到您發表在《農村青年》第7期的兩首歌詞《黃土地、黑土地》《所有的》,我受到了很大觸動,頓時打消了輕生的念頭。您說得對:生活終會露出陽光的七彩/日子畢竟長滿鴿子的期冀/那盼望的一個舊夢/終于在你的飄香中豐腴……我將重新發奮,去追尋屬于自己的日子,自己的夢。”
讀完這封信,我對自己的創作,突然有了一種全新的認識。我會好好地珍重我手中的這支筆,寫出更多更好的歌,以不負那些曾經幫助過我和需要我幫助的人們。
劉金偉1969年生。廣東健力寶集團發展部副經理。他說人常有一種負罪感。
1991年畢業前夕我可慘透了。北京的人才市場我幾乎跑遍了,都被客客氣氣地打發走,去大小部門求爺爺告奶奶,自我推銷,人事處長眼皮都沒抬幾下。頂著烈日奔波了兩個月,連坐公共汽車和買冰棍的錢都沒有,我真是絕望了。萬般無奈,我給遠在廣東的健力寶公司的總經理寫了封求職信,碰碰運氣吧。沒想公司人事部很快回信,信上只有兩個字:同意。你可以想像出我當時的心情。
前幾天有個好朋友問我:“假如有家公司出更高的薪水聘你,你跳槽不跳槽?”我說我肯定不動心。我走投無路的時候健力寶收留了我,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朋友驚訝地說,沒想到北大出來的學生觀念這般陳腐。我說,中國需要這種“陳腐觀念”。做人要講忠孝二字。公司不惜血本培養了你,一旦你羽翼豐滿,掌握了技術和客戶就另立山頭或另謀高就,這是不道德的。這樣做只能導致公司不敢培養你,處處提防你,你也不信任公司。在人人自危的氛圍中,還談什么企業的發展壯大?
熟悉我的人都說劉金偉變了。是的。我在北大校園里,也算個激進的現代派吧。那時一些名流舉辦各種講座,抨擊中國傳統文化,疾呼私有制,我是狂熱的聽眾之一。全盤西化我不太同意,但我認為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窒息了中國的發展,中國要現代化,就得把這些陳腐的東西掃除干凈。我買了一大堆儒家的書,打算研讀一番之后,給予批判。后來實在沒功夫讀,就把它們扔到一邊了。
步入社會之后,見的人和事多了,頭腦也復雜多了。有一回公司派我去外地出差,在火車站看到一個老人向旅客乞求,給他的孫兒一點吃的。旅客們的食品袋都是鼓鼓的,每人給一塊餅干就夠了,可是誰也不愿拿出一塊餅干。我看不下去,就把自己的面包給了老人。有個旅客對我說,不是我們不愿給,是被騙怕了。這件事對我刺激很大。人與人之間由于缺乏信任,連一點點同情心都沒有了!這些年來,我不知耳聞目睹了多少這樣令人心寒的事件:為了錢,親兄弟和好朋友反目為仇;為了錢,有的人不惜以身試法;為了錢,親兒子竟敢向母親開刀……在這一片物欲橫流的情勢下,我發現自己也變得俗不可耐,我就像一頭為幾根胡蘿卜拼命拉磨的毛驢。
面對紛亂的世界,該怎樣做到既無愧于人又無愧于己呢?工作一天后我躺在宿舍里冥思苦想。我的腦袋里總是空蕩蕩的。我隨意從床下取出“四書”“五經”,想排遣一下孤獨的空虛,誰知越讀越入迷。兩千多年前的先哲們的論述真是精辟,仿佛就是針對我們這些現代人的。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又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你聽講得多好,像金子一樣閃光。過去我們總認為儒家思想壓抑人,其實不然。孔夫子是主張人世的,是主張進取的,他從不反對他的弟子求高貴,只是強調不能做違背良心的事。
每天研讀“四書”“五經”,我感到自己活得很充實,說話辦事都有主心骨。我開始重新審視我經歷的人和事。比方說,重新評價我的父親。我的父親是個鞋匠。抗日戰爭時期他在重慶謀生,正趕上日本飛機轟炸。防空洞炸塌了,死了許多人。我父親冒死從防空洞里背出70多人。他把70多個垂死的人一字排開,把家里僅剩的一點米熬成米湯,一口一口喂傷員。誰也沒有命令他這樣干。解放后,我父親的許多徒弟都做了官,我家里雖然很窮困,但他從來不去走后門。70多歲了他還背著鞋箱四處飄流。過去我敬重父親,但認為他的一生很卑微,價值不大。現在我不這樣看了。我的父親不識幾個字,但他懂得推己及人,辦事講仁義。他的人格偉大。
他已長眠在武漢。每到清明節,我都坐飛機回去為他掃墓。我認為這對我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