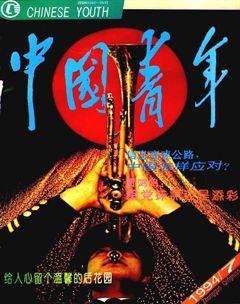從菜市口到天橋
李立
死刑是人類社會最古老的一種刑罰,并非中國獨創,然而中國古人尤重死刑,致使中國古代的死刑頗具特色。比如,中國古代的死刑非常講究執行方式,可謂形式多樣;且異常殘忍,往往延長行刑時間以增加犯人的痛苦。在現代人的觀念中,從消滅犯人生命的角度來說,采取何種方式處死,其結果都一樣。但在中國古人看來,選擇哪種方式處死卻干系重大;他們認為,同是處死,如方式不同,至少表明罪行輕重有別。在這種死刑觀的影響下,中國古代執行死刑的方式五花八門,常常由于犯罪主體以及被侵害客體的不同或罪行輕重的不同,行刑方式也大相徑庭。
中國古代法律所規定的死刑種類主要有:斬、絞、腰斬、梟首、棄市、車裂、磔、凌遲、焚等10余種。周代以后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也還有3種:斬、絞、凌遲。
斬即斬首,令犯人身首異處;絞即用吊、繩等勒死或用絞刑架絞死犯人。從罪犯的痛苦程度而言,斬刑最輕,“咔嚓”一刀,立即斃命。而絞在中國并非像西方那樣以懸吊方式致死,是名副其實地慢慢地將犯人絞勒致死:把犯人跪綁在行刑柱上,脖子上套有繩圈,由兩個行刑者各在一邊繩套上插入木棍,逐漸絞緊繩子勒死犯人。當然,用這種方法時犯人未必馬上斷氣,所以法律規定,如果實行3次還不能勒死犯人,可以改用其他方式處死。可想而知,被絞死的犯人會受到什么樣的痛苦。但在死刑等級中,斬卻重于絞。因為傳統觀念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得毀傷。”被斬者身首異處,而被絞死者可以保留全尸,所以身首異處的斬刑,比得以全尸的絞刑,更令人恐懼和感到屈辱。行刑者也往往利用人們的這種心理,在處斬前向犯人家屬索賄,一旦滿足要求,則行刑時可使被斬者頸雖斷而猶有一些皮肉與身體相連,算是身首沒有徹底分離。
凌遲,即“千刀萬剮”,屬于最殘酷的死刑之一。執行時要零刀碎割,令受刑者飽受痛苦慢慢死去。遼代始定凌遲為法定刑罰,沿用至清末。施刑方法無明文規定,據說有8刀、24刀、36刀、72刀、120刀之別。如果要割成百上千刀,則每次只能割一小塊,稱為“魚鱗碎割”。因此行刑時常用魚網包在犯人身上勒緊,使皮肉從網眼中鼓出,然后一刀刀碎割致死。史載,明代大宦官劉瑾謀反案發后,被凌遲處死,行刑達3357刀之多,時間長達3天,可見凌遲刑罰之酷烈。
古代西方死刑之殘酷,比古代中國毫不遜色。但是隨著近代文明的發展,死刑問題在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中成為爭論的中心,甚至出現了廢除死刑的主張。啟蒙主義思想和人道主義精神,敲響了古代死刑制度的喪鐘。
1789年10月10日,法國的吉約坦博士向國民議會提出議案,主張以后處刑的唯方式,應不管犯人身分和罪行性質的區別,尋求“眾人平等的,更有人情味的”處刑方法;要求采用“落斧”執行死刑。于是,法國出現了由著名外科醫生路易博士設計的機械斬首工具“斷頭臺”。
救死扶傷與尋求理想的處死方法,同樣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由醫生發明“斷頭臺”,反映了西方近代死刑觀念的本質變化。
后來,被稱為“巴黎先生”的行刑者,相繼把路易十六、丹東及羅伯斯庇爾等人送上了這個充滿“人情味”的“斷頭臺”。
近代文明精神要求死刑體現人道主義,即讓犯人能迅速而無痛苦地死去。這就使西方的科學家,不斷努力尋找適宜的處刑方法。
1851年,美國猶他州出現了一條獨一無二的法律:死囚可以從絞刑、槍斃、斬首中任選一種死法。但是,幾乎所有的死囚都選擇了槍斃。作為死刑的執行方式,槍斃最早始于18世紀末期的軍隊。原本是處決違反軍事刑法的士兵及間諜等,由于簡便易行較少痛苦,后來被普遍采用。
在電力得到廣泛應用之初,科學家為摸索快捷簡便的行刑方法已經想到了電。19世紀末葉,在愛迪生剛剛發明了電燈給人類帶來光明后不久,紐約州的立奧本監獄就奉獻給了人類第一把電椅。1890年8月6日上午,殺人犯威廉·凱姆勒有幸坐上了這把電椅。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施行電椅死刑。該州政府認為:絞架已經過時,不能適應“開放與文明”的要求;而用電椅處死犯人又干凈又快捷,能夠減少犯人的痛苦。不過也有例外的情況,據載,有的犯人被電擊后,七竅生煙,卻不能馬上死去,異常痛苦。但大多數犯人是立即斃命。
西方的死刑觀念和處刑方法,隨著西風東漸,逐漸被介紹到中國。近代中國人最早接觸、了解西方死刑制度是在19世紀40年代。
1847年,福建人林鉞赴美教習中文。回國后,林鉞將自己在美國的所見所聞寫成《西海紀游草》一書。其中記載,美國總統安德魯·杰克遜上任后實行司法改革,措施之一即在法律上廢除死刑,代之以贖刑。這是目前史料中有關國人最早接觸西方死刑觀念和死刑制度的記載。
在19世紀中期的一次英國水手導致中國船民死亡的案件中,英方認為是過失殺人,應當區別于故意殺人,不應處死刑;中方認為殺人必須償命,不清楚“過失殺人”這個概念。這種分歧導致了外交沖突。顯然,量刑和處罰的不同,包含有侵略反侵略引起的感情沖突和民族對立情緒。但也確實反映了近代文明與傳統文明,在刑罰觀念和制度方面的沖突。
古代中國非常重視道德判斷,為了維護公認的傳統道德,即便故意殺人,也往往得到輿論和法律的寬宥。“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在現代是對正義感的形象稱贊,但在古代卻是鼓勵人們為了維護正義可以動刀動槍,殺人不償命。一般而言,殺人償命是在沒有重要的道德區別情況下的懲罰。現代的共誅之共討之一類的憤慨,就是這種傳統道德判斷的現代遺存。
道德判斷對死刑制度的最重要影響,從人們對斬首與絞殺的不同態度上已可見一斑,所以直到20世紀初期,雖然西式槍炮早已在中國落戶,中國的兵工廠已經可以裝備新式軍隊,但執行死刑的方式仍然不是槍斃而是砍頭。
在中國實行槍決的首先是外國侵略軍。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失敗以后,八國聯軍瘋狂報復,曾經大批槍決被抓的義和團民眾。但不久之后,侵略軍發覺槍斃不如砍頭對中國民眾更有威懾力和屈辱感,于是把對義和團民眾的處決一律改為中國式的斬首示眾。這是西方近代文明到達中國以后,自愿迎合中國傳統文明的少數事例之一。由此可見,西方侵略者借口中國刑罰野蠻、殘酷,強行治外法權,實有虛偽的一面。
不過這種借口卻使清王朝的一些開明官員,得以向清廷提出改革傳統刑罰制度的要求。
20世紀初期,經歷了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略之后,清王朝迫于內憂外患的壓力,不得不實行新政改革,死刑觀念和死刑制度由此開始發生變化。
1905年,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奏請皇帝刪除《大清律例》中的重刑,首當其沖的是凌遲等刑罰。他們認為,西方之所以“政治日臻美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刑法由重改輕;主張學習西方刑法的輕刑主義,改革清朝刑律。尤其是在死刑執行方法上,沈家本力主或斬、或絞、或槍決,只用一種,而不應并用兩種或兩種以上,更不應有等差、分輕重。因為刑法是國家懲罰罪犯的工具,不是私人報復的手段;如果從手段分別輕重,有損國家法制的統一。沈家本的這些理論顯然是受近代西方人道主義及法制思想的影響,反對野蠻與落后的封建酷刑,具有鮮明的進步性。
光緒皇帝贊同他們的主張,命令廢除凌遲等刑罰,但保留了斬、絞二種死刑,此舉遭到來自國內外不同方面的非議和攻擊。清朝修律顧問日本法學家岡田朝太郎博士認為:“各國之中廢除死刑者多矣,即不廢死刑者,亦皆采取一種之執行方法。今中國欲改良刑法,而于死刑猶認斬絞二種,以抗世界之大勢……外人讀此律者,必以為依然野蠻未開之法。”可見中國傳統的“斬重絞輕”的死刑觀念,仍不能為近代外國人所接受。而國內的守舊者則攻擊新刑罰“刑之過輕,對反逆惡逆之犯,不足以昭懲創。”
1910年5月15日,清政府頒布《大清現行刑律》,規定死刑分為絞斬兩種。1911年1月25日,又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仿照西方近代刑法體例、原則制定的刑法典《大清新刑律》,其正文規定死刑僅用絞刑一種,但在后附《暫行章程》第一條卻規定“侵犯皇室罪”“‘內亂罪”等仍用“斬”。可見身首異處的道德考慮,仍然是影響死刑觀念和制度的重要因素。
根本廢除斬刑,是在民國建立以后。1914年11月27日,北京政府頒行《懲治盜匪法》,其第6條規定:死刑得用槍斃。從此,斬刑從法律上廢除了,槍斃成為中國近代死刑的主要執行方法。隨即,北京的刑場也從人口稠密的菜市口遷到當時空曠的天橋南大道西面的先農壇二道門外。
菜市口和天橋同在北京城南,相距不遠,但是刑場的遷移卻反映了死刑觀念和制度的重要變化。法律認可的死刑是痛苦較少的槍決,槍決代替斬首,說明社會更加重視的是死刑對犯人本身的懲罰意義,而不是對犯人的屈辱和對犯人家屬的懲罰意義,同時也反映了人道主義精神在中國的進步。此后很長時間,砍頭和梟首示眾仍然是常見的處死方式,甚至有更殘酷的活埋、棒殺,等等。但那畢竟只是缺乏人性的泄憤方式,不是合法的死刑,人們可能敢怒不敢言,卻絕不會認同殘酷的刑罰,反而會進一步增加追求人道主義精神的愿望。可見死刑的觀念和行刑方式的進步,是最能反映人道主義精神普及程度的標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