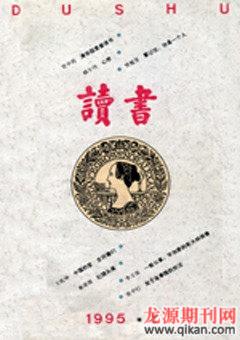前衛概念傷病員
尹吉男
無聊感勿須追求就能獲得,而真實的病態又無法掩飾。生活中無動機的謀殺確實存在,既讓饒舌的解釋者為難,又造成了他們可以任意胡說的良機,千載難逢。西方的那套“前衛”概念雖然已被說濫,不過,既然中國有志向的藝術家主要目的是要表演給西方看,似乎就得利用人家的現行概念。在中國,“現代主義”一度是“前衛”的代名詞,這個概念是一只尾隨著中國藝術家的老虎,盡管它從不吃人,且又高貴,但總令中國藝術家兩腿打戰地死命前奔。客觀地說,的確產生過許多奇絕幻象和氛圍。但中國藝術家從沒認真推究過,這個“老虎”并不是真的活生生從西方跑過來的(比如文化的“八國聯軍”進駐北京),而是中國的理論家們在讀洋書之余用書香氣吹起來的。由于底氣不足,忽實忽虛,“老虎”的晃動更顯得威勇沉雄。
中國藝術家差不多已經習慣于上述這個前提。雖說奔跑是共性,但個性還是可以通過奔跑姿勢和節律來區別。這個異時異地的虛妄概念(最具體地指稱“前衛藝術”概念的只有歐美主流藝術作品,而這些藝術作品與我們的生存狀態缺乏聯系)成為一種狂奔的心理依據,以致于許多藝術家仿佛在印刷品的油墨里氣喘噓噓地奔跑,在理論書枯燥生澀的字句中奔跑,而個人最切身的實際生活則顯得微不足道。這類奔跑自然滿足了固有的前衛概念。由此證明了理論的有效性。事情往往不會這么樂觀。中國藝術從此陷入兩難境地,就像中國廚師按法國菜譜做菜,做地道了有人就罵你抄襲摹仿,做得別致就有人指斥你不合“標準”。批評家總有話說,而且不失時機。
當熱情洋溢的人們帶著變相的政治預期來圍觀這類奔跑時,中國藝術家很起勁。他們可以把每一雙好奇的眼睛都看成是行家的鼓勵,并把眼睛的數字統計到自尊自愛的程度,其實許多觀眾很樸素,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他們認為圍觀本身就是表態,是否懂藝術并不重要,開放和寬容是個人具有超前意識的旁證。如果身為領導就等于擁有“開明”這個身份卡。可是,一旦圍觀者因故撤離現場,那種單調乏味的奔跑頓時成為證人缺席的默默奉獻和無法被誤讀盡情升華的苦役。更進一步說,當理論家因興奮點轉移而失去吹氣的熱情和責任時,繼續奔跑下去的前衛藝術家只能靠自覺自愿、靠毅力和信念。盡管如此,腳步聲益發顯得空洞、無聊、病態、傷殘。他們在一種與生存現實無關的文化假相里跑得昏天黑地,落下了一身毛病。每每到了這個時候,一部分前衛藝術家紛紛有了各自的說法,諸如追求終極精神,提倡純藝術性,反對功利主義,一下子都變成了堅定不移的苦行僧。“墨索里尼,總是有理。”他們用一種把奔跑姿勢類型化經典化的方法來代替更具文化針對性的新的創造;他們通過一再的重復來加深人們對他們的深刻印象;他們利用自己的傷病狀態作為藝術上的鮮明標志。實質是為了個人生計在美化徹頭徹尾的保守和頹廢。但這僅僅“演義”了一個回合。
實際上事情并沒有完結。當“后現代主義”這個“老虎”作為“前衛”精神又被吹起來的時候,它還會引出雜沓的碎步和氣喘噓噓,只不過場面遠不如從前壯觀,圍觀者驟減。奔跑者主動暗扣吹氣者的設計,于是這樣一來,奔跑者的落荒而逃的腳步聲似乎雄辯地證明了“老虎”的無處不在。這確實給西方學者省下了一口仙氣,就像牛頓直接幫上帝免去了“第一次推動”的當眾一試。不要小看“后現代主義”這個“老虎”的出現,它確使一部分中國藝術家找到了新的出路,可以公開打出“前衛奔小康”這面旗幟。明星式的商業包裝、操作、牟利,藝術家從此不必再做苦行僧,也不再擔心后現代學者們是否玩膩了這只“老虎”。只要有“前衛奔小康”這面旗幟迎風招展就足夠了。可是,不會人人都能奔成小康,終究還是有一大批藝術家仍然很生硬地跑下去,又會造就一批前衛概念傷病員。
我突然萌發這樣一個感想:對于一個立志要在本世紀內(其實只剩下五年)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國家,短短幾年,“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這兩只“老虎”都先后跑了過去,你能說這個國家不“前衛”嗎!至少它在文化上的“前衛速度”是超一流的。有個兒歌唱道:“兩只老虎跑得快,一個沒有腦袋,一個沒有尾巴,真奇怪!”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三日于北京校尉胡同五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