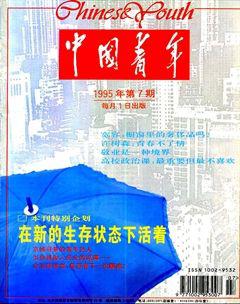橙紅色的太陽
梁粱
盧曉月,女,1970年生于北京;1992年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大學(xué)教育系學(xué)前教育專業(yè),同年分配到中國聾兒康復(fù)研究中心,從事聾兒教育工作至今。
殷會利,男,32歲,北京市“五四獎?wù)隆鲍@得者。現(xiàn)為中央民族學(xué)院美術(shù)系講師。
盧曉月
我喜歡孩子,喜歡和孩子在一起。孩子們清澈的目光和真純的語言能讓人的心靈瞬間得到凈化而變得美好。所以,考入北師大算是遂了我的心愿。讀書時(shí)我就常會想像著某一天我成為一名幼兒教師、和一群天使般的孩子在一起的情景。這么想著的時(shí)候,我常常情不自禁地笑出聲來。
分配到聾兒康復(fù)中心倒是我沒有料到的。我無法想像,當(dāng)我面對一群耳不能聽、口不能言的孩子,我怎樣才能與他們交流,又該怎樣去教育他們。
但我還是上任去了,雖然心里忐忑著。當(dāng)我走進(jìn)教室,看到那些因?yàn)槎@而比正常孩子顯得木訥、神情僵硬的學(xué)生時(shí),我的心里涌起一絲嘆息,一份感慨。他們本來也應(yīng)該和別的孩子一樣快樂、活潑、無憂無慮的呀!我曾經(jīng)看過一份材料,是1987年所作的殘疾人抽樣調(diào)查。調(diào)查結(jié)果表明,我國當(dāng)時(shí)有0~14歲聾兒171萬,每年還在以2~4萬的速度增長。這是一個(gè)多么龐大的聾兒群體1如果我們能不失時(shí)機(jī)地發(fā)揮他們的殘余聽力,對他們進(jìn)行聽力和語言訓(xùn)練,使他們得到有效的聽力補(bǔ)償,那么,他們必將可以得到最終的康復(fù),從而回歸主流社會,回到正常的生活中來。這該是一項(xiàng)多么有意義的工作啊!那一刻,我感到一股神圣的責(zé)任感在我心里慢慢滋長、升華。
與教正常孩子相比,教育聾兒要困難得多。光“點(diǎn)名答到”這一關(guān)就花了我整整一個(gè)月的時(shí)間。也有忍不住想發(fā)脾氣的時(shí)候,可一想到他們生理上的暫時(shí)缺陷,再大的氣也消了。最后,終于可以不讓他們看我的口形就能通過“點(diǎn)名”關(guān)了。不讓看口形,是怕孩子們據(jù)此猜測我在點(diǎn)誰的名,更是為了誘導(dǎo)和發(fā)揮他們剩余的最后那點(diǎn)聽力。這對他們今后的學(xué)習(xí)是大有益處的。
聾兒因?yàn)槿鄙倭艘粋€(gè)獲取信息的重要途徑,較之正常孩子會顯得更為執(zhí)拗。我班上有個(gè)叫張大偉的,性格就怪怪的,好像總處于一種極度的恐懼之中。每次我走近他,他的眼神里都有一股明確無誤的排斥和敵意。我不知道他為什么這么急于逃避我,不留任何余地地拒絕我的接近。后來我了解到他的父母都在外地工作,家中常年只有一個(gè)老人。我理解了這個(gè)孩子的心理狀態(tài)和特殊的情感需求。于是,在課堂上我對他的行為總是表現(xiàn)出最真切的關(guān)注,并毫不氣餒地一次次走近他,用各種方式與他交流。漸漸地,他眼神里那股強(qiáng)烈的拒絕意味淡化了;他最終接納了我。而此后他表現(xiàn)出的想與我交流、與我友好的真誠和熱切,令我感動。他母親回北京見到我時(shí),拉著我的手一個(gè)勁哭。
現(xiàn)在,張大偉已調(diào)入正常幼兒園上學(xué)。每次想到他,我都在心里深深地為他祝福,為他明天的美好祝福。
首先必須付出,然后才能贏得一個(gè)聾兒的心。這是我兩年多工作的體會和總結(jié)。吳桐,一個(gè)來自江西的4歲聾兒。他父親在北京找了個(gè)工作,因遠(yuǎn)離康復(fù)中心無法接送。我承擔(dān)起了吳桐的一切。白天上完課,我就將他帶回家,吃、睡都在一起。那段時(shí)間,我是在緊張和極度的疲憊中度過的。媽媽看我實(shí)在累得不行,便常常幫著我照看吳桐。以前,由于父母的遷就,吳桐固執(zhí)而任性,同他講道理是件很困難的事。我?guī)粋€(gè)月,他變得懂事多了。而且,他已將我視作最親近的人,每天都須臾不離地跟著我。甚至,見了他父親,也遠(yuǎn)沒有對我親熱……
我想說說那些孩子的父母。他們都是些最了不起、最具愛心的父母。他們中有很多是從偏遠(yuǎn)省份千里迢迢趕來北京,將孩子送到康復(fù)中心。他們都曾擁有很好的工作,但為了孩子,他們毫不猶豫地放棄了。在北京,他們找臨時(shí)工做,租住最簡陋的民房,冬天沒有暖氣,夏天蚊叮蟲咬……我常想,我們這些當(dāng)老師的如果不用心教好他們的孩子,在他們面前,我們都將罪無可恕!
所以,雖然我每月的工資、獎金加起來也超不過400元,干的是最操心勞神的工作;別人下班了,自己還得經(jīng)常留下來給個(gè)別孩子加小灶——但我還是要說,我喜歡我的工作,發(fā)自內(nèi)心地喜歡我教的這些孩子。我覺得我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價(jià)值的。
是的。我今天用愛心澆灌的這些小苗苗,總有一天會長成一棵棵參天大樹的。我堅(jiān)信這一點(diǎn)。
殷會利
1983年我考入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裝潢系。在那之前,我在家鄉(xiāng)鶴崗嶺北礦區(qū)算是個(gè)小有名氣的畫師。我曾經(jīng)打著格子為人家畫巨幅毛主席像,還常常爬上腳手架,畫各種會議的宣傳和招貼。時(shí)間長了,就有人“慕名”邀我去作畫。當(dāng)時(shí)的那種自得和興奮,是難與外人道的。畢竟,對于一個(gè)十八九歲的年輕人來說,能擁有社會的承認(rèn)和矚目,便足可令他傲視闊步、睥睨同類了。當(dāng)然,今天想來,是不免要惶然的。
但如果我就那樣安于現(xiàn)狀,陶醉于那份微不足道的成就感,或許直到今天我還只是邊陲小城里一個(gè)技術(shù)嫻熟的畫匠,藝術(shù)上永遠(yuǎn)也走不出沾沾自喜、墨守成規(guī)的窠臼。我的機(jī)緣來自那次心血來潮般的沖動:想去北京,去看看故宮、琉璃廠,看看中國美術(shù)館里每天都有的中國最高層次的畫展——那是無數(shù)畫界新人都急欲一瞻其風(fēng)采的藝術(shù)圣殿啊!
于是,我參加了高考,并如愿以償。登上赴京的列車時(shí),我滿懷著朝圣者的心情。
在北京,除了經(jīng)常性地光顧美術(shù)館之外,我成了班上最用功的學(xué)生。外出隨吳冠中教授寫生,大師常常把最高分獎給我。似乎順理成章地,我成了班上唯一在院內(nèi)舉辦個(gè)人畫展的學(xué)生。
畢業(yè)后,我被分配到教育出版社美編室,先后任編輯、編輯室副主任。1990年底,我離開出版社,到民族學(xué)院任教。我教過素描、色彩、風(fēng)景、工業(yè)設(shè)計(jì)等專業(yè)課,還兼任班主任。因?yàn)楣ぷ髑趭^、努力,我曾被學(xué)校評為優(yōu)秀青年教師。但使我的名字走向社會、為人們所熟知,卻是由于一方方小小的郵票。
1988年,中國郵票總公司就《麋鹿》郵票的發(fā)行公開向社會征稿。我參加了,卻名落孫山。現(xiàn)在想來,那完全是由于我對郵票認(rèn)識上的淺陋和偏頗所致。我覺得郵票設(shè)計(jì)純粹是一門雕蟲小技,難登大雅之堂的。后來,再比較自己的設(shè)計(jì)稿與中選的作品,我立刻為其間的差異所震動。我終于意識到,要畫好一枚郵票,就必須調(diào)動我平生所掌握的所有繪畫技巧。或許,僅靠這些還遠(yuǎn)遠(yuǎn)不夠。
我開始將郵票作為一門真正的藝術(shù)去對待,開始從設(shè)計(jì)思想、構(gòu)圖、色彩等不同角度去研讀、揣摩。1990年,我設(shè)計(jì)的《野羊》一舉中的。1992年,《鸛》《昆蟲》《奧運(yùn)系列》三套郵票也順利發(fā)行。這一年,全國共發(fā)行18套郵票,而我一人獨(dú)占三套。我為此也付出了許多。僅為《奧運(yùn)系列》一套,我不僅費(fèi)盡心機(jī),還差點(diǎn)跑細(xì)了腿。我到圖書館查閱資料;去體育學(xué)院觀看運(yùn)動員訓(xùn)練,希望可以發(fā)現(xiàn)我應(yīng)在畫稿中展現(xiàn)出的精彩瞬間。我姐姐殷秀梅是位歌唱演員,和許多運(yùn)動員都有聯(lián)系,她書房里有不少體育畫報(bào),我也統(tǒng)統(tǒng)抱了回去,當(dāng)然有用。《奧運(yùn)系列》里那枚體操票的設(shè)計(jì),就是從體操王子李寧送給我姐姐的一本畫冊里獲得的靈感。那段時(shí)間,北京正在搞“卓別林電影周”。我平素最喜卓別林的片子,特意讓人搞了一套。但直到電影周結(jié)束,那套票還完整地揣在我口袋里……
1993年,我接受了《野駱駝》的設(shè)計(jì)任務(wù)。在大學(xué)讀書時(shí),我曾利用暑假去過一趟陜北。在榆林地區(qū),我第一次看‘到了沙漠,那茫茫大漠,綿延起伏,一望無際,予人無限遐思。但激動過后,我忽然覺得眼前還缺少點(diǎn)什么。后來才發(fā)現(xiàn),這種感覺是因?yàn)闆]有看見駱駝,哪怕是遠(yuǎn)遠(yuǎn)的,沙漠與天際交接處有幾點(diǎn)駱駝的影子也好。在我的印象里,沙漠總是和駱駝連在一起的。現(xiàn)在,當(dāng)我著手設(shè)計(jì)《野駱駝》的形式和總體風(fēng)格時(shí),我的直覺引導(dǎo)我向有關(guān)沙漠的范疇去思考,如沙漠的色彩、沙漠流動的節(jié)奏感和沙漠作為背景與主體野駱駝的關(guān)系。《野駱駝》的構(gòu)思可以說自始至終都是圍繞這一基點(diǎn)來發(fā)展和完善的……在這一年舉辦的最佳郵票評選中,《野駱駝》獲專家獎。在中國,我是迄今為止第二個(gè)獲得此項(xiàng)殊榮的郵票設(shè)計(jì)者。
常有習(xí)畫多年尚未成功的朋友向我訴說他們的煩惱,并問我在郵票設(shè)計(jì)上何以會如此一帆風(fēng)順。我舉了一個(gè)例子給他們聽。我曾畫過一套2枚《張聞天》紀(jì)念郵票,從時(shí)間、空間上看,我都與張聞天相距甚遠(yuǎn),僅憑幾張存留下來的照片,最多也就湊合個(gè)形似。我沒有對著照片貿(mào)然下筆,而是翻閱了大量史料;張聞天夫人寫的回憶錄我至少看了5遍。每讀一遍我都會深深地感動一次。漸漸地,我明了了他的經(jīng)歷,走進(jìn)了他的思想。拿起筆來,他的形容、情態(tài)歷歷如在眼前。在2枚小小的郵票里深刻地反映出張聞天同志革命、戰(zhàn)斗的一生,在我便不再成為難事……常說“功夫在詩外”,對于作畫,也是一樣的道理。希望我的這點(diǎn)小小的感受對朋友們能夠有所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