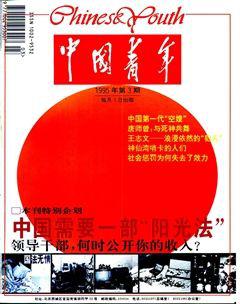希望工程讓我生命飛揚
一個不安分的靈魂
一個挑戰的性格
和一個名揚海內外的崇高事業
希望工程干了5年了,這是第一篇關于“我與希望工程”的文章。因為《中國青年》雜志社的記者執意要我寫一篇,不得不遵命而作。
有人說我在團中央時就不安分,不像個“組織部長”,搞“希望工程”更出人意料,這可能是溫州人的性格使然。
溫州人性格中最本質的特征是務實和對于新事物的勇于探求,據說這些源于南宋時期浙江的“永嘉學派”。我是否受到此熏陶,不得而知。
我是1978年籌備共青團十大時調到團中央工作的,在組織部一干就是10年。從一般干部做起,每兩年一個臺階,直做到組織部長。自我評價,那段時期的工作是兢兢業業的。所謂“不安分”是因為我總探求些新的、別人沒做過的東西。譬如,倡導并推行農村團干部招聘制;將競爭機制引入團干部差額選舉;搞起了競選試驗;主張企業團干部的“非職業化”;以及有關團的其他方面改革的實踐。許多在現在看來已習以為常的事,在當時并不被多數人接受。記得一次我在北京市團校講課,指出了一個令人擔憂的現實,“共青團聚集優秀人才的機制在弱化,許多團干部不過是二流或三流的人才。”臺下立即響起一片抗議聲:我們就是一流人才!我只好回答他們:“如果是一流人才,為什么我作為團中央組織部部長,接到的卻是到處告急團干部安置困難的報告。現在正是用人之秋,一流人才何以安置困難?”
有人批評我走得太快、偏激。我笑答道:這是我自覺的角色選擇。結果,麻煩還是來了。在團的十三大上,我作為團中央委員的候選人,險些落選。好在,由我主筆起草的《關于共青團體制改革的基本設想》被大會順利通過。
這時候,我感覺自己已經完成在共青團中央機關崗位的使命,應該做點別的什么了。
我不習慣欣賞沉浸在已有的成功中,對否定舊的東西不感到可惜,常有人對我從團中央組織部部長到青基會秘書長的轉變感興趣
前不久我接受北京電視臺記者采訪,記者向我提問:“你為什么不繼續做官,而來辦‘希望工程?”我回答:“做官也好,做公益事業也好,只要為老百姓做事,都是有價值的。我這個人走仕途不得要領。一個做官的徐永光和一個做‘希望工程的徐永光,我以為后者更適合于我。”
我把生命中最寶貴的一段獻給“希望工程”,也許是命運的呼喚。我剛來到人世父親就離我而去。母親靠給人衲襪底養育我們5個孩子,小時候我們經常餓著肚子讀書。現在兄弟姐妹都成人了,哥哥姐姐都是教授級的教師。我想要不是讀書,要不是國家給的每學期三五元的助學金,哪有我們的今天。
還有1986年,我下基層到廣西蹲點兩個月,在金秀瑤族自治縣的金秀鄉,了解到一個4000多人的村子,解放以來沒出過一名初中生。在廣西三江縣富祿鄉的16個行政村中有8個村找不到一個初中畢業生。金秀鄉、富祿鄉,都是好聽、誘人的地名,然而卻是公路不通、照明無電的窮鄉僻壤;“金秀”“富祿”,這地名中寄托了幾代人的期望,然而卻是金秀鄉中無秀才,富祿鄉里難富祿。
在廣西大瑤山中度過的兩個月真令我難忘,在以后的生活中想起那些失學兒童的身影,我胸口就仿佛被那沉重的大瑤山壓得喘不過氣來。
投身“希望工程”這一崇高的事業,令人生命飛揚,創造力如涌泉奔突。如果說這幾年工作中有什么得意之作,似乎也可舉出幾件
首先當推“希望工程”四個字的命名。當初,大家給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兒童的事業取了許多名字:“春雨計劃”“育人計劃”“桃李計劃”,都覺得不盡如人意。宣傳提綱的清樣出來了,還是沒有一個中意的名字。一天夜里,在輾轉反側中,腦子里突然閃現“希望”兩字。啊!“希望工程”,多么令人神往的字眼。那時怎么也想不到,這四個字竟然成了當今的一種社會時尚。
“希望工程”的發展中,不是固守一種工作模式,而是在不斷調整和否定中達到新的突破。
“希望工程”創辦之初,我們以信函方式集資。幾十萬封請求募捐信,都是靠手抄漿貼發出的,真是勞民傷財,費時費力。如何才能提高效率呢?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一天下半夜2點多,我腦子里突然蹦出個念頭,為什么不在報刊上做公益廣告?假如在《人民日報》上做一個廣告,不就等于我們給幾百萬、甚至上千萬讀者發出信函了嗎?我興奮得把妻子叫醒,說我想了個好主意,這個主意價值200萬。我妻子睡眼惺松地對我嘟嚷:“你有病。”第二天,我把這個主意告訴了大家,一些同志懷疑,“黨報怎么會登這種廣告?”我說,“哪個文件也沒規定不能登這種廣告啊?在中國有些事并沒有規定能干或不能干,而是要我們去試去闖。”接著我自己撰寫了廣告詞:
“……陜西省鎮安縣貧困地區有一名12歲的女孩卿遠香,她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去年父親病逝,母親帶著她和不足4歲的妹妹過著艱難的生活。她失學了,白天喂豬、砍柴,晚上拿出珍藏的課本自學。期末考試到了,她匆匆干完活,跑到學校,在剩下的半堂課里認真地答完考卷。在考卷未尾,她含淚寫下了四個字:‘我想上學!……”
寫完后,我派人送到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很快廣告刊登出來。我們的廣告打動了無數善良人的心,許多地方的報紙都紛紛轉摘這份廣告。這大概在中國廣告業恢復以后也是僅見的。
廣告刊出后,我們收到的捐款額直線上升。
辦“希望工程”中的又一得意之作,是定向資助為導向的籌資機制的建立,使“希望工程”真正成為全民參與的事業。在起初的兩年多里,“希望工程”捐款由我們統一分配,對此,我們在報紙上正式聲明:“鑒于貧困山區通訊不便,不接受一對一的捐款救助方式,但我們保證把捐款全部用于救助失學兒童。”這種從我們自己管理能力出發而設置的救助方式,使捐款使用情況無法得到直接反饋,影響了群眾捐款熱情。一天,一封群眾來信放到了我的案頭。來信說:“作為一名熱情支持‘希望工程的人,僅僅捐款總覺得不夠,希望能與受助孩子保持聯系,看到孩子的成長,使自己有一種榮譽感和成就感。”捐款人情真意切的話語使我感動和茅塞頓開。雖然當時我們的聲明剛剛見報,我還是通知救助管理部門重新審視我們的觀點,拿出一對一救助的新方案。經過一段緊張的調研準備工作,1992年4月15日,我們推出“希望工程百萬愛心行動”,號召結對救助失學兒童。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鄧小平、江澤民、李鵬同志為“希望工程”的題詞。這一年救助失學兒童的規模也由前一年的4萬猛增至32萬。
但是,成功的背后又潛藏著隱患。由于結對捐款者的大量增加,使我們的工作量也大增。有人統計過,從接受捐款到捐受雙方建立聯系,完成一名失學兒童的救助,需要經過20多道工作程序。這意味著1992年我們的救助工作需完成七百萬道工作程序。在我們最忙的時候,當時與我們為鄰的警衛國家主席楊尚昆的部隊指戰員都來幫忙了。即使這樣還是忙不過來。于是有人擔心:“希望工程”的容量是否已到了極限?這時,我想:人腦不行,為什么就不能用電腦呢?這個提議立即付諸實施。由美國AT&T;公司捐贈設備,由航天部二院研制開發的“希望工程計算機管理信息系統”于1994年投入運行,并在全國大部分省區實現聯網。1994年的“希望工程1(家)十1助學行動”在該系統的支持下,救助規模在過去54萬基礎上突破了百萬大關。
共青團,是我人生的轉折點,她使我認識了社會和自己,使我走向更廣闊的人生
我從1978年進團中央機關,至1988年脫離團中央機關工作來作青基金會事業,其間作了10年的專職團干部。是10多年的團中央機關的生活,使我有機會了解農村、學校、工廠等廣泛的社會,這對于我今后的生活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財富;是10多年的團中央機關的生活培養了我一種綜合、理性思維的能力,使我能從一些零碎、具體的現象中找到理性的結論;長期從事組織工作的經歷,使我養成了做事規范、注意協調和善于用人之長的習慣。而這些正是我今天能做好“希望工程”的人生經驗。而“希望工程”這一令人神馳的事業,又使我追求到了生命的至高幸福,走向更廣闊的人生。
不久前,我同1978年同時走進團中央機關的幾個老朋友在福州不期而遇,他們是中共中央統戰部某局局長覃志剛、中國青年旅行社社長張希欽、福建某學院教授黃章煌。老朋友見面,分外欣喜,舉杯之間,感慨系之。那天,我說了這樣一段話:“人生的道路很寬,我們四人都有點本事。但不必只在仕途一條道上擠。做官的把官做好做大;經商的把生意做好做大;教書的把學問做好做大;那就各得其所。而我,能把‘希望工程做好做大,也此生足矣!”這或許可以作為此文的注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