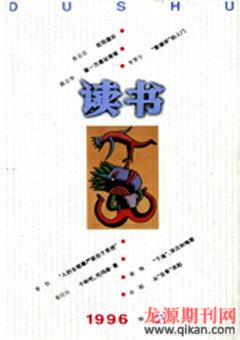“景風(fēng)東扇”第一葉
李天綱
中國統(tǒng)治階級承認(rèn)的宗教素來只為“三教”,儒道佛有時(shí)并存,有時(shí)相爭。然而,基督教綿延千余年,但在士大夫知識分子中一直未予應(yīng)有的關(guān)注。歷代儒家在發(fā)展自己思想的同時(shí)排斥過許多有價(jià)值的學(xué)說,基督教神學(xué)是其一,這是中西思想文化史上的遺憾。
“景風(fēng)東扇”,現(xiàn)在全世界都公認(rèn),唐代景教就是最早傳入中國的基督教。但是清代大多數(shù)學(xué)者不承認(rèn)。明朝天啟三年(一六二三),在西安附近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五年,當(dāng)?shù)亟掏綇埜輰⒈耐仄闹两希?jīng)耶穌會(huì)士陽瑪諾(Emmanuel Diaz)與被稱為“中國基督教三柱石”的李之藻、徐光啟、楊廷筠考釋,判定景教即為基督教聶斯脫利教派(Nestoria)。《景教碑》的額端有明顯的十字架,單單憑這符號就可以斷為是基督教的遺物。然而,紀(jì)昀在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時(shí),還是不肯承認(rèn)是基督教,他把基督教與波斯襖教混為一談。他說:“西洋人即所謂波斯,天主即所謂襖教”。明末清初的大學(xué)者因?yàn)椤毒敖瘫返陌l(fā)現(xiàn),對基督教史產(chǎn)生了興趣。錢謙益《景教考》說:“(景教)非果有異于摩尼襖神也”。錢大聽對別人告知的景教和天主教同奉耶穌的說法,表示存疑,“未審然否”。他憑很少的證據(jù)考證耶穌生于“隋開皇之世”(公元六世紀(jì)末)。其它學(xué)者,如杭世駿,更誤指景教為回回教(伊斯蘭教)。清初的學(xué)者都是考據(jù)大家,很博學(xué),但他們在涉及基督教的時(shí)候,都犯了錯(cuò)誤。
本世紀(jì)中研究基督教及其神學(xué)的不乏其人。如卓有成就的史學(xué)家陳垣、向達(dá)、馮承鈞、王重民、方豪都在此領(lǐng)域作了大量基礎(chǔ)研究。現(xiàn)在我們對中國古代基督教的狀況有所了解,仍然是與他們的工作分不開的。但是拿現(xiàn)在學(xué)者們喜歡說的話:基督教是“邊緣文化”,還沒有像佛教那樣進(jìn)入“文化核心”,成為中國文化水乳交融的一部分。其實(shí)從唐代景教算起,基督教在華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和佛教傳入中國的歷史相差并不太多。
古代基督教被忽視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其中一個(gè)原因是景教的漢語文獻(xiàn)沒有一脈相承地傳下來,基督教在華傳播幾次出現(xiàn)斷層。從唐代初年到元代末年,這段長達(dá)七百多年的中國基督教歷史,給中國文化史留下的可供分析的東西太少,以至我們今天談?wù)撍鼈儠r(shí)因缺乏資料,而不得不求助于地下文物和外國文獻(xiàn)。現(xiàn)在放在我們面前的這本《漢語景教文典詮釋》,就是根據(jù)明末出土的《景教碑》和清末民初出土的敦煌石室經(jīng)卷編成的。它收入八種文獻(xiàn),其中包括:《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尊經(jīng)》、《大秦景教宣元本經(jīng)》、《志玄安樂經(jīng)》、《序聽迷詩所經(jīng)》、《一神論》、《大秦景教大圣通真歸法贊》。除了在新疆高昌、北京內(nèi)閣大庫發(fā)現(xiàn)的兩種敘利亞文的經(jīng)贊文字未采納外,整個(gè)清末民初考古大發(fā)現(xiàn)中的景教文獻(xiàn)被本書悉數(shù)收入。
從這些經(jīng)文的題名看,很有佛教氣味。事實(shí)上當(dāng)時(shí)的景教文獻(xiàn)就是與佛教經(jīng)卷同時(shí)翻譯的,《景教碑》的作者“釋景凈”,就是因?yàn)椤皨购Z”,“解唐言”,而去幫助翻譯佛經(jīng)。反過來,一些佛教徒也幫助了景教經(jīng)文的翻譯。這表現(xiàn)在這八部經(jīng)文中,多數(shù)篇章都有佛教術(shù)語,少數(shù)使用了道教術(shù)語,迎合唐代朝廷尊崇老子的風(fēng)氣。如《序聽迷詩所經(jīng)》中,記耶穌行跡,大量使用“諸佛”、“果報(bào)”、“慈恩”、“善佛善緣”、“閻羅王”等中國佛教概念。《三威蒙度贊》中,“三威”指“圣父”、“圣子”、“圣靈”,“蒙度”就是佛教詞匯。贊文中還出現(xiàn)“妙有”、“慈航”、“世尊”、“大德”、“法王”、“施主”、“救度”等語。這樣形成的經(jīng)典在文字上異常的龐雜。說的是基督論、一神教,但借用了許多佛道儒的概念,給閱讀帶來困難。當(dāng)時(shí),錢謙益、錢大聽、紀(jì)昀等較少神學(xué)知識的學(xué)者不能把它從佛教等其它西域宗教中區(qū)別開來,情有可原。本叢書的策劃者劉小楓、楊熙楠,和本書的注釋者翁紹軍,對全部經(jīng)文進(jìn)行逐字逐句的注解,這是比單單把全部景教文獻(xiàn)集于一冊更有意義的工作。使基督教神學(xué)和教義信息得以從其它宗教的語言中透露出來。透過這層文字,我們看到了景教傳播的是非常道地的基督教神學(xué)。
佛教進(jìn)入中國,最重要的活動(dòng)就是佛教典籍的翻譯。和佛教的經(jīng)書規(guī)模相比,景教經(jīng)籍被淹沒,只在近代經(jīng)考古發(fā)掘才找出八種。但是景教文獻(xiàn)自有其思想價(jià)值。這本《漢語景教文典詮釋》值得一讀。
(《漢語景教文典詮釋》,翁紹軍注釋,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