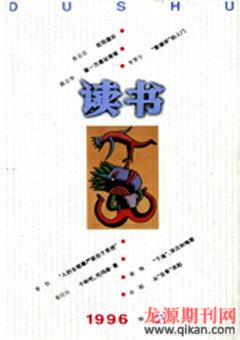絕非野生動(dòng)物的文化眼光
尹吉男
如果我們是野生動(dòng)物,將會(huì)怎樣欣賞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我們會(huì)認(rèn)真反思各自的表情和眼光嗎——其中的集體主義個(gè)人主義成分各占多少、國(guó)際主義與民族主義成分又各占多少?當(dāng)然,我們實(shí)際上的目光和眼神比上述的非此即彼的二元抉擇要復(fù)雜得多。借助上個(gè)世紀(jì)那些天才的進(jìn)化論學(xué)者從而得知,我們是自我馴化了的動(dòng)物,由此總是用人的眼光去看世界。毫無(wú)疑問(wèn),我們先是攻讀一大堆有關(guān)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的經(jīng)典著作,然后再一本正經(jīng)地解讀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作品。這個(gè)順序自然是人的,而絕非野生動(dòng)物的。走進(jìn)中國(guó)美術(shù)館的那一瞬間,我們真希望就是個(gè)藝術(shù)史博士,一見(jiàn)到夏加爾、米羅、巴爾蒂斯,就能滔滔不絕背誦出來(lái),每一本劃過(guò)道道的厚書(shū)都在起作用,就像穿了一套體面的禮服去拜見(jiàn)西洋藝術(shù)大師。我們以最復(fù)雜的目光和心態(tài)在孜孜不倦地研讀西方的每一件藝術(shù)杰作。
不過(guò),我們并非總是用這種眼光去打量世界的其它部分。是足球還有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小說(shuō)才把我們的視線帶到了南美洲。一旦我們的目光和眼神充滿了體育和文學(xué)成分并凝結(jié)成一種流行說(shuō)法,人人都會(huì)以為:生活在南美洲那里的人,除了踢足球,就是寫(xiě)小說(shuō),生活得相當(dāng)詩(shī)意!那么,足球和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小說(shuō)以外的生存與精神空間我們看得到嗎?!同樣,種族沖突和內(nèi)戰(zhàn)一度把我們的目光帶到了非洲。我們無(wú)數(shù)次地從傳媒上看到了饑荒、瘟疫和難民潮(相比之下,南美洲真該慶幸他們還有小說(shuō))。這時(shí),我們的目光不再是體育和文學(xué)的了,而是近似于民族的或政治的。在以往的電視節(jié)目里,非洲成了“動(dòng)物世界”,這是成功的西方電視人的“特別奉獻(xiàn)”,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在我們的視覺(jué)空間里把完整的非洲制作成了牢不可破的“動(dòng)物世界”形象。跟隨著《正大綜藝》導(dǎo)游小姐的足跡,我們有幸領(lǐng)略了世界各地的自然景色和風(fēng)俗人情,但對(duì)于大多數(shù)地處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發(fā)展中國(guó)家,我們的目光一接觸屏幕就是民俗意義上的。給人一個(gè)印象,似乎發(fā)展中國(guó)家或民族唯一能光臨電視的文化產(chǎn)品只能是地道的“民俗制品”,呈現(xiàn)給世界的必須是已經(jīng)死去或正在消亡的傳統(tǒng)風(fēng)習(xí)。總之,我們已習(xí)慣于民族的、宗教的、體育的、新聞的、文學(xué)的目光去看一切非西方國(guó)家,這十足地強(qiáng)調(diào)了我們目光的娛樂(lè)性質(zhì)和白癡狀態(tài)。由此看出,我們對(duì)非西方國(guó)家文化與藝術(shù)的了解雖說(shuō)不是野生動(dòng)物的水平,起碼也逼近于馴養(yǎng)動(dòng)物的標(biāo)準(zhǔn)。
我們的“世界”概念既脆弱又空洞。兩種看世界的目光表達(dá)了我們的文化態(tài)度:人的和馴養(yǎng)動(dòng)物的。當(dāng)我們批判西方的西方主義時(shí),可以想見(jiàn),西方的東方主義者們肯定會(huì)嘲笑我們看東方文化或非西方文化的目光和心態(tài)——不免有些勢(shì)利小人的兩面性。轉(zhuǎn)過(guò)頭來(lái),當(dāng)我們回視自身文化時(shí),也同樣出現(xiàn)上述偏差。我們對(duì)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于用“能歌善舞”、“熱情好客”來(lái)贊美,而“奇風(fēng)異俗”則是自然而然的事。這種心態(tài)和目光并不局限于少數(shù)民族,也擴(kuò)大到偏遠(yuǎn)的中國(guó)農(nóng)村,種植在相當(dāng)一部分繁華都市的市民心中,直接貫穿在相當(dāng)數(shù)量的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電影和美術(shù)作品中。所謂的中國(guó)風(fēng)情油畫(huà)、電影和小說(shuō),實(shí)質(zhì)上是一批矯揉造作的“民俗制品”,可以直接滿足西方文化霸權(quán)主義的恒定需要。當(dāng)一些中國(guó)同行以上述心態(tài)玩命地夸耀中國(guó)古董、武打和京劇時(shí),我們的心情比我們的目光還要復(fù)雜。
一些時(shí)髦的小說(shuō)、電影和美術(shù)作品,在利用中國(guó)近現(xiàn)代史資源時(shí),往往混雜著一半以上的民俗眼光。尤其是在利用“文革”歷史素材時(shí),把許多驚心動(dòng)魄的沉痛變成了奇風(fēng)異俗般的擺設(shè),成功地將中國(guó)近現(xiàn)代史“藝術(shù)地”轉(zhuǎn)換成了當(dāng)代“民俗制品”,進(jìn)而受到西方世界的注意。這種創(chuàng)造性是空前的。有些所謂的“前衛(wèi)藝術(shù)”作品從表面看是直接采用國(guó)際流行的藝術(shù)形式,諸如裝置或行為,但骨子里是主動(dòng)適應(yīng)西方看待中國(guó)文化的舊態(tài)度的——民俗眼光。
誠(chéng)然,今天的少數(shù)民族和外鄉(xiāng)農(nóng)民已不再是《山海經(jīng)》所描述的類(lèi)似“貫胸國(guó)”的怪物;而大部分東方國(guó)家也已不再是《異域志》或《諸蕃志》里所描繪的奇異世界。不論非洲的發(fā)展多么不平衡,但本質(zhì)上無(wú)可爭(zhēng)辯的是“人的世界”。而南美洲的人們除了寫(xiě)小說(shuō)、踢足球,也忙其它的。他們終會(huì)知道作為中國(guó)人的某先生既不會(huì)練中國(guó)功夫,也不會(huì)唱京劇,卻寫(xiě)了一篇《絕非野生動(dòng)物的文化眼光》。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三日于南湖渠小區(qū)十七號(hào)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