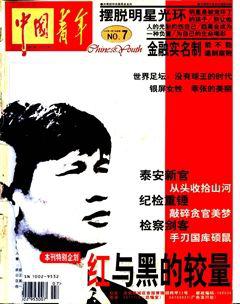第四課 張中行 太陽下的清供
麥克
讀他們的東西,
經常使你有一種大凋零的感覺;
讀他們的東西,
醇厚之中,總覺著還缺點什么……
張中行老先生的書總是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那一篇篇舊事掌故,很有些古人筆記的味道。怎么說呢?不大像魏晉,那種鋒芒畢露的智慧;而是像晚明,有一份滄桑之后的無奈,娓娓道來的平和。
只有談起“文革”的時候,老先生才有點火氣。這也難怪,中國幾千年下來,大概只有三數個蔑視文人的時期。秦始皇焚書坑儒是一個;元朝有“九儒十丐”之說,秀才的地位,還在娼妓之下,也就比要飯的高些,算一個;再一個,就是知識分子被稱為“臭老九”的“文革”時期了。老先生是文人,說起那段日子,心里難免不平,也算不得什么。
最初朋友向我推薦張老先生的書,說:“那可是一個真正有學問的人,文章每一句話都是有來歷有出處的。”就像黃庭堅推崇杜甫的口氣。我陸續買來看了,覺得朋友說得不錯。
這世道,大儒不多了。退一步,張中行,或者還有南懷瑾他們,就顯出來了,很可以用“水落石出”來形容。讀他們的東西,經常使你有一種大樹凋零的感覺。的確,他們算不上大學者,但他們還有著大學者時代的余韻,就像風雨后的晚晴,也是人世間最美麗的風景。
對這樣的宿儒,從學問的境界上講,現在已沒人有資格對他們說三道四了。但是讀他們的東西,醇厚之中,總覺著還缺點什么。或者,就是宋儒朱熹所說的“為有源頭活水來”的“活水”吧。這樣的文字,是不動的風景。按張中行老先生的話,應該叫“清供”。
張老先生曾經寫過一篇《案頭清供》,講他的書桌上的幾件擺設。所謂“清供”,就是不花錢得來而又自己喜歡的小玩藝。張老先生的清供有三樣:大老玉米一穗,看瓜一枚,葫蘆一只,各有各的來歷,各有各的故事,拉拉雜雜,也敷衍成一篇好文章。
談起文人的書桌,最有名的大概是聞一多的那張。詩人的名作,就是《聞一多先生的書桌》,幾乎是逢集必收的。聞先生的書桌上,似乎并沒有什么清供,有的只是沉甸甸的憤怒和郁悶。這張書桌,給人感覺,并不是安放文房四寶的地方,而像是一片大草原,風暴滾過,間或夾雜著野獸凄厲的怒吼,讓你感到一個書生也有拍案而起的靈魂。而張中行老先生的書桌,顯然更具有傳統文人的情調,就像是晚秋時節的麥田,鳥雀飛來飛去,啄食著田間遺落的麥穗,落霞滿天,漁舟唱晚。
這兩種境界,主要出于亂世與盛世之別。亂世多拍案而起之作,而盛世則不乏清供的閑情,倒也不必強分個高下。歷來所指責的,只是亂世中的清供,像周作人的知堂小品文。仿佛不知從什么時候
起,文人已經失去了逃世的自由;只有在好世道,人們才有閑適的權力。張老先生的案頭清供,不過是好世道一個最雅致的注腳。
但張老先生可能并未意識到,他的清供,不只三件,而應是四樣——加上他自己。這絕非微詞,事實上,依照中國傳統,人老了,就該是供起來的,而又能清,就是不糊涂不添亂,也就很好了。只是不知道,老先生自己以為然否?
老先生最暢銷的書,《負暄瑣話》及“續話”和“三話”,是最中正平和的文字。“負暄”,是曬太陽的意思。按照老先生“清供”的定義:不花錢得到而又自己喜歡,日光浴不要錢,除了愛美的女士大概人人都喜歡,這種方式無疑具備清供的充分條件。再說必要條件,就是要有閑適的心情。現今的人越忙,就越講究消閑,印的書雖然多,但能坐著讀的倒也沒幾本———讀書,不再為了尋求真理,而是為了打發時光點綴心情。老先生的“瑣話”,說白了就是瑣細的家常話,既然是曬著太陽說的,自然也并不要求聽眾都正襟危坐。這就符合了清供的必要條件。
滿腹經綸的老先生說“瑣話”,而不是板著臉教訓人,使人如坐春風,本來這是一種好的不得了的境界。但既為清供,總覺得缺幾分活泛,在老人大概也是難免的事情吧。
元稹詩曰“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可謂一語道破暮年心態。那位宮女年輕時伺候過唐玄宗,老了,雖然天子已經換了好幾個,但一張口還是玄宗舊事,不免一種遺老氣。張老先生是講古的高手,特別是所談“五四”人物,頗有野史的魅力,本來跟遺老氣是不沾邊的。但問題出在,文人的通例,似乎總有一種厚古薄今的傾向,認為今天的世道斯文喪盡,而只有自己年輕時才是“郁郁乎文哉”的好時候。然而就今天看,事實似乎也是如此——大儒輩出怎么也是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事了。張老先生雖然不薄今,但因此卻可以理直氣壯地“厚古”,對于舊人舊事,飽蘸深情,終不免缺乏一些冷靜的剖析。大概這也是古人筆記的通病。張老先生的筆法接近古人筆記,不覺也就染上了些遺老氣。是這樣的,白頭宮女說玄宗,說一萬遍,也還是家常話,不脫“春寒賜浴華清池”的路子,說不出“漁陽鼙鼓動地來”的前因后果,終究不大解渴的。
不過,所謂“述而不作”,老先生也許不是不能說,只是不想說罷了。老一輩的學風,往往有清朝樸學的影子,發展到極致,有的老學者,一輩子就出一本小冊子,嚴謹到簡直是水潑不進。張中行老先生是有大學問的人,但似乎并沒有什么宏篇巨著,只是以閑適文字見稱,大有舉重若輕的況味。但學問是藏不住的,總會露出來,引一段經,埋一個典,對于蕓蕓讀者,有時就難免曲高和寡了。把學問注入文章里,張老先生所做,大概沒錢鐘書先生那么密集,又沒南懷瑾那么做作,很得中庸三昧。但一輩子教書生涯的影響,學問中就不免帶些方巾氣,不是很靈通,損害了清供中的“清”字。
再者,人久坐書齋,雖可神追千古心鶩八極,但舉目所見,無非書魚粉蠹,所寫文字,也就不出大老玉米看瓜葫蘆等“清供”之屬,果真應了“瑣話”中的那個“瑣”字。如果也硬歸一“氣”,可謂布頭氣。如今不少作家,為了應付各方頻頻稿約,被迫連刷牙洗臉也要成篇,說他們是布頭氣,大概還算是客氣的。張中行老先生非此輩可比,瑣碎也是瑣碎得極雅致,但大老玉米與讀者何干?想也是寫得多了的緣故。
遺老氣、方巾氣、布頭氣,晚輩我斗膽總結出這三氣,并非當真膽敢坐上“給名人上課”這個欄目,不過是盼望張中行老先生松柏長青的意思。畢竟,全都說好就不那么好了。
《案頭清供》見《張中行選集》,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
責任編輯:邱四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