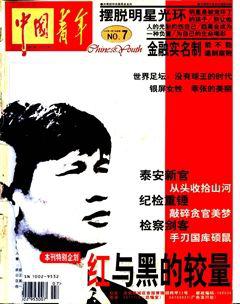銀屏女性:是不是太乖張
艾禾 王鋒
“流行文化沙龍”今日開張。
“流行文化沙龍”討論的都是我們日常最多見的流行風景:電視、電影、流行歌曲、暢銷書、廣告……我們們司空見慣,但我們可能對里面包含的社會文化內涵視而不見。參加沙龍的有風頭正健的青年學者,也有最具平常心的普通觀眾讀者。愿我們的討論,給當今風靡社會的文化潮流添上一道理性色彩,讓社會聽到一種清明的批評之聲。
祝華新:(《人民日報》記者)
女性題材從來就是影視作品中一個很重要的母題。它往往通過一系列女性形象折射出整個社會、時代的特質,看看近幾十年的金雞、百花、金鷹獎最佳女演員及她們塑造的形象,我們能看到一些有意思的東西。影視中的女性形象“文革”前后差異很大。“文革”前是壓迫與革命的主題,歌頌的都是翻身解放后的新女性。第一、二屆百花獎的獲得者所飾瓊花、李雙雙都是反壓迫的女性。“文革”后,女性形象回歸傳統,從《喜盈門》《鄉音》《鄉情》中,“天下第一嫂”王馥荔式的人物出來了,在銀幕一溫柔就是十幾年。再后來,進入90年代,事情就要復雜些,農村女性形象少了,城市女性形象又分為好幾類,一是女革命家依然存在,只不過從反壓迫的政治主題轉向了反封建的文化主題。如張藝謀拍的影片中一系列女性,就是蔑視一切道德規范的叛逆者,而這些規范的代表就是男人,她們就要反抗男性;二是貴族女性出現,貴妃太后題材,像楊貴妃,武則天,慈禧都頤指氣使地出現了。在封建時代,只有太后級的女性才能張揚個性,凌駕男性之上;三是出現了一些風塵類女子,古人有句話,名妓如名俠,肝膽相照,置生死不顧,且行為乖張。這些女人旁邊往往配以儒弱男子,典型如《原野》《春桃》。另外還有一種新形象,就是“都市小蜜”小女子形象。既瀟灑可人,又依附性強,典型的是《過把癮》里的杜梅,以折磨男人為事業,這類女性在現代銀屏上愈演愈烈,大有蓋過其他女性,成為主流的架式。我不知道影視界這種以“消極的小女子”為關注對象的興趣從何而來?這種轉變的基礎在哪兒?
楊遠嬰:(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
這種基礎很明顯:影視傳媒的功能變了。以前影視是教育工具,自然出現有楷模意義的革命家。現在商品經濟,影視物化了,人物也就要“賣”得出去。就像好萊塢中的所有女性。以前是計劃經濟,農村題材由組織分配,上面給指標給錢;現在走市場,那樣做不行了。10部大片里面多少垃圾?可偏火爆得很。中國電影要反抗,往哪兒反抗?還是得往這條路上走,塑造出一大批瑪麗蓮·夢露那樣物化的女人,或者說就是性的對象。考察影視中東西方形象的差別正好是一個逆轉。西方60年代發展起來的女性主義一共經歷了三個階段,先是在電影中發現了男性視點和女性視點;后來女性從電影語言上分析,為什么鏡頭拍男人時仰,拍女人就俯呢?再后來,女權主義者說,女性要首先爭取自己人的地位,然后再談女性。女人要重新回到歷史回到社會,
從單純的性別角度脫離出來。60年代西方著名女權主義者克里蒂斯王來到中國,覺得中國簡直是女性的王國。江青凌駕于那么多男性之上,男女同工同酬,這些都是西方女性謀求已久的。現在不了,改革開放后,傳統社會轉向商品社會,許多女性又主張回到家庭,向往悠閑優雅,覺得以前孜孜以求的不過是一個男性化的女人。與此相并行的,是四五十年代希區柯克電影中的女性,猛女型、蕩婦型,玉女型若干女性類型,今天又被我們當作影片拍攝的基本規律。
祝華新:這些類型女子包括我前面說的小女子類型的泛濫弄得銀屏一片刀光劍影。這些形象敢愛敢恨的多,善于合作的少。男人在里面要么就是反抗的對象,要么就是儒弱的陪襯,總之沒法溝通。影視對生活的影響是巨大的,這些所謂的“女權形象”會在當代女性身上種下雷管。我覺得今天不需要乖張,相反急需規范。
楊遠嬰:憑什么規范?怎么規范?
祝華新:我的文藝觀比較保守,基本遵循“文以載道”的原則。我說銀屏“猛女”過多,需要規范,是從中國的現實出發。中國社會正處于現代化的轉型期,矛盾和動蕩的因素很多,女性是社會的穩壓器,女性多一點平常心,多一點合作,多一點和氣,有助于國家平穩轉型。中華女性還是有很多審美資源的,善良,溫和,嫻淑等等,像在現在的廣告中,那里面的女人就比影視中的可愛得多。
解璽璋:(《北京晚報》編輯):這是典型的男權思維。
祝華新:我不是為男性而是為我們民族著想。
解璽璋:許多人都是打著“民族”的幌子貫徹自己的男權思想,要求男性權力。
楊遠嬰:解璽璋是為數不多的“男性女權主義者”,真讓人感動。
解璽璋:不客氣。你想想中國婦女解放的歷史,實際上一直被男性規范著。女性要求自身的解放首先就要把自己預支給男性,然后再跟著男性去鬧革命,吳瓊花、林道靜都是這樣。她以為由此可以贏得自身的解放,后來會發現這是個陰謀。好不容易到90年代了,婦女才意識到,應該把首先成為自己,而不是成為男人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
楊遠嬰:這只是一個趨向,但有的做得也不好。如大受歡迎的“小女子”杜梅(江珊飾),整天就折騰一件事:你愛不愛我,你到底愛不愛我。所有的小動作,所有的乖張,都集結于此,反映出女人的一個情結。再說宮廷女性,也是很商業化的,她集權力、美、乖張于一身,那也只是一個被男人窺探的女人。
劉君梅:(《三聯生活周刊》記者)
還包括一些現代女老板的形象,她們能指揮許許多多男人,像當年的江水英、阿慶嫂一樣。不同的是江水英們因革命的理想主義而氣宇軒昂,女老板們則普遍個人生活不幸福。
祝華新:那也難怪。我們影視中給外國人看的女性形象可愛嗎?我如果是美國移民局官員,《北京人在紐約》中的阿春來申請我就要嘀咕一下。
楊遠嬰:那是你站的位置決定的。中國男人大多喜歡《鄉音》里的“我隨你”。
劉君梅: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罷,這些女人的出現,畢竟豐富了我們影視中的女性形象。她們畢竟是活生生的生活在中國現實主義土壤里的女人。像什么《住別墅的女人》《洋行里的中國小姐》就更沒意思了。
金硯:(北京金硯策劃發展中心)
真是這樣,現在銀屏上的女性形象比以前豐富多了。哪像五六十年代,電影里的女人都是楷模,都是被欣賞的。現在不了,你說像關之琳,這片演烈女,那片又演爛仔,頭發染成那樣,以前沒法想像。主要是有人接受,有人需要。現在像黃鍵中那樣的導演,開機前也要問一問:“現在觀眾喜歡什么樣的?”30年代文人在閣樓上寫出精美散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我覺得,現在影視中還是有很多有價值的形象缺席。比如說生活中像我這樣的女人會是很多的。我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怎么定位。我要做一個好妻子,好母親,可我的孩子怎么也生不下來,整天瞎忙,不知怎么才能養一個孩子。還有一些下崗女工,生活更可怕。每天眼一睜,孩子在左邊,丈夫在右邊。每天的醬油錢都是問題,心態也就惶惶然,找不到500塊錢的工作300塊也得干,不管你多么委屈,多么不情愿。每個女人都在做夢,可現實生活不能提供這些。現在有部片子,潘虹、方青卓演的《下崗女工》,我沒看,但我對這部片子很期待,我希望能看到一些普通命運。
程赤兵:(《首都經濟信息報》記者)
是這樣。現在生活不容易,男、女壓力都很大。這時候影視作品在某些問題上的處理就應該注意了,對男、女的矛盾就不要再“燒”了。男女之間是一種合作關系,這不是社會決定的,是天然的,自然規律。像《動物世界》里的企鵝。雌性企鵝撈食,雄企鵝孵蛋,不會錯位,這是天然的。影視應當塑造一種融洽的男女關系。我最反感的就是《武則天》。《過把癮》里杜梅的乖張造成了悲劇,《武》劇則不不然,它把一個女性年輕時受到壓迫、虐待后產生的報復、變態心理寫到了極端,并采取一種弘揚的態度,這對人是有影響的。人在壓力大的情況下容易急,容易脾氣暴躁。如果女人都變得那樣陰毒,這社會也就完了。影視不要幫倒忙。
責任編輯:王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