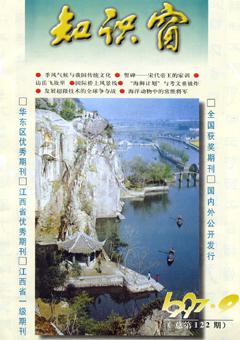季風氣候與我國傳統文化
葉岱夫
人是自然進化的產物。人類從自然地理環境中獲得物質生活所需的一切,人類社會是在自然地理環境中發展起來的。氣候乃自然地理組成要素之一,雖然氣候不能完全決定社會的發展與演化。但在今天看來。早期氣候對傳統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具有極為深刻的影響,它與農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更為密切。所謂傳統文化就是一個民族或國家的一種成熟的觀念形態。中國傳統文化經歷二千多年的發展演變,逐漸形成一種獨立的、頗具特色的文化形態。那么,在漫長歷史進程中制約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氣候背景是什么?氣候又是如何影響到我國傳統文化的?這些都是今天有待逐步深入了解的問題。
通過比較世界各大洲的氣候特征,我們可以發現亞洲的季風性氣候典型而又突出。我國恰好處在大陸(亞洲大陸)與大洋(太平洋)的交接部位,季風氣候更趨顯著。
植物長期適應于一年中溫度水分的節律性變化。形成與此相適應的植物發育節律——物候。與同緯度的氣候類型相比,季風氣候能較之有效地創造出作物在發芽、生長、現蕾、開花、結實、果實成熟、落葉休眠等各個物候期的光、熱、水配合適宜的生態環境。如亞熱帶季風氣候與地中海式氣候相比,前者表現出雨熱同期的氣候生態,后者則不然。事實上,我國農作物的種植北界比同緯度的其它地區更為偏北,這就是得益于季風氣候的結果。
另一方面,受季風氣候的影響,我國大部分地區高輻射、高濕和高溫集中,這對于發展單季生產十分有利。但氣溫年變化大則不利于多年生作物或生長期較長的農耕制度。為了經營那些生長期短的作物,只好投入更多的勞力。使社會大量勞動力被牢牢地束縛在耕地上。這又在客觀上確立了種植業居于中心的地位。落后的生產方式,亦加深了耕作業對季風氣候的依賴程度。歷史上我國農業實行粗放經營和廣種薄收的方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中,氣候對收成之豐歉尤為重要。古詩說:“季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說明夏季降水與收成的關系密切。
由上可知,季風氣候為我國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業生產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可以說,氣候環境提供了我國古代種植業持續發展、長盛不衰的客觀必然性。從而使中國古代文化成為一種既區別于游牧社會文化,也不同于工業社會文化的種植農業社會文化類型。
“中和”的思想亦稱“中庸之道”,它作為一種文化觀念,在中國傳統文化史上長傳不息。這種思想的形成與特定的氣候環境條件有關。首先,農業社會小農經濟靠天吃飯的特點,必然使人們重視風調雨順、天人協調的氣候條件。而這種認識和期望正是建立在我國農業氣候災害種類多、發生頻率高、分布廣泛、危害嚴重等區域自然特征的基礎之上。季風氣候在給耕作業帶來實惠的同時,亦常常因為其不穩定性而伴隨有周期性和多發性的農業氣候災害。如旱澇、寒潮、凍害、臺風等災害性天氣都與季風氣候密切相關。干旱是我國歷史性的、范圍極廣泛的氣候災害。據記載,自公元元年至1900年全國范圍內大旱出現984次,平均每兩年發生一次。這無疑給靠天吃飯的傳統農業帶來巨大影響。在如此頻繁的災害性氣候面前,人們一次又一次地把希望寄托于好的年景,但是自然氣候也一次又一次地使人們失望。于是,天人一體、天人相與、天人感應等“中和”的思想方法開始進入人們的意識領域。
其次,自古以來的多熟制農業,把春末秋初氣候資源不足而又不穩定的部分也利用起來,勢必增加勞動投入的風險,人為造成氣候災害的發生和擴大化。在辛勤勞動付之東流和勞而無獲的時候,人們總以為蒼天不作美,而往往忽視了自身是否按氣候規律辦事。在這種情況下,對上天恩賜的感激、崇尚和對上天懲罰的痛恨、恐懼之情往往交織在一起。而這種思想感情的理論抽象就必然是“致中和”的思想方法或中庸之道。“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傳統文化也就應運而生了。
在我國,“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既是一種普遍的自然現象,又是民族氣節和民族文化特點的寫照。可以認為,季風氣候對農業生產的雙重影響不僅給種植業帶來創傷,而且又帶來了迅速彌補創傷的自然恢復能力。因此,社會經濟也具備了一定的再生機能。從而成為我國傳統文化頗具頑強延續力的堅實物質基礎。
中國傳統文化最富有魅力并引起世人贊嘆的,不僅在于它的古老,更在于它一次又一次表現出來的頑強再生能力。這種生生不已的文化活力不能不部分地歸咎于氣候兩重性影響下人們的那種矛盾思維和心態。在這種思維結構的支配下,自然萌生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頑強精神,氣候的災難性和資源性的不斷交替作用,漸漸磨練出一種堅強的民族意志,最終發展成為民族文化的強大驅動力和再生力。
(責任編輯/韓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