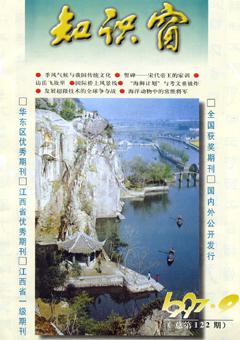東坡戲詞亦有神
蔣譜成
《賀新郎》詞的產生
蘇東坡的一生,前后在杭州居住的時間最長,其次就算是黃州了,在杭州他度過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建樹頗豐,政績卓著;在黃州度過了他一生最輕松的日子,使他的文學作品,書法藝術充分體現了個性和情感,為后人留下了千古絕唱。
東坡第一次到杭州任通判,除了會審訟案外并沒太多的事情,因此他一有機會就游山玩水,投身于大自然的懷抱,在酒宴與祝典中與歌妓盡情玩樂。
初夏的一天,風和日麗,杭州城里的府僚與文人學士設宴西湖,絲竹管弦,飄蕩四方,但歌妓秀蘭遲遲未到,派人去喊,才姍姍而來。問她原因,她說,洗澡后困倦,就睡覺了。忽聽叩門聲,才知樂師們早到。蘇東坡聽她一說,也不再計較,但旁邊的一位副官一直盤問秀蘭。當時石榴花盛開,秀蘭折了一枝,獻給副官,以表歉意,副官見狀,更加生氣。東坡見秀蘭處境尷尬,即席填《賀新涼》讓秀蘭詠唱。
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是,風敲竹。
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濃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
秀蘭婉轉輕歌,情真意切,一曲未終,副官怒氣頓消,酒興已濃。后人稱此詞為《賀新郎》。
帶著妙姬聞進禪房
東坡是個幽默風趣的人,三教九流都愿與他交往,他也廣交結游,不拘小節,他與大通禪師過往甚密,大通禪師是圣潔的佛教徒,若單獨見他必須先行沐浴,女人當然不能涉足禪房。東坡一次攜歌女妙姬上山逛廟,突發奇想,帶著妙姬闖進大通禪師的禪房,并向禪師行禮,大通對他的舉止十分不悅,但東坡似乎啥事都沒有發生一樣,還要求禪師把誦經用的木魚借給妙姬,他填了一首道歉詞叫妙姬唱《南歌子》:
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皺眉,卻愁彌勒下生遲。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
大通聽了放聲大笑,東坡才高興地帶著妙姬離開大廟,還向別人說,他們學了“神秘的佛課。”
“鄭容落藉”,“高瑩從良”
東坡第二次離開杭州回京城任職,再也不像元豐二年那么惶惶而狼狽了;因此,他路過京口,即今之鎮江,還去拜訪南徐太守林子中,并休息幾天。林子中當然盡地主之誼,設宴招待東坡。宴會上有二名歌妓拿著木牒,類似今日的名片,那木牒上分別寫了“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并請求林子中批準;林子中也是一位喜歡逢場作戲的人,對鄭容和高瑩二位說:“你們去求今天在坐的大名鼎鼎的蘇學士吧,只要他為你們寫一首詩或填一首詞,能表達你們的愿望,我立即就答應你們。”鄭高二人早就欽佩蘇的為人。更想得到他的恩賜;東坡聽后,欣然命筆,在鄭容的木牒上寫道:
鄭莊好客,容我尊前時墮幘。落筆生風,籍籍名聲不負公。
接著在高瑩的木牒上寫道:
高山白早,瑩雪肌膚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
大家一看,原來是一首《減字花木蘭》,各占半闕。并把“鄭容落藉”,“高瑩從良”嵌于句中,眾人拍案叫絕,太守林子中也高興地批準鄭、高二位的請求。
醉意朦朧,詩贈李琦
東坡謫居黃州,政治上失意,但精神上富有,生活在大自然的懷抱,與群眾打成一片,找到實實在在的東坡了。他能靜下心來從事詩、詞的創作、佛教的研究,從而使創作獲得豐收。
東坡雖居鄉下,但他仍不忘結交游玩,黃州的徐大受太守經常約他去喝酒,長江對岸的朱壽昌太守也時常過來交談,少不了帶些好酒好菜來,還有他的朋友詩僧參寥,陪他足足一年,陳糙也多次和他住在一起,使他的生活并不寂寞,況且還有那么多的農民朋友,耕牛和可愛的黃狗。蘇東坡有時喝得醉醺醺的,哼著“黃泥坂詞”,蹣跚地行走在山間的小路上;有時橫臥在山間的石頭上,看日出日落和山間的云升霧降。過著自然而閑適的輕松生活。
蘇東坡是書法家、詩人,當時向他求字畫詩詞的很多。在他即將離開黃州時,他都向朋友們一一題贈;一個叫李琦的歌妓也向東坡求詩,恰好東坡此時已多喝了點,醉意朦朧,揮毫寫下:
“東坡五載黃州住,何事無言贈李琦;”這時東坡的酒勁上來了,醉臥桌旁,后來以“卻是城南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續之。這詩一傳在外,李琦名聲大震,身價百倍了。
東坡一生參加過許多次聚會,幾乎每次都應藝人之求,在她們的披肩或香扇上題詩,但他的詩格調清雅而艷。東坡與妓女的交往,只是趨于社會潮流,并沒有風流韻事傳于后世。蘇東坡的一生,是多面的,恰巧是這五彩的多面構成文人心目中的蘇東坡。
(責任編輯/楊劍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