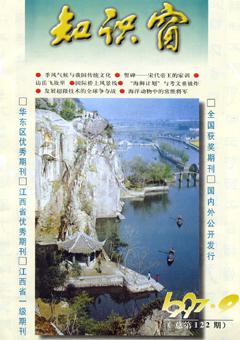香港秘密大營救
李鐵強 萬軍杰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從大陸上沿著港九鐵路進攻香港。12月12日,日軍占領九龍。12月25日,香港淪陷。這天下午六時,香港總督府掛出屈辱的白旗,野獸一樣的日軍沖進飽受炮火創傷的街道,肆意劫掠奸殺,港九頓成人間地獄,160萬居民陷于恐懼、寒冷、饑餓的深重災難之中。這其中就有一大批避居香港的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他們大多數是1941年由于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而到香港去的。他們原在重慶、桂林等地辦報著文集會,宣傳抗日救亡,揭露和抨擊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遭到國民黨頑固派的迫害,在黨中央和周恩來的關懷幫助下,撤離到香港。他們在香港創辦了進步的報刊和社團,對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爭取港澳同胞、海外僑胞以及國際人士的同情和幫助,起了重大的作用。
黨中央一直關注著香港戰局的發展.關懷著香港文化界人士和其他各界人士的安全。香港淪陷后,周恩來指示八路軍駐粵港辦事處的負責人廖承志:為了保護我國文化界的精華,必須動用一切力量把全部旅港的抗日文化工作者搶救出來。
廖承志接到周恩來電話后,馬上召集東江人民抗日游擊隊和八路軍駐粵港辦事處的負責同志開會,擬制搶救計劃。經過周密研究,決定由辦事處的劉少文領導香港方面的聯絡營救工作;游擊隊政治委員林平負責布置九龍到東江游擊區的護送、接待工作;廖承志等前往韶關、老隆,布置國民黨統治區的掩護地點和交通線。
東江人民抗日游擊隊是一支在抗日烽火中誕生并成長起來的隊伍。1938年10月,日寇登陸華南大亞灣。國民黨守軍大敗。是月21日日寇攻陷廣州,東江各縣人民紛起抵抗,在我黨領導下的惠寶人民抗日游擊隊和東莞縣模范壯丁隊成立,分別以曾生和王作堯為大隊長。1940年,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成立,曾生為第三大隊長,王作堯為第五大隊長,此即以后的東江縱隊。1941年12月,日寇從廣州出動集結東、寶前線以進攻香港,游擊隊即主動配合英軍作戰,到處截擊日寇,更派隊伍突人敵占之香港、九龍、新界牽制敵人。港九全部陷落后,即動員與組織當地民眾,堅持港九敵后游擊戰爭,并成立港九大隊。接到上級黨委的指示后,整個部隊即全力投入搶救工作。游擊縱隊挑選了有經驗的戰斗骨干,組成一支支精悍的小分隊,一個站一個站地連成了一條護送文化人的通道。
營救工作是艱巨而復雜的,首先把營救的對象找到就很不容易。香港淪陷后,為了躲避日軍搜捕,許多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一再改變住處。留在香港領導聯絡工作的劉少文,派出熟悉情況的同志,根據廖承志提供的名單,通過各種關系,把營救對象一一找到,并幫助他們轉移到較安全的住地,然后安排他們分批轍退。九龍方面,在林平領導下,建立了秘密接待站,解決食宿問題,然后按照不同的對象,安排他們進入游擊區或其他地區。
1942年1月9日午夜,三只小艇載著鄒韜奮、茅盾等一批文化界人士從香港偷渡到九龍,來到秘密接待站,踏上了脫險的旅途。11日清晨,鄒韜奮一行二十多人,由交通員帶領來到青山道口。這時青山道上,由于香港糧荒日軍實行疏散人口,內地的難民源源不斷,他們即混入難民的隊伍,向北走去,經九華徑到荃灣。隨即向北走小路進人大帽山區,山區的路雖然崎嶇難行,卻是游擊隊控制的地區。一支短槍隊在這里警戒、掩護。他們爬過山嶺。穿過峽谷,走進了平坦的盆地,到達元朗十八鄉的接待站。
這里已經聚集由交通員帶回來的一百多“難民”了。除了鄒韜奮、茅盾夫婦這批二十來個人之外,還有幾批文化界人士,以及來參加游擊隊的工人和學生。接待站當下殺豬相待。第二天,接待站干部把“白皮紅心”的元朗鄉長簽署的難民回鄉證明交給他們,然后分批上路,短槍隊仍然暗中護送,經元朗、落馬洲,到深圳河邊,乘船過渡到北岸赤尾村。再往北過寶深公路。日軍設有崗哨,不時有軍車和巡邏隊來往。但當時公路上從香港來的難民也很多。交通員帶著鄒韜奮等順利地越過公路,進入了便于隱蔽的丘陵地帶,再爬上梅林坳,往北下山即到達東江游擊隊總部的駐地白石龍村。當晚,駐總部的游擊隊負責人曾生等以紅燒狗肉和青菜招待了第一批脫險歸來的文化界人士。連日旅途的驚嚇和勞累,終于能安然地吃一頓晚餐,這些文化人顯得興高采烈。茅盾說:“這頓飯吃得真痛快,雖然只有一葷一素.我覺得比什么八大八小山珍海味更好,永遠也忘不了。”
從一月底到二月底是營救工作最緊張的時刻,每隔一兩天就有一批人從香港偷渡到九龍,爾后進入游擊區。原來計劃一批接一批地護送文化界人士過惠寶邊,轉入國民黨統治的惠州。但因日軍突然占領惠州和博羅縣城,大批文化人士只得滯留下來。為了安置他們。游擊隊搭起山寨,辦起臨時招待所。幾百名文化精英薈聚此地,使得荒僻的山溝里一時歌聲飛揚、生機勃勃、氣象一新。
進占惠州、博羅的日本侵略軍,在搶掠一番后又撤走,游擊隊抓緊時機,安排護送文化界人士回大后方。
為了接送文化界人士回大后方,游擊隊在惠州建立了一個聯絡站。惠陽縣委負責人之一的盧偉如,扮成從香港到惠州做生意的大老板,從香港販來了幾十擔貨物。如輪胎、布匹等。盧偉如把貨物囤積在一家叫“東和行”的商號里,自己住在東湖酒家,并把二樓全部包下。準備給過路的文化人住。由于盧偉如的派頭大,貨又多,每天都有人來東和行、東湖酒家談生意。這些人有商人,有國民黨要人,盧偉如一面虛與委蛇,一面觀察惠州的政治情況,以便順利地接送從香港撤出的文化界人士。第一批到達惠州的文化人士有茅盾夫婦、廖沫沙、胡風、韓幽桐等。他們都扮成從香港來的有錢人,住在東湖酒家和東和行里。由于東湖酒家的三樓住著一個國民黨的師長,所以大家只得謹言慎行。深居簡出。根據規定,文化人每到一地,應盡快把他們送走。但由于茅盾等到達惠州的當晚是大年三十,人們都在歡度春節,接連幾天沒有車船開出,只好等春節后再走。
把文化人士送往“后方”主要是走水路。有時買船票搭客船走,有時通過惠州縣稅務局一個同志的關系,乘國民黨官員的走私船走。茅盾他們這批人多,是包了一條船走的。這條船從船長到水手全部是自己人或進步群眾。上船的碼頭是中山公園望江亭后面。中山公園里矗立著廖仲愷先生紀念碑和黃埔學校東征陣亡將士紀念碑。茅盾望見。詩興大發,拿出藏在身上的筆記本和筆就作起詩來。聯絡站的同志因怕群眾圍觀而暴露了身份,上前勸阻。茅盾發起脾氣來,說不上這條船了。后經廖承志等勸說,茅盾才上船,一場風波遂告平息。
當時,有一部分文化界人士因為在香港逗留時間長,怕暴露身份,或因年老體弱,不宜爬山涉水,只得走其他線路,如梁漱溟、千家駒等是從香港偷渡到長洲島,然后從澳門轉內地的。何香凝、柳亞子則是由黨組織派人護送乘船到長洲,然后由長洲乘船到汕尾去的。當何香凝、柳亞子一行十多人乘的小船到達汕尾時,許多群眾涌向海邊看難民船。何香凝的照片早在民間流傳,所以她很快就被群眾辨認出來。國民黨海豐縣黨部獲悉這一情況后,便組織盛大歡迎,公開慶祝何香凝脫險歸來。此外,從九龍進入游擊區的鄒韜奮,因為國民黨緝捕甚嚴,所以沒有和其他人一道回大后方,而是在梅縣鄉下隱居一段時間后,展轉進入蘇北抗日根據地。
營救工作持續到1942年6月底才結束。在敵人的嚴密控制下。從香港到這個孤島,安全地營救出如此眾多的,在國內外有影響人物,這是歷史上的奇跡。在這場偉大的秘密大營救中,香港地方黨員、東江游擊縱隊戰士、接待站的工作人員們,勇敢機智,全力以赴,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的重大任務。
(責任編輯/韓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