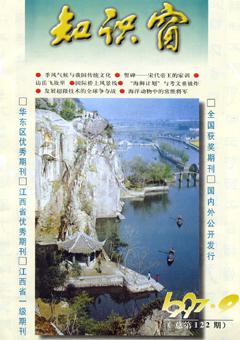中國第一個跨出國門的官員——斌椿
馬淑紅
184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封建國家,長期封閉的社會使人們無法認識外部世界,如同“井底之蛙”看不到廣闊的天空。士大夫諱談外國,固步自封,就連頭腦清醒的林則徐、魏源等人,開始也曾以為英國兵“足不能屈伸,長棍一揮即倒”。徒然成了外人的笑料。1840年和1860年的兩次戰爭,使更多的人睜開了眼睛,清政府的一部分人也感到有接觸和了解西方文化的必要。于是,官方派員考察成為近代中國和西方交流上的一個特點。第一個獲此殊榮赴“泰西”游歷的就是斌椿。
斌椿,曾任山西襄陵縣知縣,是內務府正白旗漢軍善祿管領下人。1864年應赫德延之請,到“總稅務司”辦理文案。他從小讀儒經,應科舉,喜作詩文,曾“誦讀忘寒暑”,是一個傳統的讀書人,但他的經歷和思想卻有其獨特之處。他曾到外地做官,足跡遍及九州大半。對于遠游,他曾有詩云:“久有浮海心,拘墟苦無自;每于海客來,縱談羨無已,……采風至列邦,見聞廣圖史。”這種思想在當時中國的封建社會中絕非一般讀書人所能有的,正因為如此,當總理衙門準備派人赴歐游歷時,大小官員“總苦眩暈,無敢應者。”只有63歲的斌椿“慨然愿往”,盡管周圍勸阻的人很多,但他卻毫無畏懼,堅定地說:“天公欲試書生膽,萬里長波作坑坎。”雖然談不上有認識新世界和接受新文化的自覺性,但他這份敢作敢為精神,就很可貴了。
1866年正月21日,斌椿正式被派遣出國,他3月18日到達法國馬賽。在歐洲游歷的時間不到四個月,卻歷經法、英、荷等11個國家。此行雖稱不上碩果累累,卻也并非兩手空空而歸。最寶貴的是他留下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最早親歷歐洲的記述——《乘槎筆記》,而且當時一部分士大夫的傳統觀點在其記述中也有所體現。
斌椿的游歷使他大開跟界,不僅印證了“地形如球,自轉不息”這一點,而且,也增進了知識。他看到了倫敦的屋宇器具,體驗了瑞士的土俗民風……他說:“非親到不知有此勝境”。這正應了中國這句古話,叫作“百聞不如一見”,確實如此。就拿中國對荷蘭的了解來說吧,雖然從明朝起就聽說有個荷蘭,但當時對荷蘭的了解卻相距太遠了。到斌椿訪問荷蘭時才算對荷蘭有真正了解。斌椿在《乘槎筆記》中記載:
“荷蘭縱六百五十里,橫三百五十里,西北濱大西洋海,夷坦無山,港道紛歧,民受水害,因習水利,善筑堤,又善操舟行運,南洋各島國,皆建立埔(埠)頭。……”
筆墨不多,卻勾勒出了上世紀中葉荷蘭的簡單輪廓。而《明史·和蘭傳》中卻說:
“和蘭又名紅毛番,地近佛郎機,永樂、宣德時,鄭和七下西洋,歷諸番數十國,無所謂和蘭者。其人深目長鼻,發、眉皆赤,足長尺二寸。……其所役使名烏鬼,入水不沉,走海面若平地。”
現在看來,這不外是哈哈鏡中的形象,令人啼笑皆非,斌椿為越來越多的人直接接觸和了解外部世界,由無知到有知,由封閉到開放開了先河。
斌椿此行,不僅領略了當時西方的“勝境”,也看到了近代歐洲的先進技術。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3月18日初抵馬賽,他就做了關于火輪升降機、煤氣燈等有關機器的記載,其中對兒童自行車的描寫最有趣味。他說:
“肆售各物率奇創,有木馬,形長三尺許,兩耳有轉軸,人跨馬,手轉其耳,機關自動,即馳行不已。殆木牛流馬之遺意歟?”
三天后到了巴黎,他對自行車又做了一番描述。雖然幼稚樸拙,但他以自己的眼光和口吻,來介紹蒸汽時代的新產品,在近代文化史研究上自有其價值,也足以令統治階級深思自省。
在歐洲,斌椿曾多次乘坐火車游歷,故對火車也做了具體的介紹。他描寫火車行駛時的情況,以樸實的語言。真實的感覺,描繪出一種新奇感。且充分肯定了火車對便利交通上的作用。這對當時國內“一聞修造鐵路、電報”就“痛心疾首”的高官們是一個多大的啟示呀!
大數學家李善蘭曾慨嘆:在“中外限隔、例禁綦嚴”的社會里,“茍無使命,雖懷壯志,徒勞夢想耳!”如果他能夠得到同斌椿一樣的機會,那么他對文化的貢獻必然遠不止于此。
(責任編輯/韓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