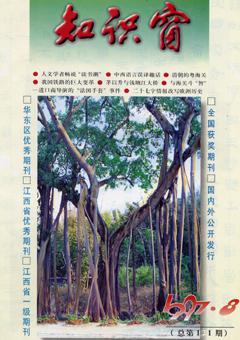清朝的粵海關
西 無
清廷開海設關
清初,清廷為了圍剿占據臺灣的鄭成功集團,對沿海人民采取了殘酷的“遷界”和“禁海”措施。所謂的“遷界”,即限令直隸(河北)沿海南下到廣東沿海一帶居民一律遷入距海岸線30—50里的地方居住;所謂的“禁海”,即嚴令不許船舶下海經商,有時連捕魚也不允許。這兩道命令重復頒布多次,并對違令者殺無赦。在給鄭氏集團造成經濟困難的同時,也給沿海商民極大的摧殘,使對外海上貿易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軍攻打臺灣。鄭氏集團向清軍投降。清廷終于消除了心頭大患,隨即允許沿海居民回遷,又開海弛禁。第二年,康熙帝為了盡快恢復海外貿易和加以有效管理,命令在廣州、廈門、寧波和云臺山(上海附近)設立四處海關,定下規則,收繳課稅。這四處海關又分別稱為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和江海關。一般來說,這是中國海關設立之始。
海關是對外通商口岸,既有中國的商民出海經商,也有外國的商船前來貿易。當時與中國發生貿易關系的,除了保持傳統朝貢貿易關系的東亞、東南亞各國之外,還有先后前來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西方國家。歐洲商船大多裝備槍炮彈藥。中國官員和中央朝廷對此很不高興,對他們總心存疑慮。
當時西方商人最需要中國的生絲、絲織品和茶葉、瓷器。這些商品主要產于江蘇、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從交通方便和降低運輸成本來看,四處通商口岸中最便利的依次是寧波、云臺山、廈門,最不方便的是廣州。更令外商頭痛的是,粵海關限制太嚴,行商壟斷弊端太多,有關官員敲詐太重,船鈔關稅信口添加。于是,外商不愿意在廣州通商交易。當時與中國貿易額最多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就牢騷滿腹,他們看中了寧波海關。寧波海關不僅離中國最好的生絲、絲綢和茶葉產地、集散地最近,而且關稅較輕,弊端較少。漸漸地。寧波周圍的外國商船多了起來。后來浙海關遷到定海,這更方便了中外商人。外國商人還在定海城外建起了“紅毛館”,以便居住和辦公。
這變化引起了廣東官員和乾隆皇帝的不安。外國商船都去寧波、廈門、云臺山做生意了,廣州市場蕭條肅然,船鈔關稅驟減,官員私囊也癟了。接著又出了一樁“洪仁輝事件”,從而使乾隆皇帝總以海防和防外為重的心懸了起來。
粵海關一口對外
洪仁輝是英國人,他的英國名字叫杰姆森·弗林特。由于漢語講得好,英國東印度公司讓他在貿易活動中充當翻譯。
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四月,洪仁輝領著一艘商船到達定海,船上有大量的銀錢和酒,還裝備了槍炮彈藥。浙江官府非常歡迎外商前來貿易。雙方協定卸下船上的炮位,就可開始買賣。浙江官員不僅派官兵護送英商去寧波,命令中國商人與外商公平交易.而且愿以優待政策放寬貿易。不久,又有一艘英國商船抵達。英商這一趟貿易量不大,但非常滿意。他們高興地發現:浙海關的稅收不及粵海關一半。
次年,洪仁輝又領著商船來到定海。浙江方面依然熱情地同他們公平交易。按規定,浙江的地方官向朝廷呈送了報告。
廣東方面也向乾隆遞呈報告,反映由于外商紛紛北上,導致廣州外貿蕭條的情況,要求朝廷決策。在廣東和浙江的報告中,廣東的報告引起了乾隆的重視,使他不僅想到的是粵海關的收入少了,更想到了防微杜漸,鞏固海防。乾隆發話:將來外國商船都跑到浙江去了,寧波不又成了一個洋人做買賣的地方嗎?搞得不好,會出問題。海濱要地,一定要多加注意。他一面派人去調查,看有沒有勾引外商來寧波的漢奸,一面采取措施讓外國人回到廣州去做買賣。
首先采取的措施是成倍增加浙海關的稅收,乾隆自稱這是“不禁之禁”,你外國人之所以來寧波,是因為浙海關稅輕,現在加重了,你該就不來了吧。
但是加稅并沒有擋住外商。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英國商船又來到定海停泊,要求貿易。乾隆皇帝這才意識到外商并不僅僅是因為浙海關稅輕才來寧波的。于是,他干脆下令:禁止英國商船再來寧波。今后凡歐洲商人只限定在廣州一口通商。
乾隆把原因說得很清楚:一是為了廣東沿海依靠洋船生意謀生的居民,二是廣州虎門、黃埔到處都有官兵防衛,三是對江西和廣東有關的人民也有利,四是浙江的海防有保障。
從此,粵海關便成了中國唯一對西方商人提供貿易口岸的管理機構,廣州也因此成了中國最大的通商港口。其他三處海關對東南亞各國開放。英國人對此很不服氣,也很不理解,曾在1793年和1816年兩次派遣使團到北京,要求開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和允許自由貿易,都被乾隆和嘉慶皇帝以不同的方式拒絕。
粵海關利弊雙生
粵海關關系到海防和對西方的貿易,是個肥缺,所以不少官員眼紅此差,朝廷也很重視選派官員。清代各海關的長官叫“監督”,由皇帝從各部資深官員中選任,但實際上多由管理宮廷事務的內務府和戶部中的滿族官員派充,以至于外商稱粵海關的長官就叫“戶部”,英語發音是“Hoppo”。有時又由督撫或將軍兼任。粵海關是最重要的一關,常以朝廷派來的官員專任監督。監督任期一般為三年。
海關設置,原為的是管理外貿船舶、檢查進出商貨、執行國家稅則、征收船鈔關稅。歷史地看待粵海關。也確實做了這方面的工作。自設立海關以來,對外貿易有了一定的發展;自確立廣州一口對西方通商制度以來,廣州的關稅上升很快。1757—1761年的五年里,關稅征收1846155兩白銀;1802—1806年則征收8178153兩。年平均高達163萬多兩,由此推算的貿易總值年平均在3300萬兩左右。此后,貿易總值基本呈上升狀態,幾次超過5000萬兩。
從康熙設關開始,粵海關日漸生發弊端,弊端不在海關本身。而在海關管理制度上。這種制度導致海關官員權力極大,專權之下,必生腐敗。
海關監督是大權獨攬的官位,他的副手叫“筆帖式”,也有實權。海關辦事人員來自兩個渠道,一個是海關監督上任時帶來占住各處要津的家人、親信,也稱“委員”,粵海關監督上任時可帶60個這樣的家人親信,真可謂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另一個是由地方推薦的稅吏、巡役,約有三四百人之多。海關在管理外貿中是不能直接經營外貿的,管理者兼事經營必然產生弊端而破壞管理。就在廣州一口貿易制度確立后不久,粵海關與經營外貿的行商達成了交易,由行商負責并壟斷所有的對外貿易,其他商人(又稱散商)不能直接經營。這便是有名的“公行”制度。“公行”俗稱“十三行”,“十三行”并不是只有十三家行商,多時有二三十家行商并立廣州口岸,少時只有幾家。
行商要想人公行,就必須得到粵海關監督的同意。這筆領取“執照”的賄賂一般是20萬兩白銀。除此之外,行商還得經常應付海關官員的勒索,每當廣州有什么公共建筑開工,全國各地發生旱災水澇,行商們就心驚肉跳,捐款的通知馬上就到,數目不小,多在10萬以上,而其中大部分捐款落人官員之私囊。至于官員們家里的紅白喜事、生兒育女、生日升遷,行商都必須送禮。這些禮金數目對內地人來說,不亞于天文數字。行商能如此對粵海關官員行賄,反映了壟斷對外貿易的賺頭巨大。再者行商們的生活極其奢侈,一年不賺百萬兩白銀,是應付不過來的。行商中的大多數都因欠外商的巨債而破產,有的自殺,有的判刑,少數行商壽終正寢時手頭還有幾千萬兩銀子的遺產。
接受行商的賄賂,勒索行商的錢財。是粵海關弊端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勒索外商。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向乾隆提出的六條要求中有一條就是請中央朝廷明令關稅的稅額。因為外商始終弄不清中國的船鈔關稅到底有幾類,要多少。他們覺得海關關稅總有一個數字,但是七算八算,必須繳交的數字大大增加,膨脹了一倍兩倍。如果能夠給有關官員和監督大人一定數目的賄賂,那又好辦一些,不僅船鈔關稅可以減少,檢查刁難也少多了。他們悟出了在中國經商的訣竅:沒有錢辦不了的事。
乾隆曾派員審查粵海關稅則情況,果然發現在船鈔關稅之外,又獨創了多種規禮收費:外商船只進口,從官禮銀起,到書吏、家人、通事、頭役止,規禮、火足、開艙、押船、丈量、貼寫、小包等等,共30項;放關出口,書吏、家人等驗艙、放關、領牌、押船、貼寫小包等等,共38項。真可謂是頭緒紛繁,項目冗雜,勒索受賄,雞犬有份。但朝廷對此并沒有作嚴肅認真的處理。一陣風過后,反是愈演愈烈,越收越多。實際上,朝廷有關官員,特別是與委派海關監督和對外貿易有關的部府,都會得到粵海關送來的厚禮與好處。皇帝也同樣從中獲益,只是名目不同,叫“進貢”或“貢獻”,名正言順,反貪官也不會反到這份上來。
無論是中國商人,還是外國商人,都意識到粵海關是“沒有錢辦不成事”的衙門時,海關的性質就已經發生了變化了,它不僅不能成為國家的門戶,反而成了社會的蠢蟲,最終給國家帶來危害。道光初年愈演愈烈的鴉片走私之所以猖獗,正是中外走私毒販用錢(或用鴉片)開路的結果,粵海關的大小官吏及其屬下巡役大多因貪其利參與或放縱鴉片走私。
(責任編輯孫開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