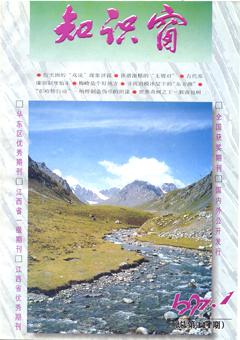古代養(yǎng)廉銀制度始末
王福田
所謂養(yǎng)廉銀,就是于正俸(常俸)之外按品級給官員們(主要是地方官員)一定數(shù)量的工作、生活補貼銀兩,以使他們具有合乎自己身份的經(jīng)濟力量,從而保持廉潔奉公,杜絕貪污受賄、營私枉法等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宋時代,出現(xiàn)過給官員養(yǎng)廉銀的做法,只是時斷時續(xù)沒有固定化、制度化,隨著歲月變遷、朝代更迭,一直到清代雍正朝才形成制度,成為地方各級在職官員的一項基本固定的、大宗的收入。
菲薄的官俸
明清以來官俸是按年度依品級高低不等頒給的,其俸菲薄。據(jù)資料記載,清代的封疆大吏、堂堂的一品總督,年俸不過一百八十兩銀子,而“親民”的父母官、七品知縣的官俸折合每月只有三兩七錢銀子。這就有些荒唐了。僅靠這么點官俸,官員們恐怕連養(yǎng)家糊口都難以維持,更談不上用于名目繁雜的各種龐大開支。
最基層的地方官知縣是“一縣之主”,掌全縣的政令,所轄縣地方的賦役、訴訟、文教諸事,都由他親自辦理,所以稱為“親民之官”。如此繁巨的工作。對某個人來說,無論從知識、能力、經(jīng)驗各方面來看。都不可能完全具備并獨立承擔完成。所以,地方官員上任伊始,一般都要延聘一至數(shù)名熟悉地方事務富有專門經(jīng)驗的“幕僚”來輔佐軍政要務或?qū)B氜k理文牘、司法甚至錢糧事項,越是高級官員,幕僚人數(shù)就越多。
與現(xiàn)代不同的是,清代皇帝只管官員的任命,卻不管他們的“辦公室”編制和工作班子的安排。從理論上講,上任官員聘請師爺?shù)馁M用是需要自己掏腰包的。為了使師爺同心同德、盡力任事,付給的薪酬還不能過于苛刻。據(jù)史料記載,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張集馨奉旨補授四川按察使(臬司)時,請師爺三名,每人年束修都在千兩白銀以上。臬司是一省的司法長官,正三品。年俸一百三十兩。這么點官俸只怕連請師爺費用的零頭也不夠。
對州縣官來說,延聘師爺?shù)馁M用還不是最大的;更大而尤顯重要的一筆開支是送“規(guī)禮”。清代賦稅的大宗是地丁錢糧,由州縣官催收后解送國庫(藩庫),他們的上司并不直接經(jīng)手錢糧,但上司主官對屬下官員有考核、參劾的特權(quán)。清代官員的考核,外官名“大計”,京官稱“京察”,考核的形式和內(nèi)容非常繁瑣、復雜,但核心是上司評斷屬下。另外,各省長官(督撫布按等)還有隨時參劾下屬官員的權(quán)力。如此近于獨裁的考核、糾參,不可避免地會造成下級對上司唯命是從、巴結(jié)打點。這就是“規(guī)禮”的由來。“規(guī)禮”是地方官中的下屬對上司饋送的禮金。“規(guī)禮”名堂很多,像三節(jié)兩壽(春節(jié)、端午節(jié)、中秋節(jié),上司和上司太太壽誕)要送相當數(shù)量的節(jié)禮、壽禮。其他無固定的各類饋贈更是多不勝舉。總之,不拿銀子當燈籠,那你的仕途就是漆黑一團。
至于生活上、工作上的額外支出也是一筆龐大的開銷。
作官要有官派,要遵崇朝廷的體制。出外必須騎馬坐轎、差身鳴鑼清道;起居則須下人端茶送水、前后侍候。這都要大把銀子來支撐。如果僅靠那么菲薄的一點官俸,官員們真得“枵腹辦公”了,那不顯得太滑稽了嗎?
千里作官只為錢
過去有句口頭禪,叫“千里作官只為錢”。這句話一針見血地挑明了封建社會作官賺錢是根本目的。
清代雍正朝以前地方官貪污的途徑很多,以州縣官來說,大體上分為名義上屬于非法和半合法兩類。像“虧空錢糧”(將征收的稅銀欺吞或挪用,從而虧欠國帑),訴訟收賄,利用職務之便納賄等,這些都屬于非法所得。國家對這類犯罪有明文的刑罰。像“耗羨私征”就屬于公開的、具有半合法性質(zhì)的收入。
耗羨,又稱羨余,是清代的一種附加稅。以補償征稅手續(xù)費、雜費及保管解運過程中的損耗所加征的若干錢糧。羨余中火耗所占比例最大。州縣官從百姓(納稅人)那里征收的地丁錢糧大都是成色不等的細碎銀子,而提解到藩庫的必須是重量相等、成色一致的銀錠。如此,州縣官就要將征收的碎銀重新熔鑄,熔鑄過程的損耗就是火耗。由納稅人承擔。這就為州縣官貪污中飽提供了一個機會。
由于各地沒有也不可能規(guī)定一個統(tǒng)一的火耗率,由火耗所得的銀錢上級也不過問,所以有些“不恤民命”的貪官污吏往往恣意提高火耗,橫征暴斂,籍此魚肉百姓。康熙末年魯豫一帶,火耗高達正稅的八成左右,幾乎使百姓完納的賦稅翻了一倍。
雍正朝以前.耗羨都是由州縣官私征私用。是州縣官特有的、相對固定的大宗收入(其中相當一部分要孝敬上司)。
過去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封建社會作官決不會成為賠錢買賣,由耗羨私征可見一斑。
養(yǎng)廉銀制度的出籠
清代康熙朝后期,官吏貪污,錢糧短缺,國庫空虛的情況愈演愈烈,而百姓抗糧欠稅已經(jīng)逐漸演化成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
繼康熙以后的雍正皇帝,是一個處事雷厲風行,敢于興利除弊,很有作為的封建政治家。雍正即位之初,就把清理財政、清查賦稅放在特別重要的地位。在清查錢糧虧空,打擊貪官污吏,充盈國庫的同時,經(jīng)過反復醞釀和精心策劃,雍正又實行了前所未有的耗羨歸公政策。這項政策規(guī)定州縣官在征收地丁錢糧正稅的同時。按一定比率征收耗羨(一般為10~20%),并隨正稅全部提解到藩庫。
耗羨歸公,首先保證了國家賦稅足額入庫;其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州縣官橫征暴斂、侵蝕國帑、貪贓營私等種種弊端,為澄清吏治打下良好的基礎(chǔ)。
耗羨歸公,等于斷絕了地方官的財路,若不給他們另辟財源,無異會導致新的貪污或變相貪污。養(yǎng)廉銀制度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出籠的。
按雍正的規(guī)劃,耗羨歸公后,“恐各官競以養(yǎng)廉,以致苛索于百姓,故于耗羨中酌定數(shù)目,以為日常之資”。就是讓各省從征收的耗羨銀中提取一部分,發(fā)給從總督巡撫到知縣巡檢各級官員一定數(shù)量的銀兩,作為補貼。養(yǎng)廉銀的數(shù)目主要視官職高低來確定。隨著耗羨逐年積累,各官的養(yǎng)廉銀也在不斷增加,直至雍正十二年前后才基本固定下來,一般不再變化。雍正以后的歷朝都相沿執(zhí)行這種做法,發(fā)給的對象和數(shù)目都沒有什么變化,以此成為制度。
權(quán)宜之計
實行養(yǎng)廉銀制度以后,地方各級官員正當收入相當可觀。高級官吏(督撫布按等)的養(yǎng)廉銀數(shù)目最高的竟達到其官俸的一百多倍,州縣官雖然少一些,但最起碼也是其官俸的一二十倍。州縣官養(yǎng)廉銀之所以相對少一些,主要原因在于雍正大力犁剔“規(guī)禮”,大大減輕了他們的經(jīng)濟負擔。
養(yǎng)廉銀制度只是一種權(quán)宜之計,只能用一時,不能保一世。雍正以后的乾隆朝,隨著國家財政狀況日趨好轉(zhuǎn),國庫充盈,對地方官稽查、監(jiān)察的力度減弱,貪污及變相貪污等封建制度的痼疾又發(fā)作得越來越重。
(責任編輯/楊劍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