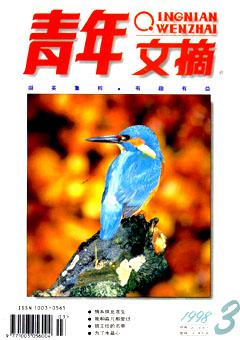不朽的畫中情人
劉雪璣
這是一段珍藏了35年的愛情往事,這是一位傣族姑娘心中永遠的小夜曲,這也是旅美畫家丁紹光首次向媒體披露的私人秘密。當您讀完這篇娓娓道來的故事后就會明白,是什么構成了一個畫家生命中不朽的畫魂……
丁紹光,一位在國內不大出名的國畫家,1980年旅美后,竟然用以不變應萬變的女性形象,以其非傳統的明媚艷畫,幾度佇立于在世中國畫家畫價之首。
1997年7月,97上海首次世界性藝術節博覽會后、記者們圍住丁紹光,一一提問。丁紹光是個高大的北方漢子,談話直率而熱情,眼中閃動著灼灼神采。可是,當提及丁紹光曾在云南呆過18年,曾走近過最美的水傣姑娘時丁紹光的眼神突然縹緲起來,縹緲中涌動出一泓濃濃的詩意……
循著這濃濃的詩意,筆者再次拜訪了丁紹光,并有幸見到了丁紹光從不示人的一封信,這封信,曾在丁的身上珍藏了許多日子,可信中的故事,卻在丁紹光的心里珍藏了35年之久……“盼天盼地,盼星星盼月亮,終于盼到了一點亮光;先生,我這一輩子,無法來看望您、照顧您了。多少次做過一千次一萬種的夢都離不開您。”這娟秀的字跡出自于位傣族姑娘之手。
一陣沉默之后,丁紹光首次向記者娓娓述說了生命中的這個故事。
35年前,也就是1962年初春,那時正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學習的丁紹光即將畢業。為了完成一幅優秀的畢業作品,他與當時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副院長張仃一同背上簡單的行囊踏進了西雙版納,踏進了一個名叫橄欖枧的小村莊。沒多久,便遇上了枧里過節。按照當地風俗,在這天,待字閨中的姑娘們盛裝端坐路邊出售噴香的吃食。小伙子們紛紛向各自中意的姑娘購買吃食以示愛意,而此時的姑娘們一個個儼然無冕之王:如果不中意求愛者,就向他索要高價放入面前的錢盤中,落選的小伙子付了巨款后自會怏怏離去;姑娘如中意求愛者,則將一張早已準備好的小凳含情脈脈地遞過去,當即對面坐著談情說愛。
那天,滿懷好奇的丁紹光走進人群,發現有一處地方蠟燭般插滿了小伙子。他不由探首進去張望,頓覺滿目生輝:原來人堆里圍著的是橄欖枧的三大美女,而中央端坐的就是水傣中最美的姑娘刀玉娟。“這個傣族姑娘真是可愛啊!”丁紹光不禁在心中贊嘆道。
當年輕的丁紹光睜大雙眼,吃驚地看著刀玉娟面前的小山般堆滿錢財的盤子時,那年方二八的刀姑娘莞爾一笑,居然伸手將小板凳遞給了他!22歲的丁紹光哪里知道其中的奧秘,他還以為這不過是傣族人出于對一位漢人的禮貌而已,遂堂而皇之地接凳坐下,繼而大嚼起玉娟送上的肥雞腿與花生米來。
事后,丁紹光全身心地投入到繪畫中,很快便忘了此事,他沒和刀玉娟講過一句話。然而,從此后刀玉娟的身影就常出現在丁紹光的寫生點,而且每次她都是一聲不吭地站在丁紹光的背后,默默地看他作畫。時間長了,丁紹光不禁問:“你喜歡我的畫嗎?”她搖搖頭;丁紹光又問:“那你為什么總跟著我?”她用并不太熟練的漢語說:“因為你坐了我的小板凳……”
不久,丁紹光接到了一封信:“先生:我做您永遠的朋友,但我不敢正視您,唯有注視著您的一言一行,把您的影子全部錄在心里,但是我沒有勇氣向您表白,我的心為青春的愛而跳動……玉娟”
這封信是玉娟寫的,一個剛上中學的傣族姑娘竟能寫出這樣流暢的漢語,丁紹光很是佩服。信中火熱的愛情更讓他年輕的心怦怦直跳。
然而丁紹光卻不敢貿然接受刀玉娟的愛情。所以,當他收到這封信后,只是心存感激地把它收藏了起來,并沒有給刀玉娟任何形式的回應。他渴望的是一種純潔而永恒的愛情。然而,刀玉娟仍執著地跟隨著他,無論他到什么偏僻的山里去作畫。
半年后,丁紹光要啟程返校了。5月的西雙版納,已進入雨季。綿綿細雨淋濕了蒼山翠嶺,也淋濕了玉娟的心,那天,多情的玉娟支走了與丁紹光隨行的翻譯,終于鼓起勇氣,向丁紹光傾訴了衷腸,痛哭著將丁紹光從橄欖枧一直送到景洪縣城。一百多里的山路,一步滴淚,從清晨步行到天黑。
在寶石藍夜幕下,在天堂般靜謐的雨夜里,看著哭成了淚人的玉娟,丁紹光陡然一陣心痛。他此時才發現,自己早已深愛上了這位情深義長的傣族姑娘,這甜蜜而憂傷的分別令他為之顫栗不已。
丁紹光回北京后,面臨著畢業分配。副院長張仃希望這個高徒留在北京,幫他完成一個民間藝術項目。在當時,這是多少畢業生夢寐以求的,可丁紹光在6個志愿欄里一口氣連填了6個心形的“西雙版納”——為了那個永遠心痛的雨夜——可惜,直到今天,玉娟無從知曉曾有過6個心形的“西雙版納”,因為當時丁紹光被命運之手推到了昆明的云南藝術學院任教。
丁紹光剛進云南藝術學院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由于丁紹光的父親曾在國民黨政府中任職,他成了主要挨整對象。年輕的丁紹光被擊蒙了,他擔心自己出身不好,如果再去找玉娟,會影響她今后的幸福生活。因此,玉娟寫給他的無數封情書都被他鎖在了柜子里,一封也沒回。
恰如丁紹光所擔心的,1966年至1967年一年時間里,丁紹光被禁止作畫,連見朋友都十分困難,那段日子他盡力回避與外界的一切聯系,唯恐給任何人帶去麻煩。
玉娟給丁紹光的無數情書石沉大海。3年半后,當丁紹光終于設法重返西雙版納渴望續夢時,傷心絕望的玉娟擋不住追者如云的無窮壓力,剛剛嫁了人。面對風塵仆仆而來的心上人,玉娟追悔莫及,哭成了淚人。后來她給丁紹光寫了一封長長的信:“(你)確實是我崇拜的人,愛是不能忘記的,我玉娟崇拜一個人,是終生忘不了的……”
10年后,文革結束。未能忘情的丁紹光又一次踏進西雙版納的景洪,尋找玉娟。當他經過無數波折、突然出現在農村供銷社柜臺里當營業員的玉娟面前時,驚訝萬分的刀玉娟旋即用雙手擋住了憔悴、蒼老的臉,死也不肯松開,并苦苦哀求丁紹光別再瞧她,丁紹光難以置信地望著眼前的玉娟,望著她那粗糙無比的兩手和雙足,驀然發現昔日那顆秀色奪目的初綻豆蔻,由于憂傷、生育、內外操勞(傣家風俗,男人不做事),以及多年的站柜臺,早已站成了一株枯萎的樹。
丁紹光仰天長嘯,連連揮動手中的畫筆,拋出萬縷線條。他要用它縛住那個難忘的雨夜,縛住那天堂般的靜謐,縛住那難再的美……
此生此世,他與她僅僅用晶瑩透明的凝視繾綣過一首詩,可那個晶瑩透明的傣族姑娘玉娟,卻永遠成了他創作的源泉,成了他無數作品中永遠的詩魂……
從此,女性成了丁紹光畫中的永恒主題,而且,他作畫時最愛用的色彩就是寶石藍和太陽金,藍是寧靜與深遠,金是激情和活力。他更偏愛在萬籟俱寂的雨夜揮毫作畫,那時,一股股創作激情就在他的胸中噴涌,一幅幅獨具特色的圖畫就從筆下誕生。
也正是丁紹光這獨具特色的畫,使他奇遇了現在的愛妻張達喜。張達喜是四川音樂學院的學生,“三代紅”出身,是當地的紅衛兵大隊長。1969年夏天,張達喜的老師去云南出差,偶然看到了丁紹光創作的一幅美人圖,他當時十分驚訝,連忙問丁紹光,是怎么把他的學生張達喜的畫像弄到了云南的。丁紹光笑著告訴他,自己從未見過張達喜,畫中的姑娘完全是心中噴涌而成。
不過,這一件奇事倒引起了丁紹光莫大的興趣,他設法趕往成都,想親眼看看那個叫張達喜的姑娘是否真的和自己畫中的人相似,結果,兩人竟一見鐘情,相識3天后便定下了婚事。
張達喜的父母知道后,顧忌丁紹光的出身不好,不太同意這門親事。可丁紹光當即為張父的工廠畫了,幅7米高的《毛主席去安源》,而且不用別人搭支架相助,開筆先從眼睛畫起,把眾人給看呆了。張家頗有發言權的老祖母發言了:“看把咱毛主席的臉畫得多像啊,鐵飯碗、鐵飯碗!”就此一錘定音,丁紹光夢境般地娶到了一個美貌的“畫中人”。這也是上天賜予他的一個絕色模特……1970年,他們結婚后張達喜又作為模特成全了丈夫許多佳作。
1980年,丁紹光終于和居住臺灣的母親與已到美國的妹妹接上了音訊。為了進一步汲取西方藝術的精華,提高畫技,丁紹光去了美國。在那里,他很快和洛杉磯的華人打成一片,通過自己不懈的努力,在南加州參加了兩個畫展,其中包括“馬丁·路德·金畫展”,取得了兩次第一名,從此他的畫風開始被人們接受。1984年,丁紹光在美國購置了房子,把妻子和兩個孩子從國內接到了美國。
此后,丁紹光獨具特色的畫業一發而不可收拾,通過近十年的艱辛努力,他從中國畫壇一步步走向了世界藝術殿堂。然而當他事業如日中天時,一個不解的中國情結卻在他心里越繞越緊了,他常想起當年那位給了他創作激情和靈感的傣族姑娘玉娟。他已和玉娟中斷聯系20多年了,那份曾經憂傷的戀情早已被歲月醞釀成了濃濃的友情,他常在心底問:玉娟,你在遠方還好嗎?
(劉衛東摘自1997年11月《知音·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