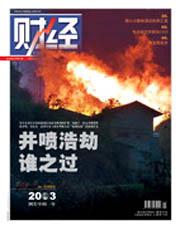揭開騙匯網
沈小雨
本刊1998年11月號刊發“為了70億美元的持久戰”一文提到,去年全國騙匯金額可能超過70億美元。這確實是個驚人的數字。在這70億美元背后,存在著更驚人的騙匯機制,犯罪分子甚至將海關和銀行都織進了他們的犯罪工具網中。
為確保國家的外匯儲備實力,徹底摧毀編織在進出口各個環節上的竊匯網,是國家此番嚴厲打擊騙匯的最終目的之一。
假關單:保稅區監管出現漏洞
1998年8月23日,在海南某海關,4張標注進口商品為“還原型輔酶”的報關單引起了全國外匯大檢查專案組的懷疑,因為如此貴重的商品(價格比海洛因還貴)在海關總署竟查不到報關存檔數據。
當天下午,專案組在該海關查出該關簽發的進口“還原型輔酶”報關單材料共19張,總金額將近1.4億美元。經仔細核查,這些關單雖為正本關單,但商品進關時海關均未做商檢,這足以對進口商品的真實性提出懷疑。
調查結果是所謂的進口“還原型輔酶”根本子虛烏有,進口方居然只是借用了一下貨物的名稱,該海關關長王某便給他們上了一個正正規規的進口“戶口”。
“還原型輔酶”的部分假關單曾落入三亞個體企業昌恒公司。1998 年4月,昌恒公司偽造了市對外經濟開發公司公章,帶著上好的正式“戶口”,堂而皇之地到海南某市外匯管理局申請“進口付匯備案表”。外管局認為其中有疑點,便將這伙人送來的商品標注為“還原型輔酶”的報關單送海關做二次核對;此后,又決定請該海關配合,自己派人再去查驗貨物。此舉遭到了海關的拒絕,據稱,這批貨物已經被置入保稅倉庫,而按規定外管局無權查海關監管的保稅倉貨物。
該市外管局只得照章簽發了“進口付匯備案表”。憑著這份蓋有官印的文件,昌恒公司陳、劉等人忙不迭從銀行騙匯684萬美元,很快便將這筆錢直接匯到了香港銀行。
此案涉案主要嫌疑人某海關關長王某之所以敢只手遮天,既出于貪欲,也確實看準了進口付匯管理制度存有某種“真空區”。
我國外匯管理的關門由海關和外匯管理兩個體系交織而成,交叉點便在付匯核銷這一環節上。國家外匯管理局規定,去外管局核銷時,進口企業須出示正本進口貨物報關單等有關材料,填寫核銷單。核銷單即用以辦理進口付匯的憑證。外管局和售匯行對有疑點的單證應進行重點核查,并可按照有關規定,隨時向報關單簽發地海關進行“二次核對”。
依照此規定,關長王某該是無權拒絕外管局的驗貨請求了。但按海關總署的《進出上海外高橋保稅區貨物、運輸工具和個人攜帶物品管理辦法》和《保稅倉庫及所存貨物管理辦法》等規定,任何被置入保稅區或保稅倉庫的貨物,只接受海關獨家監管。因此,如果假關單由海關內部的蛀蟲親手操辦,一旦購匯時受到懷疑,又可借保稅倉庫躲過外管系統的核查。
1998年10月6日,海南某海關關長王某已交由公安機關刑事拘留。10月16日,王某被移至海南省反貪局審訊。初步調查表明,由于王某以該海關簽發正本報關單,致使售匯銀行做出二次核對屬實后向騙購匯企業售匯,現已查實的已達7368萬美元。
洗票:特殊名義從何而來
騙購匯的不法分子去海關“上戶口”,目的是憑假關單從售匯行購得掛牌價外匯,然后再以高于牌價的價格賣給真正的購匯企業,或以各種名目從中吃一塊差價獲利。
從事代人騙購匯的企業,一有進出口權的“特長”,二有搞到假關單的“絕招”。于是,一些沒有進出口權卻又想搞到外匯的企業,便出高價委托這些有“特長”又有“絕招”的企業去騙匯。
代購匯企業一般并不用自己的人民幣來購買騙來的外匯,而購匯家為逃避審查,也不敢公然出面,只通過幾道轉賬洗票,讓自己的影子從賬面上完全消失。洗票要洗去的就是用于購匯的人民幣來源,洗去不合法購匯的身份。
例如,在上述案件的調查中,當查到進口方去銀行購匯的環節時,卻出現了一個巨大的“頓號”。從報關單上看,身為海南某市屬公司的進口方,其進口金額共有1億多美元之巨。但該市僅有一家售匯行在售出美元時與海關核對過“還原型輔酶”的進口關單,金額為684萬美元;這也是那19張關單中惟一一張在某市發生購匯行為的關單。
專案組意識到,線索斷處肯定藏有大案。通過全國性協查,很快便查出了還有10張關單已在上海、天津購匯時被核對過,涉及的金額占進口總額的54%。這使案情又獲重大突破,順滕摸出了此次“洗票”的全過程。
1998年9月4日,公安機關查封了上海的4家騙匯企業,僅這4家企業騙匯金額就達1.18億美元。其作案過程是先由廣東方面人持廣東地區銀行匯票,通過上海當地人,在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和工商銀行上海分行兌換成當地本票,再轉匯到騙匯企業在上海地區其它銀行開立的賬戶。然后以上海公司的名義,以預付貨款或貨到付款方式,并以特殊用匯名義購匯。從提供人民幣資金到購匯,不法分子最少“洗票”5次,最多10次,然后將騙購得的外匯全部匯往香港。
不法分子就是這樣,把代表著中國國門的關單當支票,再把用于購匯的人民幣三洗兩涮,便使國家大量的外匯儲備流出海外。
付匯:經常項與資本項較量
有人說,我國一直對騙匯行為的處罰過輕,才導致騙匯泛濫。其實僅僅從理論上計算,騙匯處罰實在不算“過輕”。依照我國1985年發布的有關外匯管理的處罰規定,對騙匯行為的處罰可罰沒所騙匯額,還可處以騙匯額10%~50%的罰款。若將海南某海關“還原型輔酶”的騙匯額按1.4億美元計,罰款額按30%計,代理騙匯的進出口公司從中僅能獲利1%~5%左右,風險遠遠大于收益。
記者曾私下詢問有過騙匯行為的企業,為何肯為蠅頭小利去搏風險,回答竟是因為“干這行沒風險”。原來,他們除了和海關里的蠹蟲進行交易公然違規之外,還和銀行的人員相互勾結,或采用規避銀行管理的手段,達到其最終目的。據人民日報報道,最近曝光的云浮騙匯案嫌疑人莊某某,向記者坦陳:“不跟銀行一起搞,哪有這么順利!”
1998年8月22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向北京市公安局移交了中國人福新技術開發中心涉嫌騙匯的線索。人福中心于1997年9月至1998年2月,利用102張偽造的海關報關單申報核銷,總計6092萬美元。公安部門根據這一線索展開偵破工作。
經對人福中心進出口三部的賬目進行審查,發現自1997年9月至1998年5月,僅該部就涉嫌用152張偽造的報關單騙購得1.3億美元外匯。
8月25日,該部業務員譚康、葉林、王濤等交待,人福中心進出口三部由王建軍、石小軍等承包,以做中關村電腦進出口代理為名騙購國家外匯。北京已有40余家公司向人福中心賬戶打入人民幣10.8億元用以購匯。人福中心則利用假關單到開戶銀行進行購付匯業務,然后付匯到委托他們購匯的公司所指定的境外賬戶上去,從中牟取暴利。
人福中心之所以敢大肆騙匯,是因為他們在銀行有“內工”,每次都由某銀行職員靳紅衛、李小風二人直接經手,為其進行銀行匯兌。
銀行某些制度中的脫節,也成為了犯罪分子的第二道保護傘。按照有關規定,在付匯業務中,銀行對一次購匯在50萬美元以上的報關單,也須拿到海關進行核對。但凡一次關單金額超過50萬美元或有疑問的關單,均應先付匯,再向關單簽發機構核查真實性。
這顯然給不法分子帶來了可乘之機:通過銀行環節核查,發現問題的只能事后懲罰,而此時外匯早以付出,逃套匯行為無法事先得到控制。另外,按照國際慣例,銀行對單據的真偽是免責的,只審查表面上的一致性,這也給熟悉銀行業務的靳紅衛、李小風提供了可乘之機。
在經常項目下人民幣有條件可兌換的進口付匯中,銀行才是我國進口付匯的國門。尤其是貨到匯款項下的進口付匯,是直接在銀行核銷,而大量的騙購匯都是采用這種結算方式的。
記者在結束采訪時獲悉,外匯管理部門將努力在1998年內實現海關、銀行與外匯管理部門之間的電腦聯網,從而實現貨物進出關境與外匯資金流出入數據的同步傳輸與核對。
人們正在期待,有了方方面面人力與政策的配合,再加上先進的技術管理手段,穿過所有管理漏洞織就的那張竊匯網終會被搗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