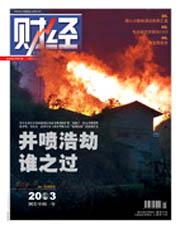天使之死
勞倫斯·瓦特金先生每次閉上眼睛就仿佛看見小女兒穿著滾軸冰鞋嫻熟地在家門口玩耍:“她可以整小時整小時地溜冰,她對所喜歡的一切事情都充滿著激情,她的人生就是這樣的。”
3月8日晚上9時許,愛梅——瓦特金先生的小女兒,紐約一個貧民區深受人們喜愛的社工,在她的公寓附近,也是她工作的地區,一個幽靜的小街口,被人殺死了。她倒下去的時候,只來得及喊一聲“救命”。一把巨大的廚房用刀從背后戳進去,幾乎洞穿了整個上身。
這個身材纖細面容姣好的女孩子,酷愛音樂和繪畫,有著一頭暗紅色的卷發,帶著她那永遠發自內心的歡笑。她來自堪薩斯大學,現在是亨特社會工作學院的“優秀碩士生”(這個名稱意味著以優等成績提前一年畢業),她選擇了到紐約最貧窮也是最危險的地區的社會工作者中心當一名實習社工。她在這里負責幫助受虐待的婦女獲得新的生活。
這個世界上許多人關注著社會正義,僅僅是“關注”而已。愛梅則為正義獻出了生命。在愛梅留下的空空的辦公桌的上方,貼著一條拉丁文口號:“No Mas Abuso (讓虐待少些吧)”。愛梅生前的男友(也是這個中心的社工)告訴記者:“她并不是無視這里的危險,她只是太忙于撒播新的生活,沒有時間去注意死亡。”愛梅的另一個男友,正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念書的勒那回憶說:“她是個無私的人,她對貧弱無助的人們充滿著奉獻的激情。所有的人都喜歡她……不,應當說,所有的人都熱愛她。她幫助那些受盡虐待的婦女,她保護那些流浪兒童,她輔導那些弱智和心理殘障者。”愛梅的朋友們都說:“愛梅所到之處總是可以找到美,或許因為她就是那個帶來美的人吧。”記者寫道:“不論何處,一切接觸過愛梅的人都被她的熱情感動。”熱愛她的人們在她倒下去的地方供了幾束黃玫瑰、一條紅色挽帶,還有三支蠟燭。有人努力要點著這些蠟燭,可是風總將它們吹滅。
這個地區的居民大多是加勒比人,生活貧困,工作艱辛,區內暴力叢生。愛梅在堪薩斯大學的同學們佩服她有勇氣到這里來定居。人們記得,去年10月由愛梅組織的“反對家庭暴力”燭光聚會,參加聚會的婦女達到200多人,這個數字真是她的奉獻精神和感召力的明證。那個在附近街上拉手風琴乞討的流浪漢回憶說,他還記得愛梅經常把零錢放到他面前地上的帽子里,并且總要說一句:“keep warm(別凍著)。” 據說兇手僅僅拿走了愛梅的錢包,僅僅是為了錢,不多的一些錢。流浪漢感慨:“其實愛梅會心甘情愿地把錢包拿給他的,因為她就是來幫助他這種人的。”
愛梅來自民風淳樸的堪薩斯附近的一個小鎮子。父親是老師,母親拉小提琴,熱愛園藝。在所有認得愛梅的人的記憶里,愛梅總在笑。同學們都記得愛梅多么熱切地想要改變這個世界,想要這個世界變得美好起來,尤其是想要幫助那些被社會遺忘的生活在社會邊緣的人們。愛梅在高中參加法語俱樂部、唱詩班、辯論和新聞學社,她還是校刊的攝影記者。“人與人幾乎總是擦肩而過,不留下任何印象,”她的一個高中同學指出,“愛梅不是這樣,她相信每一個人身上都可以找到美好的東西,需要的只是努力去找。”高中圖書館的老師回憶愛梅說:“她有最令人愉快的笑。當她朝你笑的時候,你立即就感到暖和起來。她天生有一種與人溝通的能力。”
瓦特金先生閉上眼睛繼續說:“有些人活得很長久卻從未真正生活過,愛梅只活了26歲,但她是真正做了一點事情的。我愿意放棄一切來換回她的生命……不過,我為她活過的生活感到自豪。”
天使死了,帶走了永恒的笑容,從她生活過的世界里。她來到這里,原本是要與他們分享笑容。出自她高貴心靈的召喚,她在他們中間生活。她簡樸,純潔,熱情,光彩四溢,溫暖了那棟即將坍塌的居民樓。天使被人殺死了。是生存的怨恨?還是潦倒的絕望?是被高貴反照出的邪惡靈魂?還是麻木心靈的無意識謀殺?我反復讀著來自紐約當天新聞的五份報道,端詳著那幾幅愛梅的照片。天使之死是一次人類心靈事件,它敲打著我們良知的封閉的門。
命運敲門的時候,人們不知道那是命運,于是注定了在沉淪中繼續沉淪。天使的悲劇就在于她將要被她所熱愛的人們殺死,非如此而無法喚醒“鐵屋”中的昏睡。
我們命定了的生存方式,便是不得不在物的世界中活下去,卻不斷想要拯救我們自己的心靈。事情往往是這樣的:隨著我們物欲的開發,隨著我們在世的成熟,我們便不斷地加重著心靈的遮蔽,將我們的童真遺忘。于是我們在沉淪中繼續要求著“沉淪”,在遺忘中追趕更深重的遺忘,在面向必死的路途上索性醉生于末世的燈紅酒綠之中。然而從濃睡殘酒里依舊有真摯的瞬間會涌現出來,讓人無端落淚仰天長嘯垂首沉思。心靈撞擊著軀體。白云悠悠,藍天浩蕩,大海滔滔。
回來吧,天使。回來吧,遠逝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