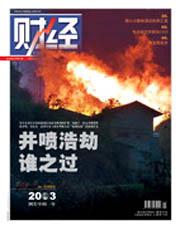信譽(yù)機(jī)制如何形成
在當(dāng)前中國(guó)向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的過(guò)程中,企業(yè)種種不重信譽(yù)的行為深深為人們所詬病,而如何建立起企業(yè)信譽(yù),又成了業(yè)界人士談?wù)撟疃嗟脑掝}之一。對(duì)經(jīng)濟(jì)學(xué)來(lái)講,關(guān)鍵是依靠什么制度,才能使大家更有積極性來(lái)建立好的信譽(yù)。
首先來(lái)看這樣一個(gè)例子,一方是企業(yè),另一方是投資者。企業(yè)可以有兩種選擇:第一種選擇是進(jìn)行欺騙,特別是在企業(yè)發(fā)行股票的時(shí)候進(jìn)行欺騙;第二種選擇是不欺騙。投資者也有兩種選擇:投資或不投資。假定企業(yè)選擇欺騙,投資者選擇投資,企業(yè)得到100的最大收益,而投資者損失20;如果企業(yè)不欺騙,投資者投資,企業(yè)得到60,投資者得到20;如果投資者不投資,無(wú)論企業(yè)誠(chéng)實(shí)也好,欺騙也好,雙方都沒(méi)收益。這實(shí)際上是一個(gè)博弈,結(jié)論是大家合作比不合作好。
問(wèn)題在于如果博弈只進(jìn)行一次,合作就不會(huì)出現(xiàn)。這是因?yàn)椋o定投資者愿意投資的話,企業(yè)的最優(yōu)選擇是欺騙! 為什么?它欺騙得到100,不欺騙得到20,所以欺騙比不欺騙好。
預(yù)期企業(yè)將選擇欺騙,投資者的最優(yōu)選擇是什么呢? 不投資! 所以在一次博弈的情況下,惟一的均衡就是企業(yè)欺騙、投資者不投資! 這就是“納什均衡”。
這是一個(gè)很重要的社會(huì)現(xiàn)象:每個(gè)人都為自己好,追求自己的理性選擇,而導(dǎo)致了集體的非理性。這就是所謂的“囚徒困境”,困就困在有好的結(jié)果,但無(wú)法達(dá)到。
“納什均衡”這個(gè)概念對(duì)設(shè)計(jì)制度來(lái)講是很重要的。一個(gè)制度是不是有效,能不能夠被執(zhí)行,那就要看你這個(gè)制度是不是一個(gè)“納什均衡”。一個(gè)國(guó)家也好,一個(gè)企業(yè)也好,在設(shè)計(jì)制度時(shí),領(lǐng)導(dǎo)人要首先想一想人們會(huì)不會(huì)自覺(jué)地遵守它。如果大家不會(huì)自覺(jué)地遵守這個(gè)制度,那么這個(gè)制度就很難存在下去。
那么,在什么情況下企業(yè)會(huì)特別看重信譽(yù)呢?
關(guān)鍵在于博弈是否可以重復(fù)許多次地進(jìn)行。比如投資人說(shuō):如果這次你沒(méi)有騙我,下次你賣(mài)我還買(mǎi);如果我受騙上當(dāng)了,那我永遠(yuǎn)也不買(mǎi)了。企業(yè)怎么選擇呢?如果企業(yè)選擇誠(chéng)實(shí),不欺騙人的話,就能獲得長(zhǎng)期的收益。如果企業(yè)選擇欺騙的話,只能獲得一次性收益。正是由于考慮了未來(lái),才重視聲譽(yù),不去欺騙。
這可以解釋好多現(xiàn)象。比如為什么政府部門(mén)、企業(yè)、學(xué)校,老是強(qiáng)調(diào)站好最后一班崗,因?yàn)樽詈笠话鄭徥亲顩](méi)有積極性站好的。個(gè)人只有對(duì)未來(lái)有信心,才會(huì)重視聲譽(yù)。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大企業(yè)更重視聲譽(yù)。博弈進(jìn)行的時(shí)候越長(zhǎng),人們就越有積極性去樹(shù)立好的聲譽(yù),不會(huì)欺騙。這也與信息的傳遞有關(guān),假如企業(yè)騙別人多次以后才能被發(fā)現(xiàn),企業(yè)就更有可能不注重聲譽(yù)。
由于信息不對(duì)稱(chēng),需要政府管制,但政府管制也常常導(dǎo)致企業(yè)不注意自己的聲譽(yù)。比如說(shuō),假如沒(méi)有政府對(duì)利率的管理,那么銀行搞得越好,信譽(yù)越高,吸收存款的成本就可以很低。但是假如政府把所有的利率都管起來(lái)了,那么銀行有沒(méi)有好的信譽(yù)還有什么關(guān)系呢? 反正所有人籌資成本都一樣,銀行就不會(huì)有積極性去注意自己的信譽(yù)了。
同樣,由于國(guó)家作最終的擔(dān)保,往往造成了銀行不顧及信譽(yù)。如果國(guó)家不再給銀行做擔(dān)保,儲(chǔ)戶就特小心了,就要琢磨是往建行存還是往工商銀行存,銀行就要注重信譽(yù)了。
中國(guó)人的文化傳統(tǒng)是言而有信的,但是現(xiàn)在不重視信譽(yù)了。為什么呢? 這源于我們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要想讓人講信譽(yù),首先必須做到讓他明天還存在,而國(guó)有企業(yè)的廠長(zhǎng)經(jīng)理對(duì)明天的位子是沒(méi)有把握的。企業(yè)家普遍感到位置不穩(wěn)。今后他是不是仍然在位,主要不是取決于他干得好壞。現(xiàn)在存在這樣的情況:企業(yè)干得越好,企業(yè)負(fù)責(zé)人越覺(jué)得職位不安全。為什么呢? 因?yàn)槠髽I(yè)干好了,上面還有另一個(gè)人要安排,而且你干得這么順當(dāng),困難這么少,他有可能把一個(gè)他更喜歡的人派來(lái)。正是由于國(guó)有企業(yè)的負(fù)責(zé)人不能確定他明天還在不在這個(gè)位子上,所以他就不會(huì)重視這個(gè)信譽(yù)。原因在于政府選人的時(shí)候不是按照他干得好壞來(lái)確定他去留的。
所以說(shuō),信譽(yù)機(jī)制在我們現(xiàn)實(shí)的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中還很難發(fā)揮作用。要解決這個(gè)問(wèn)題,最終還是要在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上下功夫。信譽(yù)機(jī)制存在的基礎(chǔ)是產(chǎn)權(quán)。當(dāng)幾十年前我們把地契燒掉的時(shí)候,我們燒掉的不僅是地主對(duì)土地的所有權(quán),還有中國(guó)人的道德觀。現(xiàn)在人們奇怪為什么“黃世仁”(債權(quán)人)害怕“楊白勞”(債務(wù)人)。其實(shí)一點(diǎn)也不奇怪。難道我們當(dāng)初鬧產(chǎn)權(quán)改革不就是為了讓“黃世仁”害怕“楊白勞”嗎?我們成功了,成功得讓我們現(xiàn)在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