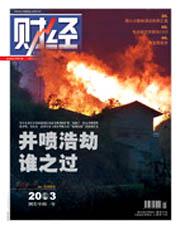西安:圓夢心情
不知為什么,許多國家的元首政要來了,第一站都要在西安落腳。秦俑、古城,都是老外眼中燦爛文明的余光。
看到西安還保存著的相當完整的城墻,他們就以為這是盛唐余澤了,其實這只是清代建筑,所圈住的面積只有當年的1/20。只有同西安的人打過交道,才明白這座被城墻圍起來的城市,處境正如這段城墻一樣不尷不尬。
為數不多的亮點,是在這里面生活的人們創造的。他們試圖讓自己過得更好的努力,給這個曾衰敗了千年的都市增加更多的生命的活力。
“有了錢再繼續我的夢想”
■李雪竹
(西安外事學院干部)
李雪竹屬于靠“死工資”吃飯的工薪一族,每月500多塊錢收入,于這個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而言,他認為剛剛解決溫飽而已。每談到“錢”這一話題,內心就有一種說不清的愧疚感,覺得有些對不住自己。
“ 其實靜下心來,倒常常喜歡用一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來求得安慰──朋友們說這是一種無奈的自我解脫,也算是吧!比起社會上那些下崗的人,我也知足了。”
但知足并不等于滿足。時有突發奇想:“如果有一天有了100萬,我會怎么辦?”
李雪竹還是告誡自己要真實地面對生活。他對社會上流行的“80年代靠膽,90年代靠錢”的順口溜很有些感慨,認為話雖露骨,但很實際。他常常用“我還年輕”來安慰和激勵自己,督促學習上進,爭取能在30歲左右成點氣候,并立志要吃“文學”這碗飯。
他的夢想是擁有一臺電腦寫作,買部比較專業的相機。幾年前剛走上社會那會兒,李雪竹曾和一群熱血青年朋友赤手空拳搞“青年志愿者愛心沙龍”,立志去幫助社會上那些“受苦受難”的弱者。“當時比較單純,自以為只要有人就行了。但最終還是因為錢的緣故偃旗息鼓了。
“這件事對我沖擊很大,將來如果有了錢,我仍將繼續我的夢想”。
置身于這個世紀末,李雪竹承認“的確還談不上有錢,最多算是一介窮苦書生而已。但我相信將來的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他覺得過去一年長大了不少,不再盲目,也不再沖動了。“如今年輕人都紛紛考研,我知道自己沒有那份恒心,也沒有時間。我更注重一種內在的東西,能力不是什么文憑能替代的。”
“蕭條的時期要把錢花完”
■任超
(西安協和企業集團董事長)
時下方方面面普遍感到掙錢越來越不容易。謹慎經營,壓縮投資,減少風險以渡過難關,似乎已成為企業界老板們的共識。然而,面對國內經濟呈蕭條之勢,任超斷言:“這正是企業擴大規模、擴大經營的大好時機。”
“作為企業家,萬不可以在這個貨幣最值錢的時候攢錢,而是要把錢花完。如果等到貨幣不值錢的時候,再想花錢,可能就花不著了。”任超如此這般判斷,如若并非語出驚人,顯然就是深思熟慮。
任老板的分析是,首先,現在物價走低,貨幣資金最值錢,可以少花錢多辦事。“企業家應當不失時機地將資金變為資產——若變成固定資產,一兩年后定會顯著增值;不能變為固定資產的,可以變為無形資產,因為社會資金短缺時,對無形資產的投資必將獲取更好的回報,并為下一次經濟高潮的到來打下基礎。”
其次,經濟蕭條的時候,市場幾乎全轉到了買方,購物可以極盡挑揀之能事,投資亦可精心選項。由于是買方市場,項目、規模可以一議再議,價位可以一壓再壓。可能一項投資完成,數年之后增值即十分可觀。“如果項目選得準,在將來高價位時出售產品,可能有意外的收獲。”
任超還認為現在是貸款的好機會,換句話說,“隨著下一步經濟高潮的到來,貨幣價值必將下降,將來付息還貸的實際價值只會有減無增。因此,企業經營者目前應該傾其所有抵押貸款,進行投資,這本身就是一個只賺不賠的生意。”
時勢造英雄,當今的任超屬于哪一路?
“停滯過后一定有活躍期”
■張斌峰
(陜西日報周末版記者)
干記者這行,收入不多,花費卻不小。每月六七百塊錢的工資,張斌峰除了吃飯,便所剩無幾了。
“還有許多根本無法節省的開支,如買幾件像樣的衣服,請朋友吃飯,因某種原因必須節省時間乘出租車的費用等等。一些老同學、老朋友還不時登門借貸,常常被緊張的經濟形勢壓得喘不過氣來。”說到這兒,張記者倒顯得格外坦率:“存折上的余額幾乎沒有突破過3000元。”
張斌峰把自己歸入“一個異地來的謀生者”的行列。剛來西安時,最大的渴望就是在這座古城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似乎那樣才能扎下根。但現在,面對不斷下跌但在他的心目中仍屬高昂的房價,已經不再敢去想那兩個字,只盤算著怎樣過好眼下的日子。
也許是職業鬧的,張“整天從報紙、廣播、電視上看到聽到世界經濟危機的態勢,以及各種各樣關于未來經濟樂觀或悲觀的預測,覺得一把利劍就懸在自己的頭頂”。
說起來,張斌峰現在最怕的竟是借債的。
“經常有借錢的登門,卻不過面子,只好咬緊牙關扣出自己的伙食費。最后實在是借到無錢再借,還有人登門。告訴他我實在沒錢,人家不信,一翻臉,不認你這個朋友。有一次,一位老同學大老遠從外地跑來借錢,我實在囊中羞澀,他卻時刻跟在身后,吃飯時我請他吃飯,上班時他也坐在我辦公室里,弄得我不能工作,最后只得向同事借錢再借給他。老同學還嫌沒達到數額,滿臉的不悅。錢也借了,人也得罪了。”
張經常外出四處采訪,耳聞目睹商店里的貨品琳瑯滿目。于是,他為自己下了這樣一個論斷:“經濟發展有停滯期也有活躍期。我相信目前的的停滯期過后一定有活躍期,日子會越過越好。”
“為幸福生活節省每個銅板”
■楊永平
(西北大學旅游系教師)
作為一名大學教師,楊永平的收支賬簿在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后,還略有節余。他說“從沒感到過經濟危機的困擾”。
“干了大半輩子‘革命工作,事業上乾坤已定,我準備以一種輕松的心情迎接新世紀的到來。”
算起來,1999年楊永平這位“老革命”遇上的新問題是房改。沒房的年輕人想房子,而有了房子的中年人想換大房子。80年代初,西安市居民住房每平方米平均只有300元左右;但到了1998年,已漲到普通商品房2000元/米2左右,高檔寫字樓和別墅更沖破5000元/米2大關。
楊永平進而算了筆細賬:“若與糧食相比,一袋25公斤的面粉,十幾年前是8元,現在漲到50元,不過五六倍。彩電、冰箱等工業品幾乎在原地踏步,而房價卻飆長了十幾倍。因此,買房才是長久之計。”
楊對時下諸如房改價、優惠價、成本價、標準價等等都摸得門兒清,侃侃而談。他認為今后家庭的平靜日子將面臨“質的變換”,因為一次交出10萬元,“對我們工薪族來說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99年我的財政預算非常簡單,盡量少花錢,盡量多掙錢,可花可不花的家庭開支基本取消。在儲蓄利率較低的今天,我準備把寬裕的資金用來買些風險較小的國債。”
“為了幸福的生活,必須節省每一個銅板。”楊老師最后的總結鏗鏘有力。
“我不會為21世紀大把花錢”
■董邦耀
(陜西省高等級公路管理局干部)
“世紀更新,不就是記錄年代的數字變化么?我不會為進入21世紀高興得忘乎所以而大把花錢。”
老董一上來首先就反問:“問題是你有足夠的財務嗎?”接下來便是理論論證:“經濟是基礎,消費也只能是水漲船高,量入而出,不可寅吃卯糧。”第三,看得出他是個很善于闡述的干部,繼續歸納道:“改革開放20年,我們在消費領域只啟動了‘吃穿用這一個‘發動機,就支撐了經濟持續20年的高速增長。人們現在把打的、打電話、在飯店就餐,都看作是買時間,舍得花。這在2兩糧票8分錢一碗面條的年代是不可能的事。但打腫臉充胖子、憑興趣把錢一下子花光的事,蠢人才會去干。”
董透露了他的家庭經濟支配計劃:一部分用來吃穿用、買書、買住宅樓和應急;一部分搞股票;一部分買債券;一部分借給別人。“孤注一擲不是我干的事。”
董邦耀很有些慧眼,敏銳地預言在世紀之交,全球的商家都會搞“本世紀最后一次”的賺錢把戲;到明年,也許會使出“21世紀第一次”的招數來誘導消費。但他顯然是鐵了心站穩立場。
去年董在西安高新技術開發區,以成本價買了一套三室兩廳120多平方米的住房,除去15%的區域調節、10%的樓層調節、14%的一次性交費優惠和夫妻雙方工齡每年3. 12元的優惠,仍要付約7萬元,幾乎花去了70%的積蓄。“好在不用負債,心里很踏實。”
董邦耀自己有駕照,但已無多少余錢。即便夫妻倆苦攢幾年,傾其所有買輛夏利檔次的車,也只怕養不起,索性現在不去想它。家里已裝了電話,也沒必要再弄個花閑錢的大哥大什么的去擺譜。倒是微機可以考慮,上高一的女兒用它學習,妻子提高業務,本人寫作,值。他已和妻子說好,過些天就搬臺回家。
21世紀的董邦耀認定“量入為出”的原則,“花錢得悠著點,不要能挑八十挑一百,小心閃了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