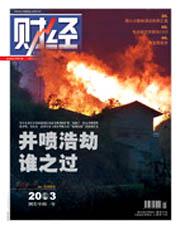柳傳志:聯想的“制片人”
當生活開始變得輕松……
柳傳志希望有更多時間鍛煉身體──在中關村家中的跑步器上;他還希望有更多的時間來看看閑書——柳傳志讀書甚廣是一眼可知的,在談話中他自如引用曾國藩或者高陽的話來輔助表達;柳傳志還想看更多的電視節目,他對正在播放的電視劇《雍正王朝》相當著迷。
柳傳志相信離這樣的幸福生活已然不遠,“再過兩三年就行了。”他告訴記者。
作為中國規模最大和受人議論最多的電腦公司的創業者和董事局主席兼總裁,柳傳志本應該忙得不可開交。從最近的行程安排看似乎也是如此:記者采訪安排在上午11點結束的一次董事局執委會后;在此前一天晚上,他才從香港回到北京;而在去香港之前,他在上海呆了一個星期。結束采訪離開位于北京科學院南路10號聯想總部大樓時,陪同的聯想公關部人員指著一輛奧迪:“那是柳總的車,看來又要走了。”
然而繁忙的日程后面,柳傳志的心態看上去沒那么勞累。
“1998年我相當放松,年輕人們成長起來了。”他說,“如果說我們在創業初是演員兼導演的話,那現在不僅已經越過導演階段,而且算制片人了。現在,很多時候是應年輕導演們的要求,客串幾回演員,主要也是表演。”
回想起并不太遙遠的1987年,真是世事如煙。當時聯想第一次從海外直接進口整機,中間商卷了聯想的400萬元無影無蹤。柳傳志與創業同仁、現任聯想常務副總裁的李勤一塊兒到深圳追款。
“那件事情真是九死一生,我在深圳住了3個月,玩兒命地追。那些日子,一到半夜兩點鐘我就被嚇醒,心狂跳不止。等追回款,機器買回來,我也成了‘橫路敬二(日本影片《追捕》中的人物,被迫害以至精神不正常——編者注),說話語無倫次,不得不進海軍總醫休息了兩個多月。”柳傳志說。
這樣的遭遇,對柳傳志抑或聯想,可能都再也不會有了。
而前面還有100億美元的朦朧目標……
15年前,柳傳志和11個同事拿著中科院計算所的20萬元下海辦公司;到今天,聯想已經發展成了總資產53億元、凈資產37億元的全國最大的電腦公司。當1996年聯想電腦以微弱優勢擊敗外國品牌,第一次坐上了中國電腦市場占有率頭把交椅時,有外國記者問柳傳志:“你們能保持多久?”
據一份最新的市場調查表明,目前聯想電腦在中國市場的占有率到了15.2%,超過其最近的競爭對手一倍以上。現在外國記者們的新問題是:“聯想會成為中國的IBM嗎?”以此為標題的文章出現在1998年年底的一期美國《商業周刊》上。
聯想自1997年以來有一個見諸公開宣傳材料的目標——2000年實現銷售收入30億美元,進入世界信息產業前100名;2005年實現銷售收入100億美元,接近世界前500家最大企業。而它1998年1至11月的銷售額是141.2億元人民幣,全年的銷售額大約會超過150億元人民幣。
2005年實現銷售收入100億美元,意味著在接下來的7年中,銷售收入要增長4倍以上。盡管聯想人有著實現幾乎所有既定目標的良好傳統,但顯而易見,這仍將是一個困難的任務。
柳傳志保持著一貫的穩重。“2000年達到30億美元沒問題,就憑現在的成熟業務,自然發展就能行;至于2005年達到100億美元,這是一個朦朧的目標。”他說,“不說死,早一年晚一年沒有太大關系。”
聯想不準備在信息產業之外實現這個目標。“到2005年,聯想也還是要以信息產業為主。房地產、金融都不做。”柳傳志說,“并且主要依靠國內市場,關鍵是要把國內這塊餅做大。”
這可以解釋聯想一年來頻頻出手的原因——去年8月12日,向著名軟件公司金山軟件注資900萬美元,取得30%股權;9月23日,與IBM簽署協議,在軟件領域展開全面合作;11月30日,與世界第二大獨立軟件開發商CA公司合資成立聯想冠群公司;與中國科學院計算所合作,成立聯想中央研究院。
很明顯,在業務的寬度和深度兩個向度上,聯想同時加快了拓展的節奏。打開聯想的1998年度工作總結,里面是一年所完成的工作清單,長得不得了。
然而回顧昨天,柳傳志仍然告訴記者:“1998年是我心情比較輕松的一年。”
把“領軍人物”推上甲板
柳傳志認為,聯想的理想模式應當是一支“艦隊”,而每一只艦艇上要站著一個獨當一面的人物。這個人當然還要是年輕人。原因不言自明:電腦業的“633”現象──6個月研發、3個月銷售、3個月處理存貨──決定了在一線搏殺的必須是年輕人。
艦只當然可以越造越多,但艦隊模式的發展,取決于有沒有足夠多的堪當大任的年輕人站到艦長席上。柳傳志承認,這是對于聯想今后命運最為關鍵的因素。“我們有好的項目,也不缺資金,關鍵還在于有沒有合適的人。這是最重要的事。”柳傳志說。
眼下最為人注目的年輕人是楊元慶和郭為,年齡都在35歲以下,都擁有從最底層做起的資歷,也有著憑借才華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脫穎而出的愉快經歷。他們現在都躋身于聯想集團董事局6人執委會之中,并且分別是聯想電腦公司和聯想科技發展公司的總經理──這兩個公司是聯想集團六大支柱產業中最為成功的兩大支柱。前者自1996年后保持并擴大了中國電腦市場占有率第一名的優勢;后者建立起覆蓋全國的超過800家分銷商的強大銷售網絡。在聯想2000年實現30億美元銷售額的計劃里,它們各自要有100億元人民幣的貢獻。
楊元慶和郭為這樣的年輕人,在聯想內部有一個響亮的名字——“領軍人物”。這個詞是柳傳志本人的發明。在聯想內部,“領軍人物”現在是帶著光環和魔力的詞匯。年輕人對此無限向往,而柳傳志說起它時,總是無限期待。“現在有五六位年輕人有領軍人物的才能,但這還遠遠不夠。”柳傳志說。
在一篇關于楊元慶的訪談文章里,楊認為自己對聯想最大的貢獻,在于“在聯想老一輩領導人那里樹立了任用年輕人的信心和信譽。”據說,這句話深深地觸動了柳傳志。
不了解聯想的故事的人,理解不到兩代企業領導人以第三者的文章為媒的相知是如此可貴。
1990年,聯想公司發生了一起年輕人“嘩變”事件。一名清華大學畢業的研究生要把人拉出去。時至今日,柳傳志不愿講述詳情,但他將此歸入了少數幾次置聯想于“生死之間”的重大事件。事后回顧,柳傳志認為,這人打的算盤是以為聯想跟一般的國有公司沒有什么區別,心態是想撈一把就走。最后因為5萬塊錢的事情,這人進了監獄。
“在此前后,聯想連續3個年輕人進了監獄。”柳傳志說。
這件事一定嚴重地打擊了年輕一代在老一代企業領導人心中的印像。雖然沒有證據,但聯想直至1993年受到嚴重挫折、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未完成預定目標時,才終于開始著手領導層的“換血”工作,肯定與此有關。
1993年外國電腦公司大兵壓境,國內原有的四個著名電腦廠家“全都頂不住了”。聯想原訂3萬臺的年度銷售任務只完成了2萬臺。
“這種情況第一次出現,所以就非常緊張。”柳傳志回憶。這是聯想最困難的時候。
聯想的應對方略便是后來被稱之為“艦隊”的模式。舊有的架構是一個副總裁管銷售,一個副總裁管生產研發,一個副總裁管采購,大家分頭負責。改革之后,這些事情被一個總的事業部全管起來。在此之前搞惠普代理的楊元慶,被推到微機事業部總經理的位子上。
楊元慶的提升充滿了臨危受命的氣息。伴隨著他的上升,聯想完成了體制上的重構,與此相應的是一批創業“老同志”們退出第一線。
有人問柳傳志,為什么敢于在生死關頭啟用30出頭的楊元慶?柳傳志回答說:“我研究他已經很久了。”
柳傳志放手一搏,楊元慶不負重望。兩代人終于合力使聯想免于陷入“不讓年輕人上就得死,讓年輕人上又不放心”的死結。
1997年夏天,在一次與新聞界的交流會上,柳傳志第一次談起“造就一批青年領軍人物”。就在這次場合,柳傳志向新聞界一一介紹了眾愛將:聯想電腦公司總經理楊元慶、聯想科技公司總經理郭為、聯想科技園區總經理陳國棟……
他們都是30歲出頭,都是在聯想最困難的時候挑起重任,都掌管著數以億元計的資產。聯想的“艦隊+青年領軍人物”的模式漸趨成熟了。
讓股權為每一名員工“定價”
也許是因為時機到了,柳傳志近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開始披露這樣一個事實:1994年,聯想大規模新老交替啟動之前,聯想的“所有人”中科院將聯想35%的“分紅權”給了聯想的員工——其中的35%分配給了“參與創業的老同志”,20%分配給了“一般老同志”,另外45%留給未來的新員工。
很顯然,“老同志”們之所以坦然地離開第一線,“分紅權”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靜悄悄地發生在1994年的這次“分紅權”分配,無疑是聯想和中科院的一次巧妙的制度安排。“分紅權”既能掩人耳目,又在實際上開始了股權的分配。由于聯想從中科院獲得了包括人事權、財務支配權、經營決策權等在內的極大的自主權,“分紅權”實際上扣上了股權分配的關鍵的一個扣子。
柳傳志現在對“分紅權”和“股權”這兩個詞匯并沒有非常嚴格的區分,在某些媒體上,他直接把這叫做“股權”。
雖然直到今天,在聯想集團最新的一份報表(1998年中期報表)上,顯示聯想諸多的董事中只有一位(不是柳傳志)擁有聯想的股份,但不管怎樣,現在完全可以說,早在1994年,聯想就開始了以類似股權的方式為人力資本定價的成功試驗。這在當時是極為超前的。
柳傳志屬于“創業的老同志”,雖然他未說明個人享有多大比例的“分紅權”,但他對聯想的貢獻顯然已得到了某種體現。同一份報表披露了聯想董事局6位執行董事所享有的認股權方案──在從1998年9月開始算起的10年中,6位董事可以以每股1.112港元的價格,購買數量不等的聯想集團(在香港上市)的股票,其中柳傳志的認股權數是200萬股。
這不是一個太小的數字。如果柳傳志以接受本刊記者采訪的當日股票收市價(2.90港元)執行認股權,他將獲得357.6萬港元的財富。
據說,聯想正在實施一場規模宏大的認股權計劃。現在,聯想在香港上市的股票為17億股,將擴股10%,以分配給以骨干員工為主的全體聯想員工,價格低于市值20%。
一個以股權方式為主體的企業激勵機制顯然正在成型。
結語
談到聯想的成功對IT業到底具有什么啟示時,柳傳志認為,最主要的是表明了“中國人也能與外國人在信息產業競爭”。
“聯想創造了民族品牌。我們不是與外國人比武術,我們偏偏選了田徑,照樣能拿分。這一點是長志氣的。”他說。
這將是一場永不落幕的競爭,而柳傳志作為“制片人”,大概可以較為安然地隱身幕后了。可堪大任的年輕將才在涌現,相當健全的股權安排基本到位。柳傳志已經為聯想的未來搭好了幾乎是最好的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