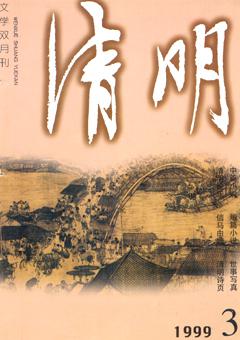以特有的方式逼近生命的真實
侯繼偉
在馬鋼,有一支頗具實力的文學創作群體。李黎、梁劍華應是馬鋼創作群體第一代的較為突出的代表,早年在電影劇本的創作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績。近年來,梁劍華投身于文學的組織工作,為扶掖后學耗費了大部分的精力。但盡管如此,梁劍華并沒有停止文學創作,這位一生鐘愛文學的人,面對寫作依舊精神矍鑠,筆力強勁。他以平和的心態,睿智的筆法,創作了一個“人物系列”的短篇集成,同時,還在《馬鋼日報》月末版開設了隨筆專欄,這使我們時常有機會領略他那洞察世事的犀利眼光和永葆青春的瑰麗情懷。
馬鋼作家群的第二代的陣容頗為壯觀。濮本林、王曉陽、郭啟林、郭翠華、王杰是他們當中的代表人物。
七十年代中期即發表了大量詩歌的濮本林,后以微型小說創作在全國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他不僅多次在全國微型小說大賽中獲獎,其優秀之作《那團云霧》更是得到了已故著名作家茹志鵑的贊揚與好評。
王曉陽早在八十年代以一篇《機關無故事》(《小說選刊》選載)開創了馬鋼新時期機關題材創作的先河。此后王曉陽的創作大多以機關為題材,寫出了一系列這樣的小說。王曉陽善于從人物出發,對人物性格進行剖掘,在展開人物關系的同時,使故事向深層演進。這里所說的“深層”就是王曉陽對于具體的人性和這種人性賴以存在的具體環境的思索和探究。筆者認為,王曉陽一直在作這樣的思考,那就是企業的體制對人的鉗制而使人產生了扭曲和變態,這種扭曲和變態反過來對企業又會發生怎樣的影響呢?我們又將如何對待眼下企業的體制呢?王曉陽特定的職位使他更易于產生這種思考,他以他的作品對他的思考進行了成功的表現。王曉陽以滿腔的熱忱目光炯炯地關注著改革的進程,我們在他的作品中,似乎看到了他的表情在改革進程中的變化,時而笑容燦爛,時而蹙眉憂思。隨著企業改革的深化,他的思考也在深化,去年發表在《作家天地》上的短篇《藍軍在一九九八》和發表在《當代》的中篇《老單》,證明了這種深化。
《老單》里老單這個人物看上去令人啼笑皆非,他是一個當過營長、享受副處級待遇的所謂的“老干部”,然而他卻身居一個當下企業里最為尷尬的角色:信訪(不是主任,只是一個負責接待信訪者的工作人員)。令人不解的是,他和黨委書記古廣田享受一人一間辦公室的同等待遇。有趣的是老單還有一塊“自留地”(這是一個已經作古的詞)……種種荒唐可笑的情節和細節——呈現在讀者面前,作品的象征意味慢慢地彌漫開來——一部好的作品總是處處洋溢著象征。
圍繞著孤單的老單展開的依舊是所謂官場的紛爭。
作者借人物之口發言了:“古廣田感到無形中有一股強大的傳統勢力,在使官場按部就班(準確有力的用詞)地沉淪……改革多少年了,就是動不了龐大的機關,治不了人浮于事的惡習。”
作者對此深感無奈。
作為作家的王曉陽當然不能給出醫治問題的藥方,但是作者生動而深刻的揭示卻讓我們感受到了不動聲色的震撼。
也許是兩人職務相近的緣故,郭啟林的創作和王曉陽有相近之處。
郭啟林的筆致十分細微,他的目光通常集中在小人物的身上,以一顆敏感脆弱的心靈去探詢去感知去同情去關懷小人物的感情,寫出了他們的悲歡、他們的無助、他們的猥瑣。郭啟林同樣關心改革年代的風云變幻,并善于用小視角予以展示。新近發表在《朔方》的《秋色深沉》就是這樣的一部中篇。某公司因欠水費面臨被斷水的危機,而改革在如火如荼地繼續進行著,上訪者也適時來臨,使公司陷入混亂和困頓。
《秋色深沉》揭示了改革帶來的陣痛。
幾年來,郭啟林還完成了一個題為《在淮北》的知青短篇小說系列。這個以作者知青生活為題材的系列短篇,是郭啟林創作的精彩別調,令人欣喜的是郭啟林擺脫了知青文學“訴苦”的俗套,也沒有進行貌似深刻的文化反思。郭啟林以一顆作家不可或缺的樸素的童稚之心追憶自己的知青時代,也抒寫了苦難,但更多的是抒寫了苦難中的美好生活。這部作品告訴我們,無論何時何地,只要有人存在,美好就不會消失,快樂就不會消失,人們對美好和快樂的追求就不會停止。這部有著童話品質的小說,是作家對逝去生活的一次善意的澄清,是作家創作的一次升華。讀郭啟林的《在淮北》,我們不禁想起了楊絳先生的《干校六記》,化苦難為無形,說人生之真味,使我們不覺向人生的大境界邁進了幾步。
王杰是馬鋼中年作家中最為勤奮的一個,二十幾年來孜孜以求,埋頭耕耘,取得了不小的收獲。近年來在中長篇小說創作方面心得頗多。新近創作的中篇小說《尋找故事》表現了王杰對中篇創作的某些追求。這個長達四萬余字的中篇小說,頭緒紛繁,人物眾多,但是王杰駕馭起來比較得心應手。小說中的周民,一個似乎是多重身份的小人物,在紛亂的世俗生活中,無法為自己定位。周民的思維似乎是極其混亂的,他有時似乎覺得作家這個身份可以使自己“高人一等”,起碼可以和一些有身份的人平起平坐,起碼可以置身局外,但是生活本身攪得他頭暈眼花、六神無主、四肢乏力——面對無情的現實,周民無疑是軟弱無力的。短暫的風光是鏡花水月,無休無止的勞煩奔波才是永恒的現實。故爾周民的心似乎永遠在到處流浪。
《尋找故事》的背后其實是在尋找生活,尋找我們期望的生活。
王杰成功塑造了一個特定時代產生的特定人物,須知在我們這個國家里,以作家(“作家”是這部作品中不容忽略的代碼)自居而不能自拔的人不在少數。而一個培養了大批“作家”的國度,同時培養了大批的精神貴族。“精神貴族”并不是壞事,但是在新的時代到來之際,“精神貴族”不應該沉湎在往昔的“光環”之中,沉湎既久,難免麻木和迷亂。
作品以現實主義的批判意識對當下的某些社會現象進行了無情的諷喻。
值得注意的是,王杰在此篇作品中,對生活進行了相當深入的反省。作品流露的意緒是多重,此外,王杰在此篇作品中對小說語言進行了新的嘗試,一些散落的幽默使作品的內涵擴大了許多。
繼中老年作家之后,馬鋼又涌現出一批六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他們當中有梁詩溟、韓衛、薛峰、朱田銀等人。他們同樣是頗具實力的一群,近年來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梁詩溟是一位迷戀短篇小說創作的青年作家,同時也是一位對小說技巧情有獨鐘的作家。美國作家約翰·厄普代克認為:當代小說有一種深刻需要——即對技巧的事實加以承認的需要。若干年來,梁詩溟對小說技巧進行了一番——可以說是細致的鉆研,全方位的研究。梁詩溟所發表的全部作品幾乎可以說是風格各異的。梁詩溟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他的短篇小說具有一定的完美的特性,起碼在形式上是比較完善的,他是一個唯美的追求者。梁詩溟對小說的可讀性、小說的單純性都有自己獨到的理解,尤其對小說的幽默感有自己的見地,他在這些方面所進行
的許多試驗,結果是令人滿意的。
發表在《漓江》的《一件武器的擁有》是梁詩溟作品中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說里一個所謂的“后現代男人”,在京城購買了一件人造的男人的武器,他不是大大方方購買的,而是通過曲折隱蔽的郵購方式。這個男人擁有了這件武器之后,當然想帶回去一展神威。可是這個男人卻發現,他無法讓這件武器發揮作用,總是有這樣那樣的原因(障礙)使他無法使用這件武器,最后他把這件武器悄悄投進了垃圾箱。他自語了一聲:別了,司徒雷登。在這里最容易想到的是:永別了,武器。梁詩溟也想到了,但是他沒有采用。采用哪一個,這其間差別是很大的。如果采用后者,那顯然是草率的不負責任的表現。筆者曾和梁詩溟討論過這個看似小小的問題,梁詩溟說了之所以選擇這個而不選擇那個的種種原因之后說,他發現“司徒雷登”這四個字的字形和發音——尤其是發音——和那件武器頗為神似。這就是梁詩溟,對細節的揣摩有時到了過于細膩的程度。梁詩溟甚至打算建議武器制造商們將這種武器統一命名為“司徒雷登”,他說這樣肯定有促銷的作用。
我們不難發現,這個男人的障礙來自他的內心,來自他的柔軟敏感的內心。武器與“現實”的比照難免令人心慌,甚至心悸,作家十分隱蔽地敞開了自己的心靈。在這里作家嫻熟地運用了技巧(隱藏),這樣使作品的意義產生了發散的效果:既是武器,就會產生虐殺,令人不忍出手,出手則有可能破壞已存的真情與溫馨(精神之愛和肉欲的沖突永遠是男人的困擾)。喜歡探究意義的讀者也許會從“別了,斯徒雷登”聯想到美國,聯想到西方文化的侵入?是不是會認為小說的主人公是個排斥外來文化的家伙,進一步聯想到東西方文化融合的問題?
喜歡探究小說意義的讀者在梁詩溟這里是不會失望的。
梁詩溟同樣是一個成功地關注和展示了意義的作家。
發表在《清明》的《浮影》,是梁詩溟短篇小說的另一式樣。
梁詩溟的探索是多方面的,去年,梁詩溟寫了一個叫《玄一閣筆記》的作品,用“現代性”的語言寫筆記小說,讀起來新穎別致,讓人耳目一新。此作被《作家文摘報》摘登。
韓衛、朱田銀、薛峰的創作也是各具特色,是馬鋼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
在《清明》發表的短篇小說,《銅斧》是韓衛的短篇代表作品。這篇小說說的是一個青年面對誘惑,在金錢和道德(人格)之間搖擺,最終導致了毀滅。小說中彌漫著夢幻般的恐怖氣氛,充分顯示了邪惡的力量和被邪惡所俘獲的可怕。韓衛在作品中流露了對小說主人公巨大的同情和惋惜。掩卷之余,我們倍加感到個人人格的鑄造是多么的重要,我們要想在邪惡面前強大起來,惟有借助正義的力量和不屈的人格的力量,即必須讓我們的精神強大起來。
在此有必要提及韓衛發表在《作家天地》的一個中篇小說《兵頭將尾》。這個四萬多字的中篇堪稱是國營企業班組生活的風情畫。作品以活靈活現的筆法,生動再現了班組生活。小說通篇筆力強勁,無一松懈之處。這是韓衛在火熱的生活中獲得的寶貴收獲,這部中篇再好不過地證明了創作來源于生活這一真理。
同樣的收獲是發表在《小說家》的中篇小說《人以群分》,也是一部反映班組生活的中篇,此篇被《中篇小說選刊》選載。
朱田銀和韓衛有一些共同之處,朱田銀的小說也全部是對小人物的描述,對小人物寄予同情和關懷。但是朱田銀有自己的獨到細微之處。朱田銀小說的魅力首先是他的與眾不同的趣味,一種與生俱來的幽默感。朱田銀喜歡對細部作不厭其煩的趣味化的描摹,對一盤菜的描寫要一直深入到盤子的花紋。一個細節總要反復把玩,一直窮盡其趣味才肯罷手。筆者開始以為朱田銀是在使用技巧,即小說的重復技巧。事實證明不是這樣——盡管這樣做達到了使用技巧的目的,但對于朱田銀來說,這樣做是他的天性使然。這是朱田銀得天獨厚的優勢,天性成了技巧。
無須置疑,趣味自然會產生一定的意義。
也許余華的一個說法比較適合朱田銀的寫作:幽默即結構。
由于朱田銀過多地感受到了生活的無望和殘酷,所以他的幽默較多的時候帶有黑色幽默的味道。
薛峰是一位很有才華的青年作家。其代表作品《素素》、《工傷》、《假面舞會》充分顯示了薛峰的創作實力。發表在《清明》的《假面舞會》是一篇對當下社會進行了嚴峻的思索之后而發出了致命的質問的小說。薛峰用人與狗建構了小說的情節(對比),對人性和狗性進行了一番充滿感情色彩的辨析與詰難,表現了動蕩年代的相當多的一部分人的思想感情,以及他們的無助和迷茫。
薛峰的中篇小說《植物人》,也是一部很有分量的作品,《植物人》是《假面舞會》的延續和擴大,也是對《假面舞會》無奈的圓整。《植物人》似乎要告訴我們,我們唯有成為植物人才能在這個世界里安靜地生存。
這是蕓蕓眾生的生存狀態的一個側面:無奈之后的頹喪與沉淪。這種現象在所有的社會轉型期都會出現。
關注當下并迅速在作品里表現,是薛峰的寫作特點之一。
這也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的寫作特點之一。
總的來說,馬鋼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在經歷了曲折的探索之后,大體上回到了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上。
讓我們來看看七十年代出生的一批更加年輕的作者。
他們是韋金山、戎勇、程迎兵、楊彤頻、邢懷中等等。這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群體,他們雖然出道不久,但顯示了良好的創作勢頭和寫作風氣。他們少有舊習的包袱,是馬鋼創作群體的新生力量。幾年來,他們勤奮寫作,取得了一定的創作實績。
僅以韋金山為例。
韋金山發表在馬鋼的文學期刊《江南文學》上的短篇小說《一只茶壺的自敘》,是一篇相當精彩的小說。小說雖然采取了司空見慣(一切手法似乎都是司空見慣的)的擬人手法,但由于作者語言的張力、內省的深入和觀察的細微,我們感到敘述的鮮活之風撲面而來。語言的外衣與內容的肉體幾乎完全熨貼,因此作品用較大篇幅抒寫一個卑微“人物”的內心沖突和痛切感受,并不顯得啰嗦。跟著這把茶壺前進,我們感到小說有了復調音樂的魅力。
小說的后半部展示了男主人公的虛偽和冷酷,為茶壺的感受找到了證據。
一篇非常可讀的意味深長的小說。
最后,讓我們來談談馬鋼優秀的散文作家郭翠華。
十幾年來,郭翠華在繁忙的編輯事務之余,擠出點滴時間,辛勤筆耕。作品數量和創作成果都頗為可觀。近年來,郭翠華的創作愈加勤奮,并且取得了更加可喜的成績。長篇系列散文《我們這代人》就是郭翠華新近創作成績的集中體現。
對于郭翠華,潘小平有一句非常精當的評語:對苦難和日常生活的敏感。
郭翠華自從事散文創作以來,即以“本真”的姿態寫作。觸景生情,見物所感,信手拈來,涉筆均成美文。
一九九五年,郭翠華將所得作品結集為
《紫色的夜》(此書獲去年的安徽文學獎)出版,周介人欣然為之作序。
周介人將郭翠華的散文概括為一株“難之花”,這個斷語和潘小平的評價是英雄所見。周介人說,郭翠華對人生之“苦”之“難”的敏感源于什么呢?我想可能是源于她的弱。
也許是序文的篇幅所限,也許因為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周介人沒有進一步闡述“弱”的含義。以筆者的理解,周介人所說的弱,正是真與善的同義語。也許真善美在與假惡丑的漫長的斗爭中,最終將戰勝假惡丑,但在許多具體的情境下,假惡丑一般是以強悍的姿態處于凌弱的位置。性情真摯的郭翠華懷著一顆善良的心面對這個世界,以至于郭翠華對男人們的豪飲都做了充滿善意與美感的詮釋。這是善者的浪漫主義理想在現實中的一次精彩的折射,是善者對久遠未來的美好向往的超前實現。
“為真情而喝的酒也許是不醉人的,所以才喝的流暢,難得醉。就是醉也醉得痛快,醉得漂亮。”《內蒙情思·酒之禮贊》
這是一顆純美的心靈所制造的脆弱的彩虹。
穿過《內蒙情思》“清脆如竹的歌聲”,郭翠華經歷了《深圳行》。
表面上這是一次由內地向沿海的旅行,本質上卻是一次精神的探險,一次靈魂的劇烈震顫。
在深圳這個商品經濟大潮率先涌起的地方,郭翠華看到了三個世界:物質的世界,金錢的世界,自我的世界。
郭翠華面對這三個世界,內心產生了矛盾和彷徨。
她寫道:“……我將躲在舞臺后面又瘦弱又渺小,而對一個自由的選擇,突然發現自己并不知道要做什么。在深圳我感到自己失去了一種安全感。”
這是心的告白。
這是真誠的傾訴。
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郭翠華的散文被“紫色的夜”所籠罩。面對日趨喧囂的世界,面對人欲躁動的世界,郭翠華開始了一個真正的寫作者的精神遠征,一次頗具悲壯意味的精神征戰。對自身行為的反詰,對靈魂的拷問。在精神意義方面,郭翠華這個時期的散文,可以說是《天問》現代版。
郭翠華的征戰取得了勝利。
我們讀到了以《我們這代人》為代表的一批新作。
在《我們這代人》中,郭翠華借助對逝去年代的事件的溫款追憶,完成了對自己紛繁思緒的梳理。我們看到了苦難,但我們很少看到怨懟;我們看到了是與非的辨析,但我們沒有看到“真理”擁有者的不應該有的倨傲。我們感受到了“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意境,我們聽到了“我們這代人”的純凈的聲音。這依然是“我”的聲音,但卻是“大我”的崇高之聲。
“紫夜”漸漸透明,迎來了燦爛的曙光。
郭翠華的散文創作就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天地。
余華在評論布爾加科夫的寫作時說,(布爾加科夫)沒有了出版,沒有了讀者,沒有了評論,與此同時他也沒有了虛榮,沒有了毫無意義的期待。他獲得了寧靜,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寫作,他用不著去和自己的盛名斗爭,用不著一方面和報紙夸夸其談,另一方面獨自一人時又要反省自己的言行……他不需要迫使自己從世俗的榮耀里脫身而出,從而使自己回到寫作,因為他沒有機會離開寫作了。(《我能否相信自己·布爾加科夫與大師和瑪格麗特》)
馬鋼的這個作家群體在創作成就上雖然無法和布爾加科夫相提并論,中國也不是斯大林時代的蘇聯,他們也并非沒有出版,沒有讀者,沒有評論。相反,他們有出版,有讀者,也有評論(眼下我正在寫著一篇評論)但他們與布爾加科夫相近的是,他們幾乎沒有虛榮,沒有毫無意義的期待,他們以業余寫作的姿態寫作,這使他們獲得了寧靜,獲得了真正意義的寫作。他們并不刻意去追求出版、讀者、評論。他們只是業余寫作,在馬鋼他們都有各自的工作崗位,他們每個人都身居要職:或者是領導干部,或者是一線工人。甚至他們都是各自崗位的杰出人士,是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他們互相有著良好和諧的關系。他們用不著去和自己的盛名斗爭,用不著一方面和報紙夸夸其談,另一方面獨自一人時又要反省自己的言行。他們不需要迫使自己從世俗的榮耀里脫身而出,從而使自己回到寫作,因為他們沒有機會離開寫作了。
他們已經結結實實地愛上了寫作。
因為寫作是他們敞開心靈的最好方式。
他們默默地在自己的崗位上工作著。
他們默默地在燈下創作著。
他們以他們特有的方式逼近各自的真實。
因為對他們來說,創作就是逼近生命的真實的美好旅程。
責任編輯潘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