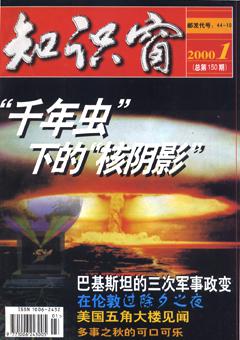澳門首任同知印光任
劉建銘
澳門已于1999年12月20日回歸了祖國懷抱。然而,在葡萄牙統治下的400多年中,為維護民族尊嚴,捍衛領土主權,一代又一代中華豪杰、仁人志士與葡萄牙殖民者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斗爭。其事可歌可泣,其人永垂千古。印光任便是其中杰出的典范。
印光任,字黻昌,號炳巖,江蘇寶山縣市寶山縣人,乾隆四年(1736),他出任東莞知縣。乾隆八年(1743)年底,為了加強澳門沿海的防務工作,乾隆初年(1736),他被清朝政府選任為澳門第一任同知(小于兩廣總督而大于縣丞之職,同縣令級),乾隆十年(1745)11月,他因治理有方、功績卓著,被調任南澳任職。在任澳門同知的兩年間,印光任以德為人、以理服人,與葡萄牙殖民者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維護了民族尊嚴,保衛了祖國疆域,為后世所稱頌。
仗責葡夷初露神威
印光任上任澳門同知的半年時間內,并不像其他官員那樣急于廣召下屬官員,而是閉門細閱有關澳門的各種史料,調查山川水路及地理等情況。閑時,他便與清正廉潔的官員唱詩答對,談古論今,尤其視香山(今廣東中山市)知縣張汝霖為知己。下屬官員感到不解,許多人在半年內還未見過同知一面,他們每天得到的只是同知安排的具體事務,完畢后所需做的事便是向印光任的幕僚稟告。但若有人稍有疏忽,便被責杖、扣餉。由于賞罰得當,人們不得不深表嘆服。印光任在他們眼里雖好像隔了一層神秘的面紗,但人們都感受到了他的一種無形的威嚴。
澳葡自治機構的官員只聽說了清朝政府派了印光任來管理澳門,但多日來只聞其名、不見其人,都不知個中底細,遂命在中國內地的傳教士對印光任的身世進行周密的調查,廣收情報,細加研究。不久他們便得出這樣的結論:雖然印光任當知縣時小有名氣,但卻是個不問事、不做事、不想事的“三不”庸官,可擇機羞辱他。
于是,葡萄牙澳門總督科·佩雷拉便派出了300多名葡人押著一名中國商人,前往同知府挑釁鬧事。
面對喧囂之眾,印光任從容不迫,凜然正氣,用華語和葡語雙管齊下,只用了三言兩語,便使葡人吱唔含糊、漏洞百出。原來,他們根據指令,在購買中國商人的貨物時,硬塞給商人3兩金子,爾后謊稱中國商人不守法規,欺詐葡人,故而前來問罪,想出印光任的洋相,以便進一步摸清他的底細。
雖然奸計已露,但葡兵們還是擺出一副能奈我何的神態。哪知印光任一聲斷喝:“來人啦,給他們每人打二十大板!如果膽敢再犯,本官一定從嚴懲罰!”長期驕橫的葡兵初臨如此威嚴之勢,嚇得六神無主,狂態盡失,一個個被扯倒在地,受木杖“伺候”。執刑的中國衙兵由于對葡兵深惡痛絕,把多年的積怨盡情地發泄在杖責之中,直打得葡兵嗷嗷直叫,大喊饒命。刑后,先前囂張的葡兵變成了殘兵敗將,他們怨聲迭迭,蹣跚地向主子復命而去。而對那位中國商人,印光任賜予了白銀20兩,以示安撫。
事后,澳門百姓聞之,無不歡欣鼓舞,反葡情緒劇增。而澳葡總督佩雷拉則啞巴吃黃蓮,這才知道印光任不是個等閑視之輩。
智破“報恩計”喝退入侵兵
乾隆九年(1774)8月,西班牙3艘軍艦滿載兵卒巨炮,在澳門附近游弋,妄圖尋機入侵澳門,壟斷中國的海上貿易。當時印光任正為修筑澳門海防工事而忙碌,他在聽說此事后,便立即派船迎往查問。哪知一位西班牙軍官西士古竟狡詐地說是為了“報恩”而來,
原來,頭一年的6月,西班牙一支海軍和葡萄牙海戰兵敗后,有兩艘船被狂風吹到獅子洋一帶,當時印光任為東莞知縣,他派人將船只俘獲。因西班牙人在海上漂泊多日,彈盡糧絕,只好哀求印光任施恩救生。雖然印光任素聞西班牙人并非善輩,但他還是本著人道主義,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并撥舍糧食,讓其平安地返航。西士古便是其中一人。
印光任耳聞報恩者前來,心覺有異。于是不動聲色地一面讓西士古上岸相見,略加安頓,一面將情況上報兩廣總督,并派人嚴密監視海上西班牙人的舉動。當聽探子報告西班牙人荷槍攜彈,兩船防范嚴密,還派人偵察過澳門海防的部署情況時,印光任便斷定此舉必有侵略意圖,于是便作了一番周密的安排。
待西士古等人了解了澳門的防務之后,欲借機辭行,準備返船部署時,印光任設計將其誘至公堂,斷喝問罪。當西士古還連連聲稱是為報恩而來時,印光任步步逼進,層層駁擊,言刑并施。驚魂未散的西士古狼狽之至,先機盡失,為保性命,只好老老實實地說明了實情:自去年與葡萄牙人海戰以來,西班牙人一直懷恨在心,幾欲尋機報復。后經西班牙情報機構調查,葡萄牙在澳門的軍事力量比較薄弱,于是便想尋找借口,前來偷襲。
印光任繼而慷慨陳詞:“澳門自古以來就是我中華民族的神圣領土,葡萄牙人只是暫住這里做生意,你們偷襲澳門,就是侵犯中國領土,我們決不等閑觀望。”西士古見大勢已去,只好狼狽逃竄而去。
內外兼治立法定規
面對國外侵略者屢次蠢蠢欲動,印光任陷入了沉思:澳門水道很淺,僅有一條供大船航行的深水海道,若不熟悉路徑,外船非擱淺即觸礁。但外船幾次均能順利進入,這說明海區管理不善,若不加以治理,來自英國、法國、荷蘭、西班牙的巨船重炮,將給澳門帶來國土難保、尊嚴難維的悲劇。
據此,印光任為防止內憂外患,穩定澳門局勢,召集了一批有識之士獻計獻策。通過廣納良言,細加整理,制定了一套管理葡萄牙人和外船進出澳門港口的規定,并刻石公布,嚴令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和其他外船必須遵守。這就是澳門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七條規定”。
“規定”指出:“外國船只要想進入澳門,必須經海防衙門嚴格盤查,爾后派人帶入虎門,停泊在黃埔灣……如果查得船上有違禁物品,必當嚴加懲處。”又有“如有人圖謀私利,擅自將外船引入港內,要按照偷渡的有關法律條款從重治罪”等等。該“規定”還對夷人寄居澳門的貿易、生活等方面進行了嚴格的規范,并且增設了海防衙門,擬定了統巡、共防等措施。
在印光任的努力下,生活在澳門的中國人和葡萄牙人均能和睦相處,互不相犯,附近海域也少有事端,使歷經滄桑的澳門出現了短期難得的平靜。
《澳門紀略》傳示后人
印光任常與香山知縣張汝霖往來,或把酒臨風,或吟詩賦詞,或評論政局時事,并曾作有“……只恐將軍畫,難分造化5-”和“……纖塵飛不到,誰是廣寒仙”的詠志詩文。但印光任并非一介文人墨客,他考慮更多的卻是如何干好工作,如何為官一任,振興一方。一次,張汝霖淚吟“……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句之后,印光任便發出“本職工作之余,能否為后人做一些值得留念的事呢?”的感慨,當即就對張汝霖說:“澳門自葡萄牙人占有以來,已有200余年了,我最近幾天研讀史書文獻,見古時資料散失較多,后人恐怕難以知悉其時事的變遷了。我想從現在起,一面做好工作,一面追述歷史,以備后人查讀。”并誠邀張汝霖共同編寫此書。
鑒于印光任治澳有方,且廣東南澳、廣西慶遠等地秩序較為混亂的情況,清政府將他調赴南澳任職。臨行前,印光任將撰寫澳門歷史的任務托交繼任的張汝霖。后又將草本托給粵秀山山長徐鴻泉加工潤色,不料部分文稿因徐的病故而遺失。到乾隆十六年(1751),印光任擔任南澳同知、并負責潮州知府事務時,張汝霖恰巧也因公到潮州,于是兩人重提舊事,并尋來剩余稿件,奮戰數月,終于寫成了《澳門紀略》一書,為后人研究澳門歷史提供了寶貴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