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夢重驚
李大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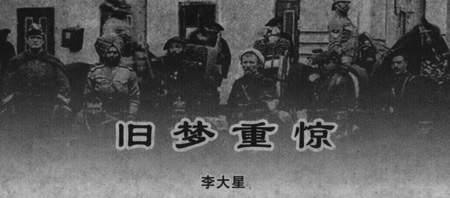
雖然資訊業在今天是這樣的“發達”,盡管知識的傳播在這樣的“發達”的載負下是那樣地容易做到,但是拿到《舊夢重驚——方霖、北寧藏清代明信片選集(Ⅰ)》(以下簡稱《重驚》),還是有了許多驚訝:原來那時竟有這般實時寫真的郵品,原來那時的中國是那么個樣子。盡管有關斯時的文字、圖案我們早已從其他專門非專門的、中國的外國的媒體上看到讀到了許多,但還是有了驚訝,歷史其實并不像戳放在書案上的那些或官家或私人所修撰的史籍那樣簡捷,那樣“條理”。形諸文字的東西,忽略去那些個人主觀的成分(其實這些并不可以簡單地忽略),也許會具有所謂理性的光點,可以將幾十幾百幾千年的脈絡縱橫捭闔地把握于掌中,可卻往往失去了具體的本相,缺乏真實靈動的原色——雖然那具體和真實大多呈現出一種零亂的形象。
《重驚》所給予我們的便正是這樣一種原色般的“本相”。翻動一頁頁印制精致的書頁,排沓而來的當然絕不僅是驚訝,看過皇帝、皇后及李鴻章、張之洞們正襟危坐的“標準照”后,行刑、砍頭、凌遲和身首異處、示眾的具象排列,不能不讓人觸目驚心。那躍然于眼前的,慘烈、殘忍之外,看客們臉上露出的,連歌女、名妓這樣的風情中人也不能免的麻木僵硬(參見圖161、216),再一次意味深長的印證了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一位冷峻的哲人有關“示眾”的話。至此,繼續翻動書頁看到的舊京圖景、江南水色以及“漂亮的小腳女人”、“白璧進來,青蚨飛入”的“大殺三方”等等,便總讓人不安于圖片的呈達,總會再想到些什么。這也許就是作者、出版者在檢閱 、簡選之后排列出的一種意味吧。這當然是值得看重的意味。
自然,這些用“光畫”(即攝影)承載著的,不單是舊時中國的原相風貌,其間不能不含有選景者的“眼光”,這些眼光是個人化的,同時也是外域化的。在我們的祖先一再強調中國與“化外”夷狄的高下不同時,這些域外的來客也從沒有忘掉華與洋的差異,那種獵奇的興致,與他們在非洲草原上將土人與動物視為同樣的目標,沒有什么根本的差別。而所謂“膺服”入侵者的“實況”(圖268)和“向中國開戰”的招貼(圖222、223)所透露出的強蠻驕橫,又是更為直截的注明。
說到“光畫”,不能不讓人對這些明信片的制作生出技術上的興趣。如果說圖片效果的精細、清晰還可以認為是攝影的水準的話,那么,這些非常個人化的作品可以在中國這樣原貌地印制出來(這個判斷只是猜測,但從理論上說,這個判斷應當是可以成立的,這一點隨后就有印證),可以想見斯時印刷出版的便利與快捷,而且似乎比今天還有某些勝出。從格款上看,這些明信片大多是洋文獨行,可以認定是洋人所為,不過其間也有純粹中國的商務印書館的制品。因此,這些制作在中國進行是頗有可能的。而不少明信片上還有序號的記錄,可見其批量生產的規模。而圖上、圖旁的中文標示,格式不一,字跡俗尚而時有粗鄙,可以認定是在中國售賣時出于商業上考慮的促銷方式,而圖199“楊記”字樣的戳印,應該是營售商號的痕跡。
展讀此書,當然要感謝方霖君夫婦的留心、細心、耐心和恒心,這其中所涵有的自然不僅僅是搜求的興趣,更有一種精神的存續延伸。而本書的編排、裝幀,也有著與這些明信片時代、風格相呼應的格調,這樣的潤滋于無聲的出版人功夫,是令人欽佩的。當然,也還有一些遺憾,像扉頁書名、序、跋、目錄等處采用的仿制圓戳,用意本來不錯,如果再有些實物感、斑駁些,似乎效果就更好。編撰上也有一些功夫可下,像一些地名,如府門(圖72)、羅蠻子街(圖73)之類,可以討教于專家,免去“譯音”的模糊;而“漢口某樓”(如89)之類的地方景色,也是可以征諸地方有關部門落實明確的。這樣的要求也許近于苛刻,但就今天中國出版的發展進程,就《重驚》這樣難得的素材和佳品,苛求或許并非過分。再說,這些應當并不是十分復雜的事情,而其效果則會很不同。《序》中曾有“它們是大約三千多件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由中國寄往世界各地的明信片”的陳述,本書即由此生發而來。但所謂“由中國寄往世界各地”的定語有些失當,僅從本書看,內中不但有尚未付郵的“未實寄片”和“郵程不詳”者,而且還有不少是“世界各地”之間以及中國境內之間的付寄片。另外,書中由編者加上的類似題畫詩的按語性文字,形式原本可取,只是個人的主觀色彩濃重了一些,立意也稍嫌粗略,給人以“隔”的感覺(如圖176、178、204等)。當然,寫這樣的文字原是一種費力卻不容易討好的事情,但也是可以有不同的處理方法的,比如只是寫實,比如采用相對跳脫的角度,也許效果會更好些。其實,如果將那些明信片上的文字翻譯過來,“按”在圖旁,或許就是不錯的說明文字。
最后,希望這樣的“選集”不止于(Ⅰ),而能夠繼續下去。
(《舊夢重驚——方霖、北寧藏清代明信片選集》(Ⅰ),廣西美術出版社1998年3月版,定價:19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