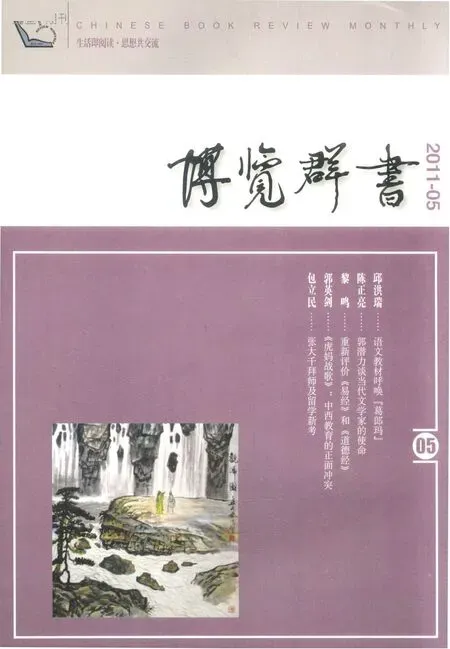民主與科學析(下)
劉自立
上個世紀初,西學東漸,西教東漸,國人視科學民主為救星,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殊不知其一,科學民主是基督教文明的產兒;只顧其子,而忽略其父母的行為,并非舉國上下都是如此看法,比如馬相伯,就鼓吹西教的傳布。其二,也是自世紀初,西方哲學中人已覺察到西學的客體化傾向,無以詮釋西方人失落于社會政治——經濟技術異化的原因,故而使西方哲學轉向對于主體化之考查與辨析。同時,他們也對他們的“上帝”繼續產生挑戰和詰難。這就是牟宗三先生所看到的東學西漸及西學自省的局面——如若可以這樣說的話。這一思維向度便是從客體論傾向朝向主體論傾向的轉變。在否定了康德、黑格爾之主體主義在人生道德上的決斷以后,牟先生說,“存在主義,自克爾凱郭爾起即十分重視主體性……發展至今日的海德格爾,雖主重‘存在的決斷,讓人從虛偽掩飾的人生中‘站出來,面對客觀的‘實有站出來,此似向‘客觀性走……然說到家,他并不真能反對主體主義”。這個論斷所包含的涵義與西方一位哲學家的觀點大致一樣。麥基在其名著《思想家·海德格爾與現代存在主義》一文中也說,自從在西方哲學即理性哲學的奠基人笛卡爾提出了他的心物二元論以后,“人這個主體又與自然發生對抗。由此便產生了心靈與外部世界之間非常驚人的二元性。此后兩個半世紀內,幾乎所有的哲學家都沒有脫離笛卡爾哲學的這條軌道。直到本世紀上半葉,我們才看到反笛卡爾主義的傾向以形形色色的哲學流派的形式在世界各地緩緩地出現——英國、歐洲、美國,無一例外。海德格爾就是笛卡爾的反叛者之一”。笛卡爾是外延與內涵(即牟氏所謂之“內容”)、主體與客體、哲學與科學二元對立的純西方哲學的始作俑者。西方哲學沿著這種把哲學變為“科學的侍從”的傳統一直走到20世紀。其間,由這種哲學引發出來的創造潛能的確盡其發揮。
在另一方面,正如西方人一如海氏所強調的,哲學之功能即是對“存在的分析”。而這種存在,已經有別于任何外延的、科學的真理,而僅僅停留在:通過存在,闡明概念。當然,這一闡明仍舊帶有理性的色彩,而不同于中國哲學中的“內容”性“啟發語言”。然而,這一語言特征——一如海氏所言——已帶有詩性的內容——雖然這種詩性與中國的詩性仍有不同,但互相接近的可能性畢竟大大加強了。
這是海德格爾哲學最為接近東方——中國主體哲學之處,亦為其第一階段;其第二階段呢,就多少又有一點回到客觀析察的氣氛中去了。因其對環境與技術問題的關注,人與客體的關系再次得以闡發。然而,由于對技術“存在”之憂喜參半之慮,海氏對科學——科技并不抱有全盤肯定的態度。人們從新近出版的《海德格爾選集》中可以讀到許多關乎于此的文章。科技本身的負面性;它作用于環境的負面影響;人在技術中的異化;乃至技術是否最終可以駕馭人……都成為他關心的課題。摒棄對于宗教、文化、藝術語言的“真理”,而轉向科技、理性、邏輯,對于無論西方人還是東方人,都是不無補益之擇,問題在于在科技、理性、邏輯之外甚而之上,人們的宗教、文化、藝術訴求,乃是另一種“存在”,即對人性本身之追求;否則,未來的高智商機器人不是理所當然地可以取代人的存在了嗎!一如邏輯實證論者們所言,“邏輯的任務不是人們通常認為的去認識世界,也不是去描述它。……那方面的位置都讓各種科學占了,……哲學的任務是提煉這些科學所采用的方法——澄清它們所使用的概念和論證方法。”有趣的是,由此一來,哲學——一如麥基和艾耶爾所說——被視為二級主題,“一級主題是關于世界的論述,這二級主題就是論述他們關于世界的論述”。
牟宗三先生固然主張要學習科學,但是,科學思維如何融入中國傳統文化,此事體大,不可不析。從牟氏的學術經歷看,他一生最喜歡兩種哲學,一為《易經》;二為懷特海。他說,“懷氏美感強,直覺尤強。他的美感既是內容的(強度的),又是外延的(廣度的)。他的直覺所悟入之事理,亦既是內在的,又是外在的。”他告知,國人知懷特海少。但在懷氏之《歷程與真實》剛出版時,“張申府先生曾有一個簡單的介紹,深致贊嘆之辭”。又說,張氏以為“沒有人能懂,亦無懂的必要”。牟氏承認,在他年輕時,卻也對主體、道德、宗教、歷史、文化的價值論抒反感,謂之“百姓日用而不知”,但后,才會正視之;謂之“落寞而不落寞的超越”。可見,連牟宗三,也不是沒有受到泛科學之潮之襲擾的。
牟氏之所以看重懷特海,實出于懷特海將主、客體一并細查的哲學特征,這一特征帶來了(或許!)東西哲學主、客體兼容的可能。用M·懷特《分析的時代》一書關于懷特海的文章標題看——《自然與生命:阿·諾·懷特海》——即可得知懷氏哲學較之海德格爾們的主體意識并不弱。“懷特海在所有人們的心目中同時具有三方面的人格——邏輯學家、科學的哲學家和形而上學家。”這位被稱之為“試圖在獅子自己的鬃毛豎立的獸穴中捋住唯智主義、唯物主義及實證主義的獅子的胡子的英勇思想家”,“極似一個邏輯的和科學的罪人轉回到形而上學的教會來一樣”,使分析哲學進入頗似柏格森的突創進化論——普魯斯特的憶年華逝水的經驗論上去。以至牟先生說,懷氏之范疇,“數學秩序、永相、緣起事、攝受、主觀形式、創造、潛能、實現、真實、現象、客觀化、滿足化、連續、不連續、個體性,等等,一起融組而為一,成一莊嚴美麗之偉構。……故既為內在的,又為外在的,既為內容的,又為外延的。義如前述。”這種思維恐怕是牟宗三將中西哲學觀點迥異所做的一次反其道而析之。西哲之本體論的特征其實須臾也不離開他們的客體哲學或曰自然哲學。一方面,科學史上的陳述屢屢被驗證、被運用、被提升,是使科學哲學之語系受到肯定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這種泛科學、泛生產力的學說在宗教與道德方面,在人的存在及其異化方面留下的巨大裂隙,也已引起西方智者們的注意與關懷。人們一方面看到外延論證的碩果累累,另一方面則從科技帶來的異化——以及終極關懷里的設問,卻始終未得解決。雖然海德格爾洞悉了語言的本體論存在,由他之口說出了“語言說出了我們”——但在終極的意義上,是誰說出了語言呢——“我們”受制于話語的本體論,不能超越而訴諸于詩性——但在中國,在東方,圣賢之士不是不斷以“我們”——主體的位置,使“語言”得以說出嗎!綜觀外延——內容的不同探究,是誰讓中國人說出了語言,抑或應當像維特根斯坦或以后的德里達、富科們那樣,否定這一說出語言之“主體”呢!牟宗三先生起碼沒有做過這種并連的思索與反省。問題在于,其一,懷特海(含海氏、郭氏……等等)是否解決了外延與內容之悖論?其二,如果撇開西方人對語言與陳述所表達的悖論,中國人的求仁得仁的“天問”的姿態是否也應當受到懷疑;故此三,如若如此,中國哲學及其傳統文化,就非但沒有了民主與科學,其內容性真理也就會受到實質上的否定——如此一來,人們只能轉回到對于西方之內容真理的考查之上,惟其如此,人們才能獲得對于中國哲學之內容真理的最終反省之結果。于是,人們可以聽到這方面的一些聲音。
一如法蘭西一度聽到過三響鐘聲(自由、平等、博愛)一樣,中國文化的三位一體即儒釋道的文化生命有無發展,是否要汲取基督教之文明,而后經過“刺激摩蕩”而獲新的發展,則成為中國文化向何處走的最大回應與挑戰。這種摩蕩在佛教傳入中國后,經千年之考驗已獲成功,耶教東漸與中國化之可能性究竟如何?確為一個偌大之疑詰。況且,西方現代哲學,多含有對于基督之挑戰;固然,他們也并不能在哲學與宗教之高度上,回答牛頓的第一推動力的設問,從而解釋“為什么一切物體相互吸引”這一致命的一問。又,固然,《等待新上帝》(現譯《等待戈多》),“以最無可忍受的方式表達了存在于一個漫無目的的世界上的人的虛無感和孤立感”。然而,人,知其必死而仍要活——這一海氏的命題,現在,抑或可以改為,人,知其上帝已死(或必死)而仍要活。從外延、內容,一元、二元論言,人的思維狀況并不會達至無論是西方詩人還是中國詩人所創建的“棲息地”——因為上帝與人必死——詩意的去蔽難道可以惟獨意外嗎!所以,一如牟氏所言,中國人在堅持其內容真理之外,尚應“吸收西方的科學、哲學展開智性的領域”——此為“中國哲學的未來”。于是,以后人的處境追步前人,以中國人的處境追步歐美,成為中國人時下不得不做,不可不做之事——而在進入或必將進入西方之科學、民主新階段的中國人,同時又面臨著他們的抉擇——一是,是否同時否定自己創造的內容真理,抑或接受西方的內容真理,抑或合璧之——二是,是否能夠兼顧這形而上與形而下、言說與無可言說、外延與內容之真理——而非求下而棄上。
讓我們以羅素評定留卡爾的一句名言對上述“二元”論做一個結語,算做對于拜讀牟宗三先生的感言吧!
“笛卡爾身上有著一種動搖不決的兩面性:一面是他從當時代的科學學來的東西,另一面是拉夫賴士學校傳授給他的經院哲學。這種兩面性讓他陷入自相矛盾,但是也使他富于豐碩的思想,非任何完全邏輯的哲學家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