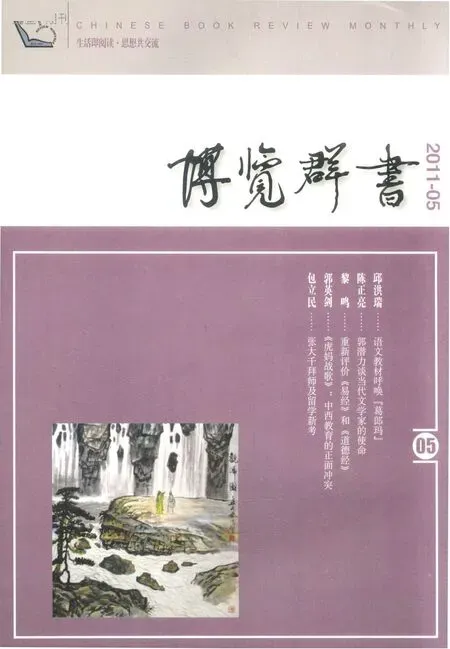談談《20世紀的俄羅斯與中國》
菩合
去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世紀的俄羅斯與中國:兩大民族及其領袖們》叢書,是作者于1998年底脫稿、隨即被中國學者譯出的。它反映出俄羅斯學者對中俄關系的最新觀點。
作者尤里·米哈伊洛維奇·加列諾維奇,歷史科學博士,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從事中俄關系史和中俄關系發展預測研究,還擔任俄中友協副主席、俄羅斯科學院漢學家協會副主席等重要的社會職務。《20世紀的俄羅斯與中國:兩大民族及其領袖們》叢書(下稱《俄羅斯與中國》)包括《尼古拉二世與慈禧列寧與孫中山》、《兩大領袖:斯大林與毛澤東》、《兩個一把手:赫魯曉夫與毛澤東》、《勃列日涅夫與毛澤東戈爾巴喬夫與鄧小平》、《世紀之交的俄羅斯與中國》等。叢書以兩國領導人的交往為線索全面闡述近百年來的中俄關系的歷史,并試圖以史為鏡來探索中俄兩大民族友好相處的途徑。
叢書《20世紀的俄羅斯與中國》以中俄兩國關系中的民族利益問題為核心,以中俄兩國最高領導人的交往為線索,揭示了從19世紀末至1997年江澤民訪美(中美俄新三角關系的建立)兩國在最近的一個世紀內相互交往的歷史過程,是迄今俄國學者撰寫的最為完備的一部中俄關系史。前蘇聯時期的學者們撰寫的中蘇關系史(例如:賈丕才的《蘇中關系(1917—1959)》、羅滿寧等人的《蘇中關系(1945—1981)》等)的共同特點是以意識形態為主線,以蘇共對外政策原則為基準,闡述和評判中俄關系的歷史。加列諾維奇的這部叢書完全突破了意識形態框架,緊緊把握住影響中俄關系發展變化的核心——中俄兩大民族在近百年來相互交往中的民族利益問題——展現中俄關系的全過程。這是加列諾維奇這部叢書的最大特點。
在前蘇聯時期這一中俄關系史的特殊階段(筆者認為中蘇關系是中俄關系的組成部分,與加列諾維奇教授的觀點一致),貫穿于這一階段的雙邊關系表現為中蘇兩黨之間和中蘇兩個國家之間的關系。在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執政地位之前,中蘇兩黨關系和中蘇國家關系從總體上看是相互背離的(在個別情況下也有相一致的時候),但在1949年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以后,中蘇兩黨關系與中蘇國家關系完全是一致的。當然國家關系更直接地反映出民族利益要求。黨際關系在反映民族利益要求方面就比較間接(特別是反映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相互關系方面更是如此),有時還出現與民族利益相背離的現象,但這種背離是短時間的,最終黨際關系還是要回到符合民族利益要求的軌道上來。中蘇關系的實際情況就是如此。加列諾維奇教授將中蘇國家關系作為體現兩國民族利益的主線并較充分地闡述中俄兩大民族的利益關系,給人以許多啟發;而對中蘇兩黨關系與兩國民族利益有時一致、有時背離的復雜情況沒有展開分析,無疑是個缺憾。盡管有此缺憾,加列諾維奇所構筑的中俄關系史研究的新框架仍然是一個重大突破,對中國同行仍不失借鑒意義。
叢書的第二個特點是作者注意將中俄關系史的一些重大事件置于當時大的國際背景下進行綜合分析。二戰后形成的以美蘇為首的兩大營壘的相互關系是影響世界各種國際矛盾發生與演變的基本因素。離開了蘇美關系和中美關系,發生在中蘇關系中的許多重大事件就說不清楚。加列諾維奇分析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蘇聯對美緩和政策和中國對美強硬政策(在臺灣問題上)對中蘇關系的影響,特別是對60、70年代越南戰爭對中蘇關系的影響分析得比較透徹。當時越南是中蘇的共同盟友,中蘇都支持越南抗美戰爭。正是這個共同盟友的牽制,使惡化了的中蘇關系沒有走到最終絕裂的地步。換句話講,也就是美國的對越政策(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國對華政策和美國對蘇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蘇關系不戰、不和、不決裂的僵持狀態。由于作者注意多邊關系的分析,就使迭宕起伏的中蘇關系顯現出較清晰的脈絡。
叢書的第三個特點是,中俄史料并重。作者大段大段地引用中俄雙方的史料和論著(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俄羅斯新近解密的檔案文件;還有一部分是作者作為中蘇關系一些事件的參與者和見證人的身份提供的親身經歷和感受),然后得出自己的結論。盡管作者所引用的一些中文出版物遠非嚴肅的科學著作,對一些相互矛盾的記載、甚至完全失真的史料缺乏必要的辨析,導致所下結論失之偏頗。但是像作者這樣系統地、而不是斷章取義地大量引用中方資料,是在蘇聯時代以及當今的俄羅斯公開出版的著述中未曾有過的。作者這樣做顯然是為了表明自己所做出的結論具有客觀性,同時,也可以讓讀者在系統地閱讀中俄雙方的有關記述中得出自己的結論。能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除了作者有面對各種與自己不同的觀點的勇氣外,還需要有深厚的中文功底,更需要花大量時間和精力去做艱苦的閱讀和翻譯工作。沒有像加列諾維奇教授這樣的學歷和工作經歷的人,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