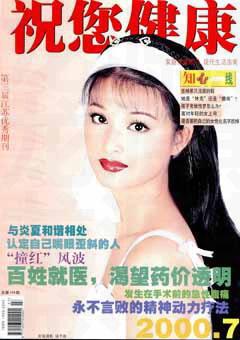面向新世紀的神經外科
趙繼宗
在即將和我們告別的整整一個世紀里,神經外科作為一門新興的臨床學科,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繼而迅猛發展的過程。世紀之交,展望神經外科發展趨勢,可以預見:這一學科必將適應時代潮流,以醫學模式的轉變為底蘊,與其他學科更緊密地結合,并不斷引入各種現代高科技成果,從而使神經系統疾病的治療不斷獲得突破性進展。同時,隨著人們對腦功能的深入探究,相信在新世紀中神經外科必將成為生命科學的前沿學科。
醫學的發展是以自然科學的發展為基礎的。層出不窮的新技術將使下個世紀的神經外科發生質的飛躍。綜觀近幾十年神經外科技術發展趨勢,諸如計算機斷層掃描(cT)、磁共振(MR)、正電子掃描(PET)等檢查手段以及導航、血管內介入等治療手段,究其根本而言,都與計算機技術的應用密切相關。在下個世紀,神經外科手術導航系統將更趨完美,檢查手段(影像)和治療手段(手術)可以合為一體。神經外科醫生能夠在磁共振或其他實時動態影像的直接引導下,隨時確定病變的切除情況,使顯微神經外科手術更準確,損傷更少。各種新型人工智能化的手術器械將使手術在計算機的控制下完成,真正做到微創傷甚至無創傷。結合高速網絡通訊技術的發展,遠程會診將由單純的診斷擴展到遠程手術指導。高水平的診斷和治療技術可以跨越地域限制,使更多的病人受益。
神經系統疾病基礎研究也將不斷出現新的突破。神經纖維瘤、顱內海綿狀血管瘤的神經遺傳學病因研究,已證實了特異性基因缺陷和變異。帕金森病、顱內動脈瘤、老年性癡呆、癲癇的基礎研究,也正在不斷推動臨床診斷和治療的發展。遺傳工程的啟動拓寬了顱內惡性腫瘤的治療手段,使之遠遠超出傳統的手術切除、放射治療以及化學藥物治療的范疇。
微電極刺激器的發明以及神經生長因子的廣泛應用,給膀胱功能障礙、性功能障礙(陽痿)的病人帶來了提高生活質量的希望。失去視覺或聽覺功能的病人也將會重見光明,再次聽到小鳥的歌唱。以往因脊柱損傷而導致肢體癱瘓的病人很難有康復的可能,這給病人帶來嚴重的身心損害,給其家庭和整個社會都造成沉重的負擔。最新研究成果已證實,人的脊髓神經纖維像其他組織一樣,同樣具備再生功能。神經科學家已經發現了多種能夠增強再生能力的細胞因子和神經生長抑制因子的拮抗劑。如今,在動物試驗中這些藥物的療效已經初步得到驗證。相信使截癱病人重新站立起來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了。
隨著功能核磁共振(f-MRI),腦磁圖等大型神經功能檢查儀器的普及與完善,臨床醫生將在治療腦和脊髓病變的過程中進一步認識中樞神經系統物質結構與功能的關系,從而使包括記憶、思維在內的認知功能的研究出現飛躍。多年來人們一直認為,隨著年齡的增長或疾病與外傷的損害,神經細胞將逐步凋亡,從而導致肢體殘疾,記憶喪失,意識消亡。近年的研究表明,動物的腦中含有一種原始的胚胎干細胞,如果將其移植到有病變的腦中,這類細胞可以逐漸分化,進而替換受損傷的腦細胞,構建起新的神經網絡。另一方面,低溫技術、免疫學、器官移植技術不斷完善,可使人腦移植不再只是科幻小說中的專利。
新世紀中,納米技術肯定會給神經外科醫生帶來各種超精細的手術工具。納米科技涵蓋物理學、化學、電子學、材料科學、微電子技術、計算機以及生物學等諸多領域,正以超乎常人想象的水平飛速發展。人們正在積極研制各種納米級的電子芯片,希望能夠制造出體積比人的細胞還小的電腦。僅僅相當于1米的10億分之一的納米級微型機器清道夫將直接進入人腦深處,疏通堵塞的血管,消滅可惡的細菌;或者像螞蟻搬家一樣,不知疲倦地把腫瘤從腦內搬到體外。進一步發展下去,也許會出現可以在分子水平上治療疾病的基因手術刀,或者是能夠自動修復細胞結構缺陷的分子機器人。等到那一天,包括外科手術在內的各種傳統醫療手段都成為歷史,醫學觀念將徹底改變。神經外科醫生將告別手術刀,在虛擬現實中完成對病人的治療。您能說這些都僅僅是美好的幻想,可是在100年前,人類登月不也只是幻想嗎?
在這個信息的時代,先進的技術成果可以在世界范圍內迅速地推廣。常見的神經外科疾病會有統一的診療行為規范。目前歐美、日本等國建立的顱腦損傷救治指南,已顯示出診斷、搶救和治療上的優勢。這不僅使專業醫生有章可循,同時對相關的專業和學科,甚至對社會醫療保險部門也有指導意義。我國也將會制定出與國際接軌、并適合我國國情的各類神經外科疾病診療指南。
社會文明不斷進步,使得病人的診療思想和要求也發生著相應的變化。現代醫療模式正在由單純生物學模式向社會一心理一生物醫學模式轉化。醫學倫理學觀念不斷更新,人文關懷將貫穿疾病治療的始終。神經外科疾病手術治療后的并發癥有時相當嚴重,甚至會影響病人的遠期生活質量。這就要求臨床醫生正確評估疾病對病人生存及生活質量的影響。治療究竟會給病人帶來什么?這是每一個步入場券新世紀的臨床醫生需要深深思索的問題。
新的世紀中,我國醫學界面臨著另一個急待解決的嚴肅課題,即制定我國的腦死亡法規。在這項工作中。神經外科醫生將擔負起重要角色。隨著現代醫學的飛速發展,臨床死亡的概念由50年前的呼吸心跳停止為標準,演變為當今以腦死亡為根本依據。腦死亡概念的提出,是對傳統的死亡概念的極大挑戰,標志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的進步。同時從醫學倫理學來講,也表現著對死者的尊重。研究表明,病人呼吸停止、出現不可逆性深昏迷、腦電圖呈直線和腦干反射消失后,即已處于腦死亡狀態,和外界的一切交流已不復存在。盡管在一些機器的支持下,沒有任何意識的病人可以被裝上各種管道,并使用大量昂貴的藥物,繼續維持呼吸和心跳,但從社會學意義上講,這樣的人無疑已經失去了生命。如果能夠確定腦死亡的標準,在病人生前表明意愿的前提下,腦死亡病人的健康器官可以及時用于器官移植工作,從而挽救眾多病人的生命。因此,腦死亡法規的制定是一項有利于全社會的工作。在制定腦死亡標準,界定腦死亡時間,確認腦死亡程序方面,神經外科學都大有作為。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的世紀將為神經外科學的發展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掌握了現代科學技術的醫務人員將盡情展示自己才華,促使人類文明向更高的一個階段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