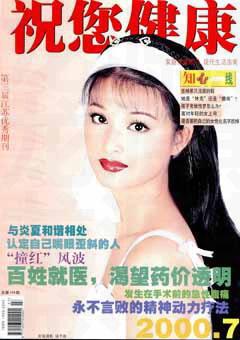實話實說無償獻血
王寧武
1998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以下簡稱《獻血法》)正式實施,我國從這天起步人了無償獻血的新階段。一年多來,全國基本上實現了由有償獻斑向無償獻血的平穩過渡。但是,由于傳統觀念的影響及其他一些原因,全國各城市及城鄉之間的有償獻血發展并不平衡,以江蘇省為例,全省1999年無償獻血305895人次,獻血量6207.34萬毫升,占臨床用血的39.95%,其中市區占51.8%;縣(市)僅占28.11%。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春生前不久說:“《獻血法》第一次在我國從法律上確定了無償獻血制度,肯定了無償獻血的方向,確定了一個基本原則,但從實際情況出發,在全民范圍實現這項制度還需要一個過程。”
無償獻血中的“有償”現象
上海市于1989年便通過了《上海市公民義務獻血條例》,這是我國第一部地方性獻血法規。在我國《獻血法》開始實施時,經過修改后的《上海市獻血條例》也同時生效。上海人民通過實施獻血法律、法規,基本解決了這個平均每天用血20萬毫升的大城市的血源問題。上海模式的特點是有計劃地組織獻血,實行個人儲血、家庭互助、集體互助和社會援助的供血制度。
1995年,深圳市制定了我國第一部無償獻血的地方性法規。與上海市不同的是,深圳市強調獻血者的個人行為,即獻血者本人獻200毫升血,便可獲得終身享受免費用血的“回報”。1998年在烏魯木齊市召開的全國無償獻血經驗交流會上,與會者對這個平均年齡只有28歲、知識層次高、用血量低的城市的獻血政策普遍感到可望而不可及,感慨者多,效仿者甚少。但是可以肯定,深圳模式正是我國開展無償獻血的方向。
《獻血法》頒布后,許多城市和地區借鑒了上海、深圳的經驗,走出了一條計劃組織獻血與街頭流動采血車采集自愿者血液相結合的道路,被稱之為第三種模式。如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組織大、中型廠礦企業的人員前來血站獻血,同時又在南京市的繁華路段,建立起了流動采血點。據統計,1999年南京街頭無償獻血24766人次,占整個無償獻血群體的53%,2000年街頭無償獻血率正在繼續上升。
同南京市一樣,目前我國許多城市采取了計劃集體獻血和個人自愿獻血相結合的方式,雖然這都屬于無償獻血范疇,然而輸血界人士指出,參加集體獻血的獻血者可以獲得所在單位的補貼和休假。因此有人認為,集體無償獻血的補貼實際上是把血站原來付給有償獻血者的錢轉給了獻血者所在的單位。然而事實上,絕大多數單位發給獻血者的錢,已是過去血站在有償獻血時期發的錢的數倍乃至幾十倍。
上海的計劃性獻血對上海的臨床用血起到了保障作用,然而街頭無償獻血的人數卻與這個國際化大都市極不相稱。一位上海市民對筆者說,上海每個單位都有獻血任務,在單位參加一次獻血可以獲得3000元補助,而在街頭采血車上獻血卻沒有任何補助。上海血液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員也證明了這一點。他說,目前,計劃獻血比較好的城市都存在這種情況,像北京和大連,這顯然于真正意義上的無償獻血大相徑庭。
對于完全取消計劃獻血而依靠公民的無償獻血,大部分大中型城市的血站站長持否定態度,理由很簡單:條件尚不具備。這是因為,一方面,街頭無償獻血的人數從一定程度上依賴于天氣和氣候;另一方面,由于參加街頭獻血的相當一部分是大中專學生,每年的寒暑假和學生考試期間,街頭獻血人數都會下降,這期間還需要計劃獻血來補充。由此看來,無償獻血中的“有償”現象還將持續相當一段時間。
200毫升血液的價值
參加過獻血的人都知道,一次抽出的血量為200毫升,對于每獻一次血后的補助問題,《獻血法》明確規定:“對獻血者,有關單位可以給予適當補貼。”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釋義》一書,對此做了進一步解釋:“適當補貼原則上界定為少量、必要的誤餐費、交通費等費用。”但是,許多單位對獻血者的“適當補貼”成了必須的變相補貼和高額補貼。
1999年4月的一天,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年輕姑娘借來南京出差的機會,在街頭采血車上獻了血。姑娘告訴筆者,她是無錫人,在南京大學上學時曾參加過無償獻血。她還說,這次才是真正的無償獻血,她如果在北京的單位參加“無償獻血”,可以拿到3000~5000元的補貼,有的單位甚至獎勵獻血者到新馬泰一游。據了解,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的有些企業對獻血者的補貼,已從幾十元發展到上千元,甚至幾千元,這給大、中型企業造成了很大的負擔,而且其中也出現了許多不正常的現象,這與《獻血法》中所強調的無償獻血的初衷相背離。
鮮血一旦受經濟利益的驅動,便會嚴重污染血液這條神圣的生命之河。在今天無償獻血尚未滿足臨床用血需要的情況下,輸血安全可以說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一名河南男子,為了獲取某建筑單位的400元獻血補助,假冒別人的名字獻血,在抽血前的檢查中,被檢出為艾滋病病毒攜帶者。
珠海某公司7名員工因化學物品燒傷,經廣州某醫院輸血搶救后不久,7人均出現黃疸、食欲不振等癥狀。檢查結果表明,他們均因輸血而被傳染上丙型肝炎。
更令人痛心的是,山西省臨汾市少年宋鵬飛,因外傷住進臨汾市某醫院,由于手術需要輸血,住在醫院附近的“血頭”李某很快帶來了長期靠賣血為生的文某,誰知文某是一個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輸完血后,李某和文某分別得到了血費提成和賣血費,而宋鵬飛卻被感染上艾滋病病毒。
血液,生命之源泉,只有割斷了與金錢的關系,才能使生命從枯萎中綻放出鮮艷的色彩。據調查,在無償獻血人群中,丙肝感染率為1%左右,而在職業賣血者中,丙肝感染率要比無償獻血人群高出幾倍,甚至十幾倍。由于受檢測試劑靈敏度和經血液途徑感染疾病“窗口期”(指獻血者在感染了丙肝、艾滋病等經血液途徑傳播的疾病后,用目前的檢測方法尚不能查出的一段時期,一般為1~3個月)的影響,血液檢測的漏檢現象難免發生。從國內對艾滋病病毒抗體的檢測情況來看,漏檢率為0.55%。由此可見,不治本堵源,不改變有償供血,不加強血液源頭的管理,血液質量將難以保證,臨床用血者的安全將受到嚴重影響。
人的生命是無價的,血液是生命的組成部分,因此血液也是無價的。獻血者獻出的血應該無法用金錢來衡量,人道主義的崇高精神是用金錢無法買到的。
街頭采血車——真正無償獻血的象征
將街頭作為無償獻血宣傳的窗口,持之以恒地堅持以此為主要采血渠道的是深圳。隨著《獻血法》的頒布,街頭流動采血車、流動采血點在各城市如同雨后春筍。山東省青島市政府十分重視無償獻血工作,他們為血站配備了12輛流動采血車;江蘇省蘇州市血站在繁華的街頭修建了“獻血屋”;山西省太原市血站“大篷車”式的獻血屋成為當地一景;南京市血液中心的流動采血車被新聞媒體譽為“精神文明的風景線”,等等。在全國各血站和流動采血車上,許多人對無償獻血表現出了極大的熱忱,默默地奉獻著一片愛心——
1999年12月下旬的一天,大雪飛揚,南京的氣溫降到-10℃,這是南京近年來最冷的一天。一對夫婦特地領著孩子來到流動采血車上,他們對醫務人員說,今天是孩子18歲生日,意味著他已長大成人了,我們贊成他參加無償獻血的主意,為社會盡一點責任。
南京市第一輛流動采血車是1998年11月啟用的,然而采血車去的第一個目的地不是街頭,而是市政府大院。原來市政府武警國旗班的退伍老兵們,在臨行前有一個共同的心愿,就是為南京人民獻出自己的一片愛心。
不是每一個獻血者都帶著笑容離去的。一位來自某縣城的女學生,當被告知未滿18歲不符合獻血條件時,她竟傷心地哭了。當血站的同志勸她獻愛心也可以通過其他形式,比如向災區人民捐款等,這位姑娘卻說,我捐過錢,可實際上捐的是爸爸媽媽的錢,而血是我自己的。
隨著街頭采血車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人們的眼前,也有人對街頭獻血產生了疑慮:平時到醫院進行抽血檢查,要三四天后才能得知化驗結果,而在采血車上驗血,20分鐘就可以知道結果,這么快的檢測準確嗎?血的質量符合要求嗎?
為了針對街頭無償獻血的特點,現在的采血車上只化驗血色素、血型和乙型肝炎。目前醫院使用的酶聯免疫法和反向間接血凝法檢測乙肝,需2小時后才能知道結果。而采血車檢測乙肝使用的金標法,是一種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檢測法,靈敏度高,一般20分鐘后就可知道結果。除此之外,各血站對街頭采血車采回來的血,還要進行甲肝、乙肝、丙肝、梅毒和艾滋病病毒的檢查。不合格的血液將被淘汰,絕對不會進入臨床使用。
獻血是愛,是勇氣,是奉獻。讓我們在消除附著在血液上的種種污染后,在國家提倡無償獻血的同時,獻出自己心中的真善美,讓我們的國家更加美好,人民更加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