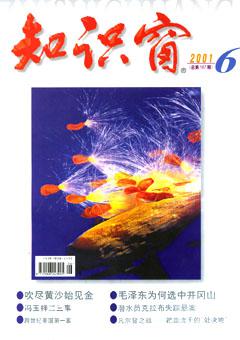美國乞丐千姿百態
孫紫玲
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同樣有不少行討的乞丐。在街道上、地鐵里,或道路交叉處,這些乞丐們逢人便說:“我是殘疾人,生活無著落,給25美分吧。”讓人一看,憐憫之心油然而生。
芝加哥最常見的是老年乞丐。冬天,他們身穿不足御寒的破舊衣褲,老頭戴頂過時的舊帽,老太披條雜色圍巾,三三兩兩蜷縮在街心公園或立交橋頭瑟瑟發抖;一見行人走近立即伸出顫抖的手,用一種“沉默”的方式乞討。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我看見一個70多歲的老太太在超級市場外翻垃圾袋,她將罐頭盒、可樂瓶放入大提袋,將過期的面包、香蕉等放進手提包,甚至迫不及待地剝塊撿來的巧克力放入口中。紐約中央公園假山后的樹叢旁、拱橋的涵洞里更是乞丐喜歡棲息的地方,被美國人戲稱為“無家可歸者的天堂”。即便是華盛頓白宮前的長椅上也常躺著衣衫襤褸的乞討者。那些露宿在哥倫布公園的老年乞丐,披著一頭白發向人們訴說著世事的滄桑,他們往往一呆就是幾個月。
我看到不少中青年乞丐,乞討的方式是舉著牌或胸前掛塊厚紙板,上面寫著“尋求幫助”、“我要錢”、“無家、餓、幫我”之類的文字。有時,他們突如其來弄得你措手不及。一天傍晚,我走在曼哈頓的大街上,突然,一個男子轉身朝向我,敞開的衣襟內露出一塊紙牌:“退伍軍人、無家、我要錢!”我曾不止一次聽說過大街上發生的搶劫案,嚇得心怦怦直跳,無暇去想他的真實真份,趕忙掏出早已準備好的5美元,直到身后傳來“Thank you”才讓我稍感平靜。
美國還有一些變相的乞丐,比如你開車出去,十字路口遇到紅燈,便會有人一手拿著盛水的可樂瓶,一手拿塊抹布,迅速地替你擦幾下擋風玻璃,隨即向你要錢。車站、碼頭、地鐵入口處或超市門前,一些賣藝行乞者或彈或唱或跳,這些人有的是出自對藝術的愛好,有的是用這種方式解決溫飽問題。1999年5月,我在加州好萊塢大道看昔日影星的足跡,影院前有一卓別林的扮演者頻頻向游人招手,我上前和他握手問候。他要求與我合影留念,而這正是我所愿意的,但攝影后他向我索要了10美元。
美國還有一種超級乞丐,他們有住房,衣食不愁,沒有酒喝的時候,就在行乞牌子上寫著“我需要啤酒錢”、“請給我一瓶啤酒”,有趣的是酒丐行乞所獲遠比其他乞丐多,因為美國人認為乞食的太無用,連起碼的工作都找不到,而酒丐只是暫時的困難,救急不救窮嘛!
美國乞丐不少,也就出現許多為乞丐服務的機構。為了救助最貧窮者,加利福尼亞洲的柏萊克發行了一種換取物品的“慈善券”,代替現金散發給乞丐,券上印著“可換食物、汽油票或支付洗衣費,但不能用來購煙酒,也不能當現金使用。”為了提高乞丐的乞討能力,紐約還辦了個“乞丐學院”,學制6晚,收費100美元,前4個晚上學習行乞的理論知識,后2個晚上到街頭實習,院長親自在旁邊進行觀察,指出不足的地方,并加以輔導。據院長介紹,成績優異的畢業生每月可乞到2000~4000美元。35歲的洛杉磯企業家米克·普拉布林還推出了《行乞套餐》一書,包括行乞指南、行乞裝備和行乞衣物。該書作者保證任何有志于行乞人士只要熟練掌握書中理論,配備必要的行裝,保證每年可乞到3萬美元左右。
行乞界甚至還產生了一些不同凡響的人物,如乞丐頭目南哥麗芙姬對群丐說:“富人靠積累財富去旅游,我們可以靠行乞去旅游。”她的倡議立即得到眾丐響應,于是,她組織了一個189人的“乞丐旅游團”從紐約出發,第一站到意大利,繼而是法國、德國、挪威、瑞典和芬蘭,前后240天,其中行乞141天,實際旅游99天,這群身無分文的乞丐們竟瀟灑地飽覽了各國的秀麗風光和名勝古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