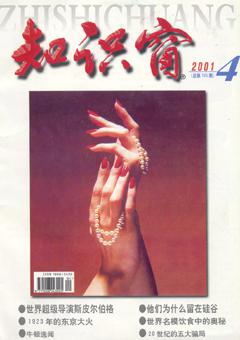讓自己坐進自己的懷里
何西風
面對山姆大叔的文化入侵,芬蘭人急忙舉起自己的“文化內容創作計劃”。
難道中國人就只能追捧可口可樂之類的舶來品。而沒有自己的文化產業嗎?
說起信息產業,人們馬上會想起網絡,而說到網絡,人們又無不注意到它面臨的最大問題——內容貧乏。幾年來網站建了一撥兒又一撥兒,但其中究竟有幾個能讓你難忘和迷戀?如今我們有了日益松快的帶寬和廣大的信息平臺,那么帶寬上走的和平臺上放的該是什么?一句話,當眾人盡情歡呼信息技術產業正在把我們帶入美妙的“應許之地”時,我們可有誰在那塊土地上看到了期待中的大片葡萄園——文化產業呢?
SiSu:芬蘭構筑的文化防線
北歐的芬蘭只有幾百萬人口,但那滿世界打著“科技以人為本”廣告的“諾基亞”,卻是國際信息技術領域中的翹楚。諾基亞的技術讓芬蘭人驕傲,但其巨大網絡所承載的內容卻是一水兒的美國文化產品,至少也是被美國人包裝過的本地文化產品!
且不說作為網絡世界普通話的美式英語,單是無數的美國網站和電子雜志、美國廣告和歌星影星臉譜、美國公司制作的影視音樂,就讓原本很傲慢的北歐人覺得丟不起那人——要知道,在西北歐的傳統語匯中,“美國文化”就是“沒文化”!
說美國文化粗鄙,那還只是個口味問題。但若說到美國文化產品充斥本國文化市場,那就是個關乎一個民族精神家園的“生存還是毀滅”的大問題了。為此,芬蘭政府在1997年公布了一個文化產業研究項目,它有一個特別便于記憶的芬蘭名字——SiSu,即“內容創作啟動計劃”。
在發達世界的第二集團中,芬蘭還不是動作最早的。早在1992年,法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國就制訂了國家文化產業發展計劃。但芬蘭人的危機感似乎更強,并且最能喚起歐洲人的普遍共鳴。
如今,SiSu已不再是芬蘭人一家的計劃,它已成為歐盟成員國的“框架性合作項目”,成為美國之外的許多西方發達國家的便帖。它貼在網絡上,貼在報刊上,貼在每個國家的年度發展報告里。這些文字中只躍動著一個主題:拯救文化——通過發展本國的文化產業來拯救自己的文化。
這種拯救意識顯然來自強烈的危機感:可口可樂已經漫過了他們的軀干,現在美國的娛樂產品終于要淹沒他們的頭腦!要逃過這種命運,不僅要有“諾基亞”,還要有打上自己印記的文化產品!
不難看出,在歐洲、澳洲和北美的加拿大,文化產業“首先是作為一種針對美國的對策而出現的”。這是發達國家對最發達國家的抵抗和防范!在那些歐洲人眼里,民族文化像一只易碎的玻璃杯,為了保護這只原本用來喝水的杯子,所以要搞SiSu,想方設法舉高那只杯子,讓它不至于被擠碎。
美國沒有文化部
美國人不搞SiSu。美國文化是只大塑料杯,不怕擠,極易復制和批量生產。多少年來,隨著可口可樂流淌到全世界的,不僅有好萊塢大片、迪斯尼的卡通形象、華納灌制的唱片,還有自命為用一個聲音傳達所有聲音的美國之音或CNN、美國《財富》或《時代》雜志以及麥當娜或杰克遜那特有的音樂動作。
截止到2000年,全球互聯網有60%以上的內容來自美國;美國傳媒娛樂業產品已超過波音公司的飛機,成為第一大出口行業;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電視臺和網站其實只是美國視聽產品的轉播臺或連鎖店。
美國是個文化產業的超級大國。但奇怪的是,美國居然沒有文化部,他們的媒體也不提文化產業,這倒不是因為他們“沒文化”,而是因為他們一開始就關注著文化的產業化、市場化,讓文化坐在市場的懷里。結果,市場做大,文化生產能力也被隨之做大。
好萊塢、迪斯尼、寶麗萊,這一切帶來的不僅是可供人們歡悅一時的視聽比薩,也不僅是一些光怪陸離的時尚,而是世界上多數國家中的多數人對于20世紀的基本記憶。一句話,20世紀市場的高度決定了美國文化產品制造業的居高臨下之位勢,這恐怕不能簡單地以文化殖民主義的動機來加以詮釋。
所以,要生產出高水平的文化產品,固然要有高技術手段,如昂貴的攝像機、錄音棚或通道寬大的光纖纜,更要有一個尊重消費者需求、充滿競爭活力、法規嚴格透明的市場。
在這里,文化產品的生產者不是消極等待著顧客訂貨,顧客要什么才生產什么,他們的活力在于創造產品的同時也創造著顧客的需求、品味和時尚。這種生產和營銷本身就與藝術創造相似,他們導演著顧客,導演著文化消費的世界。它們最后嬗變為一種文化權利或權力!
2000年初,美國在線與美國華納公司實現組合,人們在關注高科技與高文化這兩大要素的強勁組合時,更把目光聚焦到了納斯達克股市。那里不斷向美國的文化制造業和信息產品業發出一個個脈沖信號,控制著那個龐大巨人。
在很多人心目中,技術、市場與文化的品格毫不相容,老派的歐洲人如此,我們的老派學者也多如此。深刻的人愛把美國產品稱為“垃圾”,無非是說它充滿了市場味或能令人聯想起市場的氣味,如漢堡包中的香料氣味、可口可樂中令人上癮的口味、還有迪斯尼或好萊塢中那或虛擬或現實的卡通味,他們特別能讓人上癮,所以很俗,很糟踐文化。
但反過來想一想,難道不正是這些味道,才使得文化消費區別于單純的食物吞咽或精神灌輸嗎?對比那些把美德詮釋得面目可憎的黑貓警長一類的娛樂產品,迪斯尼動畫這類在市場中長大的產品似乎更合乎人性:它們做的也是人類共同的純真美德和智慧,但卻訴諸節奏、趣味和想象,注重人的視覺、聽覺和口味的全面需求。
它們不僅以關懷人性為目的,而且本身就體現著對人性的關注。面對這樣的產品,孩子們是全無抵抗力的,即使是那些具備特有文化的成年人,不也充滿一種愛恨交織的情結嗎?成熟的市場告訴我們,消費者的偏好是無法強制的。所以,塑料杯越來越多,而玻璃杯越來越成為收藏品。
中國文化與美國的《木蘭》
中國文化是瓷杯子,同樣不經碰不經摔。在我們一向的信念里,文化就是教化,教化就是教育,教育就是育人,育人是百年大計——如此一來,文化一事便需特別鄭重和嚴肅。
在這個背景下,將文化產品產業化,讓人們習慣文化產品上那股子市場味和卡通味已屬不易,但如今偏偏又遭遇上了信息時代,大家緊緊張張忙乎了幾年,燒了幾年的錢,最后才發現這信息時代太邪門。
所有玩過一陣網站或音像制作的人都知道,在這個行當里,上“手段”容易,上“內容”難;挪用別人的文化產品容易,制作自己的產品難;一句話,花錢容易掙錢難!
這種狀況讓人感到意外。我們原以為只要掌握了信息技術,就可以擁抱信息時代,誰知半路竟冒出個文化產業問題!與這種“信息內容產業”相比,我們在信息技術設施方面所做的那些事,如鋪光纜、設網站、更新數字化設備等等,充其量只能算信息時代中鋪路
修橋的“粗活”。
尼葛洛龐蒂說,高速的信息管道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還是那里“上載”、“負載”或“下載”的內容。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最重要的是,那里負載的是何種內容、誰的產品。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文化產業的信息時代是不完整的。
面對山姆大叔的文化入侵,芬蘭人急忙舉起自己的“文化內容創作計劃”。
難道中國人就只能追捧可口可樂之類的舶來品,而沒有自己的文化產業嗎?
目前,發達國家正大規模地將文化遺產轉換成數字化形態,而我國各種文化資源的數字化水平還相當落后。在這個背景下,一些擁有大量文化資源的單位,如圖書館、博物館或文化遺址保護單位,便忙不迭地引進外來資金和技術,使自己的內容多媒體、虛擬化。
從技術的觀點來看,這是一種“文化的躍升”,但從市場和文化的觀點來看,我們更關注的是.經過別人的“數字化改造”,這些內容是否還是我們的資源?
對于花高價購買別人用我們的資源生產的產品,我們從來不乏體驗。君不見我國的《木蘭辭》硬是被美國人改造成日本女孩模樣的“木蘭”而風靡世界;國外唱片公司搶灘中國,讓中國歌手紛紛與世界接軌。這還僅僅是開始。看著大量文化單位熱衷于通過引進外資建立數據庫,我們擔心,不定哪天一覺醒來,我們只能手捧著美國版權的信息文化產品來“弘揚民族文化”。
簡言之,在文化遺產數字化和“介質轉移”過程的背后,有可能發生“產權轉移”和“資源轉移”,這是一個與我國經濟、政治、社會的未來發展有巨大干系的問題。
傳媒匯流:將世界一網打盡
前幾年,一位美國人寫了一本書,其書名變成了一個口號:數字化生存。我們由此關注0與1這兩個數字與我們生活世界的關系。最初,我們對這個說法的理解是,一切電器都已經是或者即將是數字化的,如數碼相機、數碼電視、數碼音響等等,更不用說電腦或保險柜了。
然而,我們客廳或廚房中出現的這一系列變化其實只是那波瀾壯闊的數字化革命的一點細枝末節。在信息業領域中,這個革命有一個響亮的名稱,即“傳媒匯流”。
所謂“傳媒匯流”,意思是把數字技術當作一切信息資源形態和媒體形態的基礎,為與信息有關的一切產業——無論它曾經多么傳統或原始——提供一個統一的平臺。
傳媒匯流的一個嚴重后果是,使許多以前各自為政的企業產生了“跨產業”、“跨平臺”、甚至是“跨部門”合作的動機。它由此對傳統媒體起到了一種“解放”作用:破除不同傳媒問的傳統壁壘,信息資源共享。這勢必引發傳媒業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整合和競爭。
在2000年以前,整個世界的信息傳媒領域,主要由9大傳媒娛樂巨無霸把持,排名前5位的是:美國時代華納公司(1998年銷售額285億)、美國迪斯尼公司(1999年銷售額234億)、新聞集團(1999年142億)、貝塔斯曼(1999年141億)、維康公司(1999年120億)。
從內容上看,這些公司長于新聞和娛樂內容制作。它們把持重要的電視頻道,掌控響當當的出版機構與報刊雜志,擁有遍布全球的連鎖品牌營銷系統,甚至舉辦重要體育賽事、經營著名主題公園……。隨著信息革命的到來,這些依賴傳統媒體經營文化內容的公司,開始與網絡企業合并。最著名的合并發生在時代華納與美國在線之間,經過1年的艱苦努力,兩家終于實現全面聯合,從而成為上述巨無霸中的“諸侯上將軍”!
國際傳媒娛樂業巨頭的出現,帶來了“范圍經濟效應”。作為制造、傳播、消費“文化符號”的特大型企業,各大傳媒娛樂公司日益成為“團塊式的”、超大型的實體。它們同時介入多種產業,往往是一種投入推動大量不同種類產品產出。
比如,迪斯尼制作一部電視,既可以將其在不同的傳媒上推廣,也可以同時制作該節目的副產品,出版有關的書刊畫報,建立主題公園,在連鎖零售店中出售與該節目相關的玩具或時尚物品,等等。它們還彼此互相參股(9大傳媒巨頭之間有2/3的業務彼此參股),既競爭又聯盟,令它們更易于將經營單一傳媒的中小企業擠出牌局。
在“范圍經濟效應”的作用下,傳媒巨頭的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時代華納集團2000年的國際市場收入已達到其總收入的40%以上,貝塔斯曼公司的國際市場收入已經超過其國內收入,默多克的新聞集團更是早已走出澳大利亞,在國際市場上翻云覆雨。
上述發展趨勢的結果是,由傳媒、電信、信息業的匯合產生了一個空前巨大的新興產業部門,成為全球經濟中的最大的和發展最快的部分。在這個產業領域里,以令人無法想象的速度與面貌誕生了一批空前絕后的“巨無霸”式的企業,正是他們推動著新一輪“全球化”的浪潮。
隨著“文化產業”這個話題的展開和深入,我們忽然發現窗外是一個十分陌生、但卻對我們影響甚大的世界。遺憾的是,過去由于我們只帶著單純技術的有色眼鏡,所以對它視而不見。如今看過去,我們不單感到新奇,更感到震驚。我們素稱文化大國,但我們的文化制作作坊在哪兒呢!
在冰冷的技術世界里,在優勝劣汰的市場環境中,我們寶貴的、唯一的、蘊育著民族情感的文化還需要呵護與培育。文化的失落是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都無法承受的失敗,我們面臨的挑戰實際上是根本性的!
“頭腦國家管思想,肌肉國家干粗活”,有人對知識經濟時代的新世界格局作如是推測。
信息產業的發展必須依靠綿綿不絕的創新動力和源泉,它包括技術創新、內容創新、制度創新。文化產業只有成為信息產業的“內容”才能煥發新的生機,而信息產業只有成為文化產業的操作平臺,才具有真實的價值。沿著信息技術革命開辟的大道,我們正在全面進入“內容為王”的時代!
讓自己的文化坐進自己信息技術的懷里,這就是我們走向頭腦國家的通行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