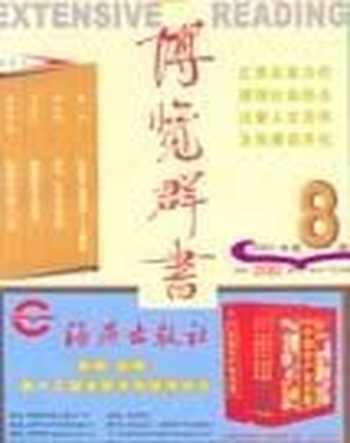來自草根文化的造詣
釋 然
在《博覽群書》雜志社主辦的會議上,筆者有幸接觸了傅謹先生的作品——《草根的力量——臺州戲班的田野調查與研究》。這本書說它是文學?報告?田野筆記?風格上的定位這一點并非問題的本質。該作品拋棄了狂想和多情,又增加了可供學術分析的厚度,另外,它也沒有停留在記者的那種單純的紀實性描述上。《草根的力量》究竟是什么?
我在陜北的田野調查中也遇到過與傅謹先生同樣的問題。中國的體制改革,使得地方的國營劇團也面臨著命運挑戰和選擇。他們采取了他們習慣的做法,即通過與他們簽約的村落,使劇團更加接近了草根。其中一個重要的角色是介于劇團和村落儀式(包括廟會)之間,穿梭于不同社區之間的中介人(陜北稱其為“寫戲的”——地方劇團與廟會或鄉間集市之間的經紀人)。表面上,我們看到的是娛樂,但在實際上,無需文字表達的諸多生活場景和情緒,在一方表演和另一方觀賞的過程中,得到了知識性的溝通和對話。這種面對面的生活方式,在老百姓的生活觀念中是值得信賴的,是高密集的、高質量的。
一、方法論
1、承認草根文化的存在和重視草根的力量。我們的一些學者為了表達自己的研究處于何等重要的地位,張口一個大中國,閉口上下五千年。他們忽略了表達學術思想的基本方法和邏輯。傅謹的《草根的力量》告訴我們植根于具體的社會脈絡中的那種草根文化的力量、草根文化的智慧、草根文化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重要的是,這一歷來被忽視或者干脆無視的草根及其土壤,在傅謹的眼力中具有它的可塑性,這一點不同于結構主義形而上的分析。因為它并不拘泥于既定結構的約束和國家力量的約束。人們盡其所能地發現自己的需求、表達自己的價值,營造適合自己社區生活的信賴系統。這些努力給予人們對自己社區生活的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認識機會,而且參與社區內社會生活的人們,都具有基于這種信賴系統,表達他們日常生活中的瑣碎需求的欲望。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草根的力量是原創性的,也是高質量的。與此同時,我們的認識是否真正地能夠在基于與外界隔絕的情況下進行,形成屬于自己的所謂價值體系?筆者仍然存有疑慮。在這一點上,傅謹的《草根的力量》告訴我們,劇團的活動客觀上參與了上述意義的社區建設。演員們也并沒有因為舞臺藝術化而使自己的思想脫離具體的社會脈絡。換言之,我們以往的“二元結構”的那種兩分法固然漂亮,但存在著嚴重的疏漏。他們的一個最為簡單的變通辦法就是,當出現問題時,他們寧愿修煉研究對象(別人),也不情愿修改自己的分析模式。
2、表述與理解:人類學研究的工作程序中不可想象沒有田野經驗,甚至體驗、學習異文化過程中的精神、心理和生理上的諸多冒險。如果平和地表述這一問題,那就是:對于我們既定的知識體系無法衡量的,異己的知識體系,如何表述和理解的問題。這不僅僅是書齋里的矛盾,重要的是學者研究之前既定的那個生搬硬套別人的分析框架,將筆下的人真正地寫成了“別人”。如果我們說這種意義上的“別人”具備客觀性的話,那么,神話里的任何一種東西都具備了客觀性。宇宙人在你研究之前就具備了完美的客觀性。我們有必要將一個天生具備客觀性的東西再用“另”一種所謂客觀性來重新表述一遍嗎?事實上我們人類,無論草根的力量還是宏大的敘事,都在不斷地從事著這樣一種努力——思考/認識/理解這一人為的事實,批評者也為此如火如荼。由于凝視事實過程中的認知作用,導致學者“不能自醫”的情景并不見怪。我的問題是,同專業不用說,跨專業“對話”性質的交流同樣需要講究一套方法(收集/表述/閱讀),即:它在一定的表述規則的前提下的開放性和可討論的余地。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偉大之處并不單純地在于他的研究成果,重要的是他給我們后者提供了令人再思考和為之實踐的命題,而且我們也沒有忘記,在科學主義式的工具理性之外,還有將馬克思的命題情緒化的沖動。
3、民族志:作者在自己的引言(方法與緣起)中反復強調自己在參與觀察過程中的所謂因自我意識而導致的“距離”感的側面。但我認為,比較起那些在調查之前就擁有某種模型或者框架,并依此觀察被研究者的學術活動和浮躁的作品來說,傅謹先生經過長時間的參與觀察,把握了被研究對象的行為和思維的問題,進而達到了觀察被研究對象的社會脈絡以及在這種社會脈絡中方能產生和成立的意義系統。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作者給我們提供了一部通過戲劇的社區活動來窺探國家與社會相互編制意義的民族志。關于民族志方法學方面,如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茨在印度尼西亞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中,給我們展示了在表面上看似賭博的“斗雞”游戲的深層,其實隱含著大量圍繞人格、威信、名譽的斗爭。這一研究對經濟學意義上的所謂“理性”提出了顛覆性的挑戰。正因這種草根的力量和相對意義上的距離感才賦予民族志以批評價值。
二、值得思考的問題
作為學術的對話能力,我們再看《草根的力量》。在方法上,除了作者強調的所謂“參與觀察”以外,本書缺乏嚴格意義上的概念體系的支撐和成為知識背景的方法論。這樣也就導致了作者的問題意識不夠明確。為了彌補這一缺陷,作者采取了翔實地描述過程的做法。我認為作者尚有兩個工作需要繼續進行。
1、對所謂“傳統”的梳理。傳統本身并沒有傳遞的功能,相反,作為傳統的載體的人類具備了這種傳遞的欲望和力量。筆者在信仰的研究中發現,人們帶著現世的問題意識,通過抽簽和解簽的形式,實現“前車之鑒”的知識性對話。可是這種對話,在官方的版本里被認為是封建迷信。學者通過翻閱前人的書籍,實現與前人研究之間的對話的目的非常清楚,即在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推進當下自己的問題。政治家也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時刻注意“以史為鑒”的解釋邏輯。在霍布斯鮑姆所作的《傳統的塑造》中,原以為英國皇家軍隊的儀式與皇權一樣來自久遠,其實它作為表達國家的正統性的儀式,產生于十九世紀末。所以,在他的研究中促使我們進一步領會了所謂“人為的事實”。也在這種意義上,面對所研究的對象,我們也基于這樣一種認識,即他們是活靈活現的人熕們能給客觀事實賦予靈魂!我們在研究這種“人為的事實”、具有“靈魂的事實”時,就不能也不可能僅僅依靠自己的模式和想象去生搬硬套自己的研究對象。我想這是“草根的力量”的初衷,也是需要進一步明確的地方。
2、對知識本身的貢獻。任何一個細小的研究,如果認為它有價值讓你沖動的話,那么你就必須向讀者交待它的價值所在。討論這一價值并非大吹大擂,而需要在知識的脈絡里論證。通過已有的研究,發現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知識這棵大樹上的哪個枝椏里。這些工作應該由作者本人親自梳理(而不是以評論的形式代勞)。它同時也引發下述問題:即研究者(筆者)與讀者之間的那種不同層面的知性運動。如何將這兩種知性運動很好地結合起來,這是學者自己的功夫,而不是被研究者的問題。知識運動再生產的動力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