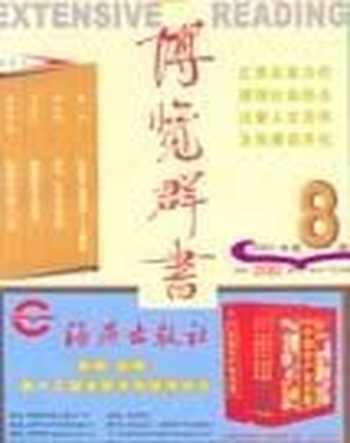《中國歷史年鑒》(1998)的缺憾
肖傳林
《中國歷史年鑒》自1979年誕生以來,已步入青年時期。它以嚴謹、開放的學風,高密度的信息量,以及對中國史學研究的權威性評述而贏得國內外一片贊譽。它折射新時期史學二十年的輝煌歷程,影響、培育了一代史學工作者,成為海內外了解中國史學的首選圖書。但是,《中國歷史年鑒1998牎罰熑聯書店,2000年第l版,以下簡稱《年鑒》犞柿棵饗韻祿,引起了學人的極大憂慮。
第一,《年鑒》作為編年體工具書,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以年度作為收集資料的單位時間,《年鑒》應該系統匯集1997年我國史學界的信息,但它沒有遵守這一基本要求,無論是歷史研究綜述方面,還是論文索引方面,反映的對象還有1995年、1996年的內容。這種現象對《年鑒》來說,已是見怪不怪了。
第二,《年鑒》的基本要求是將一年之內的重要研究文獻信息、有關資料文獻信息盡可能全面收集進去,但《年鑒》卻存在明顯的缺項,主要表現在二級分目熥ㄌ猓牭納杓粕稀W魑歷史專業年鑒,對中國歷史一般是按照朝代列分目,由于近代中國的特殊性,學術界對這段歷史的分法又有不同的認識,是按照社會性質來分還是用階級斗爭的觀點來分,或是沿襲傳統的分法,成為仁智相見的問題,給《年鑒》帶來了分目上的困難。作為過渡辦法,年鑒以政治、經濟、文化及某件大事為中心作為分類標準,體現出了設計者的聰明才智。但令人不解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有五十多年的光輝歷史,無論叫當代史,還是國史,作為斷代史理所當然地應該納入歷史學的視野里,《年鑒》的書目、論文索引也有這方面的篇目,然而正文中卻沒有分目。而當代史又不屬于《中國年鑒》的反映對象。
我國1840—1949年的歷史,根據不同的研究對象,分為晚清史、民國史、近代史、現代史、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等,《年鑒》反映這一時期內容的有7個分目,然而基本上沒有中共黨史研究的優秀成果。由于我國的特殊國情,中共黨史研究在中國近現代史園地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一支龐大的研究隊伍,改革開放以來,在史學觀念、研究方法、史料的挖掘和研究成果上,都取得了巨大進步。就論文而言,僅據《年鑒》“中國現代史”的論文索引統計,有關黨史的論文有800篇,占同期論文總數的60%以上。就專題而言,1997年是南昌起義等三大起義六十周年,有關論文49篇,然而《年鑒》有盧溝橋事變60周年牭姆幟浚熒枵飧鱟ㄌ馕蘅珊穹牽,但對三大起義的研究卻只字不提,這就匪夷所思了。
第三,《年鑒》作為高密度的信息庫,要求每個分目熥ㄌ猓牫對其綜述的對象進行全面掃描以外,還必須將新的、大的、特殊的成果表現出來,《年鑒》的某些分目離這個要求相差甚遠。以“民國史”為例,該專題反映面太窄小,選擇對象過于集中一家刊物,“民國史”中介紹了10篇論文的新成果,其中有6篇來自《近代史研究》。民國人物只評介了顧維鈞一人,《從<顧維鈞回憶錄>看顧氏其人》煛督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犖蘼鄞幽且桓黿嵌瓤,依據一份回憶錄來研究一個人物,其史學價值就很有限,但綜述者竟用整篇文章13%熑文3500字牭鈉幅加以贊揚,而對同時期出版的、在國內外產生一定影響的《蔣介石全傳》熣畔芪鬧鞅,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犜螄墨如金,沒有用一個字加以評價,這就缺乏公允性和客觀性。
第四,“論文索引”作為二次文獻,是通向信息庫的路徑,成為《年鑒》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但《年鑒》的“論文索引”編排的相當粗糙。
其一,同一論文篇目多次重復。如第527頁倒15行《五四運動與民族主義的高揚》,隔6個篇目煹528頁第3行犜俅緯魷;第529頁《大革命后期黨的路線的兩次轉變》,僅隔一個篇目又重復出現熤桓3行,而且將作者的名字印錯熐拔“劉誠”,后為“劉成”牎M頁倒11行《大革命時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工作的考察》,在530頁第4行又出現。
其二,“中國史論文索引”對1840年—當代的論文是分“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當代史”三個時期來排序的,但不少甲時期的文章放到了乙時期里,如《武昌起義計劃泄露真相》、《試析中華革命黨失敗的原因》、《八大前后安徽的社會發展》這類從標題就一目了然研究對象所屬時期的文章煛賭曇》竟然將其歸在“中國現代史”里。又如有23篇盧溝橋事變和“七七”事變的文章被放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內;再如將《試論解放戰爭初期華中戰場的縱深作戰》、《評重慶談判期間<大公報>的立場》放到“抗日戰爭時期”內,而將《重評1944年中國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百團大戰對國民黨抗戰態度的影響》則放入“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內。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很多,這類常識性的錯誤出現在規范性強的權威性的工具書中,實在是令人非常遺憾的事,有傷《年鑒》的聲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