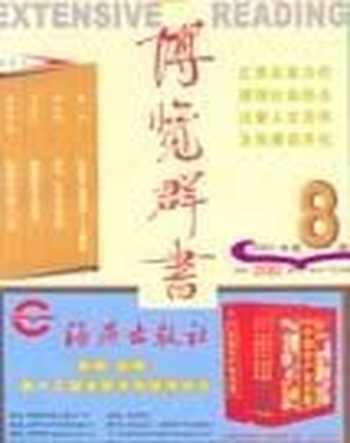了解美國(guó):讀者的常識(shí)理性和學(xué)者的“科學(xué)結(jié)論”
東 來(lái)
在很多情況下,對(duì)許多問題的分析和判斷,一般民眾的生活常識(shí)往往比一些理論家的長(zhǎng)篇大論更有說(shuō)服力。比如說(shuō)要判斷一個(gè)國(guó)家是否充滿活力,是否強(qiáng)盛,理論家可能要引經(jīng)據(jù)典加以全方位多層次的說(shuō)明,而常識(shí)卻告訴我們只要看兩個(gè)現(xiàn)象就足夠了:這就是世界上的人才往哪里跑,國(guó)際上的財(cái)富向什么地方流。在諸種生產(chǎn)要素中,還有什么比人力和物力資本更重要的呢?以此來(lái)衡量,美國(guó)的確是世界的龍頭老大。九十年代,移民美國(guó)的實(shí)際人數(shù)創(chuàng)美國(guó)歷史最高,至少在一千萬(wàn)以上,其中有一半左右是來(lái)自亞洲地區(qū)高素質(zhì)的技術(shù)和投資移民;同時(shí),美國(guó)這個(gè)世界上最富庶的國(guó)家又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國(guó)家。多么地不平等!世界上最需要外來(lái)資本發(fā)展的第三世界國(guó)家得不到“雪中送炭”般的輸血,而世界上最強(qiáng)大的國(guó)家卻獲得了“錦上添花”樣的滋潤(rùn)!而且,其中很多的滋潤(rùn)恰恰來(lái)自需要輸血的第三世界。就像人往高處走一樣,資本的洪流永遠(yuǎn)流向能夠帶來(lái)更多利益的市場(chǎng)。這實(shí)在是令人很無(wú)奈的現(xiàn)實(shí)。
美國(guó)憑什么有這么大的吸引力,可以無(wú)情地“掠奪”第三世界寶貴的人力資本?美國(guó)為什么至今尚未像歷史上其他大國(guó)一樣顯露出衰落的征兆?美國(guó)靠什么能夠在二十世紀(jì)強(qiáng)盛不衰,保持著可持續(xù)的發(fā)展和強(qiáng)大?美國(guó)有能力把“美國(guó)世紀(jì)”維持到二十一世紀(jì)嗎?人們常常提出這些非常自然的疑問,可是我們一些理論家的回答卻是那么的不自然。八十年代,美國(guó)人對(duì)美國(guó)衰落征兆的自省和警覺曾使國(guó)內(nèi)的學(xué)術(shù)界掀起了一股談?wù)撁绹?guó)衰落的熱潮,其熱烈程度比起美國(guó)自己的討論也有過(guò)之而無(wú)不及。
的確,七十年代以來(lái),美國(guó)開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zhàn)。美元霸權(quán)地位的喪失、侵越戰(zhàn)爭(zhēng)失敗和水門事件丑聞,從國(guó)際經(jīng)濟(jì)和政治地位兩個(gè)方面說(shuō)明了美國(guó)力量的限度,顯示了相對(duì)衰落的征兆。在國(guó)內(nèi),國(guó)民經(jīng)濟(jì)的停滯和通貨膨脹(滯脹),政府威信的掃地,社會(huì)道德的淪喪,種族關(guān)系的緊張,多元文化的興起,嚴(yán)重削弱了美國(guó)的內(nèi)在凝聚力。國(guó)際上,冷戰(zhàn)勝利的欣快轉(zhuǎn)眼即逝,越來(lái)越多的國(guó)家和國(guó)際組織開始對(duì)美國(guó)說(shuō)“不”,美國(guó)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與盟國(guó)的合作和協(xié)調(diào),來(lái)維護(hù)其超級(jí)大國(guó)的地位。這些表征暗示著美國(guó)正在像歷史上的其他大國(guó)一樣,走上了盛極必衰的道路。這些看法大體成為當(dāng)時(shí)的一種共識(shí)。似乎只有資中筠等極少的幾位國(guó)內(nèi)學(xué)者提醒美國(guó)衰落論者注意,美國(guó)在科學(xué)和人力資源上仍占有絕對(duì)的優(yōu)勢(shì),而這恰恰是現(xiàn)代國(guó)家的強(qiáng)盛之本。
可笑的是,當(dāng)年美國(guó)衰落論者現(xiàn)在轉(zhuǎn)而大談特談美國(guó)的“新經(jīng)濟(jì)”和美國(guó)的“一超地位”,似乎忘記了自己當(dāng)年討論美國(guó)為什么衰落時(shí)頭頭是道的分析。基于這樣的觀察,我們幾位學(xué)習(xí)和研究美國(guó)歷史的年輕博士覺得,與其尋求對(duì)當(dāng)前現(xiàn)象的“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式的解釋,還不如討論二十世紀(jì)美國(guó)發(fā)展成為一個(gè)超級(jí)大國(guó)的歷史進(jìn)程。坦率地講,我們沒有能力回答前面提出的那些重大問題,我們所能作的是從經(jīng)濟(jì)、政治、外交、軍事、移民社會(huì)和科學(xué)文化六個(gè)專題,分門別類地、比較全面和深入地描述美國(guó)在二十世紀(jì)的發(fā)展變化,并在這種變化和發(fā)展中尋求美國(guó)歷史的連續(xù)性和繼承性,探討這個(gè)超級(jí)大國(guó)由富到強(qiáng)的成長(zhǎng)過(guò)程及其對(duì)外部世界的影響。
讀者總是希望歷史學(xué)者給出一個(gè)最終的答案,我們的歷史教育也要求我們回答各種各樣的“為什么”焀hy,否則歷史學(xué)家就沒有盡職盡責(zé),更有辱歷史作為科學(xué)的美名。可是,對(duì)我們這些普通的學(xué)者來(lái)說(shuō),對(duì)歷史進(jìn)程本身的注意,對(duì)歷史是“如何”烪ow牱⒄寡荼湓侗壤史“為什么”發(fā)展演變更為重要。“為什么”的問題永遠(yuǎn)是建立在“如何”的基礎(chǔ)上的。而且,“為什么”的問題不應(yīng)該由歷史學(xué)者來(lái)告訴他的讀者。歷史學(xué)者應(yīng)該相信他的讀者可以從他所建立的歷史“如何”發(fā)生的敘述中,得出自己的“為什么”的結(jié)論。歷史上有太多太多的例子說(shuō)明,讀者憑常識(shí)理性從歷史中得出的看法要比受某種客觀條件限制的學(xué)者的“科學(xué)結(jié)論”更可靠、更有說(shuō)服力。
煛兜貝美國(guó)——一個(gè)超級(jí)大國(guó)的成長(zhǎng)》,任東來(lái)、王波、張振江等著,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