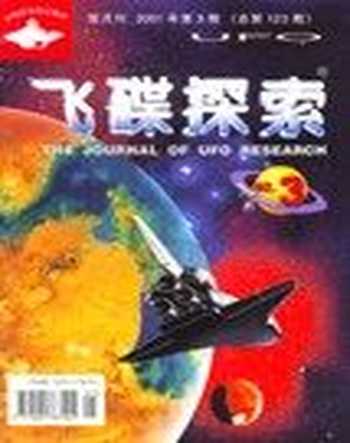發現外星人的機會
何 寧
搜尋地外生命已成為天文學和生物學中的一個熱門話題,但很少有人記得這個課題是怎樣在40年前被提出的。1959年9月,物理學家考康尼和莫里松在英國《自然》周刊上發表了一篇“尋找星際通訊方式”的文章。考康尼和莫里松認為,射電望遠鏡已變得十分靈敏,足以接收到來自遙遠恒星周圍的文明發射的信息。他們認為,這樣的信息可能以21厘米的波長發射,這是宇宙中最普遍的中性粒子元素氫的無線電輻射的特征波長。外星人可能將它們用于電磁波中的一種邏輯信號,像我們這樣的搜尋者會想到在這一波段上進行搜索。
1960年4月,射電天文學家弗蘭克·德里克成為探測來自宇宙的智慧信號的第一人。利用西弗吉尼亞州格林班克的國家射電天文臺的25米口徑射電望遠鏡,德里克“監聽”了附近兩顆類似太陽的恒星:鯨魚座τ和波江座ε。他的這個奧茲瑪計劃是不成功的。
在奧茲瑪行動之后,德里克組織了一次會議和一群科學家討論了搜尋地外智能生命的前景和可能遇到的困難。在1961年11月,10名無線電專家、天文學家和生物學家在格林班克召開了兩天會議。年輕的卡爾·薩根及伯克利大學化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卡爾文也出席了會議。正是在這次會議期間,德里克提出了他的著名方程:
N=R×fp×ne×fl×fi×fc×L
其中,N代表銀河系中的文明數量,它是幾個可以求出的未知數的乘積。R是每年在銀河系中誕生的恒星數,fp是擁有行星的恒星比數,ne是行星系中“類地”行星的平均數,fl是類地行星中具有生命的行星比數,fi是具有智能生物的行星比數,fc是能夠進行星際無線電通訊的智能生物的比數,L是通訊文明的平均壽命。
通過將一個大的未知量分解成一系列更小更容易求解的未知量,德里克方程使搜尋外星文明變得更加現實和有希望。這一方程為地外生命問題提供了進行科學分析的基礎。
天文學家和生物學家曾試圖解開這個方程。初看起來,得出準確的估計值似乎很簡單,但在實際情況中,算出地外智能生物的數量并不容易。近年來,這一方程中的一些變量已被確定,但一些變量仍未確定。
在銀河系中,恒星生成的速度均為每年一顆,所以R=1;fp可能小于1,不是每顆恒星都有行星伴隨。如果一顆恒星有一個行星系統,可以認為,其中至少有二到三顆行星和衛星可能適合生命的起源,所以,fp×ne<1,但接近1。
樂觀者認為,生命在類地行星上都會生成,即fl=1,而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過程最終都有利于智能的進化,即fi=1。另外,沒有智慧文明會存在很久而不發現電和無線電并感到迫切需要通訊,即fc=1。在這種情況下,德里克方程可簡化為N=L(智能社會的平均壽命),如果L是1萬年,在銀河系中就會有1萬個左右的文明,或大約每2000萬顆恒星中有一個星際文明。如果它們均勻地分布在銀河系中,最近的文明可能離我們有大約1000光年遠。因此,雙向通訊將需要一段漫長的時間——相當于有記載的人類歷史中很長的一段時間。
然而,35年的搜尋地外智能生命的努力卻一無所獲,盡管射電望遠鏡的口徑、接收器技術和計算能力自20世紀60年代初以來已大大增加了。
是不是我們過高估計了一個或更多的德里克參數的值?智慧文明的平均壽命是否很短暫?還是因為天文學家忽視了一些更深層的因素?
讓我們通過分析每個因子來重新求解德里克方程。
平均每年在銀河系中生成的恒星數R的值約為1——天體物理學家們相當肯定這一點(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每年正好有一顆新恒星生成,而是介于03~3之間的某個平均數)。
有多少行星(fp)
第二個變量fp,是擁有行星系統的恒星百分比。最近發現的被行星盤環繞的年輕恒星以及探測到圍繞附近的類似太陽的恒星運行的行星,證實了天文學家們早就提出的猜想:行星是普遍存在的。
原始行星盤已被各種紅外觀測設備探測到并在哈勃太空望遠鏡的獵戶座星云照片中被直接看到,該星云是一個恒星大量生成的區域。這些觀測似乎暗示,在所有新生成的恒星中,至少有50%被行星環繞。雖然沒有人肯定這些行星盤會存在多久。最近的亞毫米波觀測表明,在大量老年恒星周圍,有更稀薄的塵埃盤,包括德里克的第一個探測目標波江座ε星。這些圓盤有許多是炸面圈型的,按照某些理論家的說法,那些中心洞只能是由于行星從圓盤內部吸積氣體和塵埃造成的。
在探測200個太陽型單星時,發現了10個行星系,這表明約有5%的恒星有行星伴隨,所以fp應為005。然而,有一個誤區,現行的探測技術只對大質量行星尤其是那些在很近軌道上的大行星是敏感的,和太陽系完全一樣的行星系仍不能確認,很有可能,帶有行星的太陽型單星的真正比例要遠遠高于5%,可能高達50%,甚至100%。
適合生命的行星(ne)
這個因子代表在其他行星系中有適合生命起源的環境的行星的平均數目(e代表“地球型”)。在1992年出版的《地球以外有人嗎?》一書中,德里克回憶說,格林班克會議的參加者估計,ne值介于1~5之間。換句話說,每個行星系至少包含一個類地行星(一個存在液態水的行星),而每個行星系可能有三個、四個或五個這樣的世界。
這種樂觀的看法是根據這一假設得出的,即我們的太陽系在大小、行星數量和分布上是具有普遍性的。今天,火星和木星的衛星歐羅巴被認為是早期生物的世界,在太陽系中,確實形成了三個“類地行星”。然而,在最近3年中發現的太陽系以外行星使人類認識到,擁有眾多行星和衛星,在完美的、穩定的、近乎圓形的軌道中運行的太陽系,可能是個例外。
有多少個生命起源(fl)
fl是可居住行星的比值。建造生命的分子(復雜的有機碳氫化合物和氨基酸)在宇宙中是豐富的。它們在隕石、彗星和星際氣體及塵埃中被發現。在星際空間中比在地球生物圈內存在更大量的氨基酸。無疑,大量原生物的進化正在恒星之間和黑暗的宇宙中進行。
也許,在適當條件下,生命的起源是一個相當簡單而容易發生的過程。如果這一過程十分罕見或很難發生,生命就不會在地球早期發生,而是更晚一些時候在這顆行星上出現。現在,生物學家們正在討論生命是否曾在地球上出現過幾次。有理由認為,今天所有的生物都有一個共同的祖先,但其他獨立的生物鏈可能形成過并早早已被滅絕了。如果生命在一切有條件的地方都能生成,那么,可以推測fl=1。
智能數目(fi)
剩下的只有3個未知數。智能生命(fi)的進化又怎樣呢?怎樣才能證實地外文明能夠并且愿意用無線電發射信號(fc)呢?什么是無線電文明的平均壽命(L)呢?在德里克方程中,這些生物學和社會學因素遠比天文學因素更不確定。
按照許多生命科學家的說法,認為另一顆行星上的生命進化必然導致和人類一樣的智能生命是幼稚的。哈佛大學古生物學家高德在他的最暢銷書《奇妙的生命》中斷言,我們可能應把我們自身的存在歸結于運氣,人類不是生命進化的必然趨勢。演化是不可預測的和無序的過程。高德曾指出,如果我們能倒回地球生命演化的錄像帶并重放一遍,人類再次出現是不可能的。
當然,其他人會反駁說,我們正在尋找的不是外星球上的人類。沒有人會指望在其他行星上發現人(小綠人或其他什么人),而是說,是否有其他類型的生物進化出使用工具的能力,發展成一個復雜的社會,積累并很好地應用知識并足以發現電子學原理。在樂觀者看來,差異很大的各種動物在地球上各自進化出的智力水平和有目的的行為的區別似乎只是程度上的,而不是物種上的。
高德注意到,在生命進化中沒有統一的模式,沒有特定的方向或偏向。我們認為,生物差異的增加必然伴隨著智力的增加可能是個致命的錯誤。如果某些后來進化的動物比早先進化的動物更聰明,這可能只是個僥幸的成功。人類的智能和技術水平可能更是如此。
在某些生物學家和地外探索的支持者看來,“適者生存”這句話表明,更高的智能必然增加一個物種的生存機會并渡過自然選擇過程。但哈佛大學著名生物學家恩斯特·梅亞認為,許多天文學家和物理學家對智能的出現過于樂觀。梅亞在1996年5月出版的《行星報告》中寫道:“他們會說,如果生命在什么地方出現,到一定時候它必將發展成智能;另一方面,生物學家深刻認識到,這樣一種發展不是必然的。”
樂觀者指出,地球在被膨脹的太陽燒毀前還有10多億年時間,這是自從第一批簡單生物爬出海洋登上陸地以來的時間的兩倍多。如果智能生物的出現是十分困難和罕見的話,樂觀者宣稱,它就不可能出現得這樣早。很可能在未來10億年中,完全不同的智慧生物將再出現幾次。
悲觀論者反駁說,我們實際上不知道地球將保持這種狀況多久——地球表面上穩定的氣候可能是一個漫長的幸運時期——所以事實上,我們可能在適合生命的時間區段內出現得遲了。
奇怪的是,雙方都承認所謂的哥白尼原理,即,人類并不享有在時間或空間中的優先地位。懷疑論者如梅亞說,正是人類中心論才相信,人類型智能曾在宇宙中一次又一次出現。相信者如德里克則不原承認我們的特殊性,因為這將違反哥白尼學說。
顯然,fl在德里克方程中是爭論最多的因素。一些科學家相信它的值接近0,而其他人相信它的值接近1。似乎不存在中間值——智能生物出現的問題是地外探索中的一個兩極分化問題。
即使進化可能產生智能,fl也比1小許多。最近探索到的太陽系和行星氣候的穩定性就是證明。由麻省理工學院的拉西奧和弗洛對其他行星做的計算機模擬表明,類地行星不可能在引力拉鋸戰下即在有兩個(或更多)大質量的類木大行星的行星系中生存,它們會被拋出行星系或被搖搖晃晃地推入中央恒星內。
反之,完全沒有巨大行星的行星系也不適合帶有生命的行星生存。由華盛頓卡內基學院的威斯韋爾做的計算機模擬表明,木星的作用就像太陽系的引力吸塵器一樣,有效地掃除了闖入地球交匯軌道的眾多危險的彗星。威斯韋爾說,沒有木星,彗星與地球的碰撞幾率將高出1000倍,每10萬年發生一次災難性的撞擊(就像6500萬年前發生的那一次),這肯定會阻礙任何以簡單生命形式向更高智能的緩慢進化。
還有,由萊斯和羅伯特所做的動力學研究表明,類地巖石行星在軌道上表現出無序的傾斜變化,這種傾斜能導致猛烈的氣候變化。幸好,地球在軌道上傾斜的無序變化通過月球的潮汐作用被消除了。沒有一個很大的衛星,地球可能已經歷了類似于火星那樣的自轉軸傾斜的變化——大到20°~60°的變化,這將造成強烈的季節變化。
生物學家相信,變化和壓力會導致易變的適應性強的物種的出現。哈佛大學的霍夫曼和三位同事最近提出,在8.5億年~76億年前出現的一系列全球性冰期,凍結了各大洋洋面直至赤道。它是導致那一時期前后新的生命形式“前寒武紀大繁榮”的轉折點。在地質年代后期恐龍大滅絕后,隨著許多新物種的出現,地球又恢復了生機。人類在一次冰期中的出現就是壓力驅動進化的一個例子。
但太猛烈或太頻繁的行星災難將滅絕一切生物,或使受到打擊的生命停留在一個低水平上。無論在哪種情況下,我們目前的存在都似乎是一系列天文上的巧合產生的偶然結果。
外星人發射的信號
假設地外智能生命存在,他們會通過無線電信號和我們交流嗎?有多少文明能夠并且愿意用一種我們能探測到的方式發射信號?換句話說,fc值是什么呢?地外智能生命探索的支持者傾向于認為fc值較大;或遲或早,任何技術文明都將發現,無線電是越過天文距離交流的最有效的方式,并會選擇這樣做。也許我們還不懂得生物進化的真正多樣性,或者還有未被人類探索到的科學和技術領域。和有待于我們發現的事物相比,無線電可能是非常原始的。
壽命
對通訊文明的平均壽命L,樂觀者和悲觀者之間也相距甚遠。樂觀者聲稱,一個穩定的智能社會可存在幾千萬年,如果不是永存的話。悲觀者指出,人類在幾十年前才發明了無線電技術,而人類處于毀滅自己的邊緣(通過高科技戰爭和污染)已有很長時間了。
成功是無法預測的
我們還能相信N=L嗎?也許不能了。N=0如何?對許多人來說,這種極端情況是絕對不能接受的。也許這一說法有些道理:宇宙中沒有什么事物只發生一次。也許外星文明是存在的,其中一些正試圖通過無線電發射宣布自己的存在,但它們的數量可能非常非常少。
在《地球以外有人嗎?》一書的序言中,德里克寫道,他想“使人們對目前的探測活動的結果——在近期探測到來自地外文明的信號有思想準備。我期望在2000年之前得到證實的這項發現,將深深地改變這個世界”。1996年7月在意大利卡普里島舉行的第五屆國際生物天文學會議上,德里克承認:“也許我有點過于樂觀了,成功是無法預測的。”考康尼和莫里松在1959年的《自然》雜志上發表的文章中已經告訴過他這個論點:“成功的可能性是很難預測的,但如果我們從不探索,成功的可能就是0。”
我們離那個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第一項R十年前就已知道,我們現在正了解第二項fp。留給我們的是兩個已部分知道的因素和三個尚未知道的因素。但也許德里克方程并不在乎被徹底解開,它的真正價值可能在于那些引起深思的問題中。不確定性和好奇心將繼續使這種探索進行許多年。也許,解決地外智能生命探索的問題不是產生“是不是”的結果,而是幫助我們更多地了解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