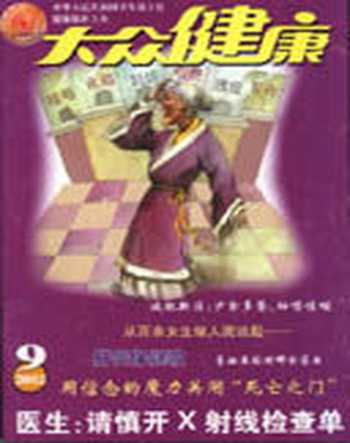一個忠誠的制藥企業
也 乜
那是一味夸大財富,人人渴望撞上數字神話的瘋狂時期。特別是尼葛洛龐帝的“資本為數字經濟燃燒”,幾乎征服了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聯邦制藥董事長蔡金樂先生,在如此“力拔山兮”的狂躁大勢之下,說的卻是“愛國主義”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
僅僅一兩年的工夫,今天,一些超級大國開始準備為偏執和狂熱付出高昂的社會成本代價。紅極一時的CEO們必須面對“再就業工程”。整個世界浮躁和塵埃紛紛落定。人們重新反思:企業的責任,財富的偏離,資本的律動。這時候,那些一步一個腳印,無級變速、平衡上升的企業;尤其是那些以國家、社會、民族利益為重的企業,毫不造作的顯現出來。
聯邦制藥的商業模式在今天更有說服力。
故事一
6月的第一個周末,下午4點,北京人民大會堂。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國內醫藥方面的有關專家,正在認真論證珠海聯邦制藥股份有限公司將與美國UBI公司合作開發生物工程藥品的項目。現在的情況是“聯邦”人已經躋身于這個領域的前沿,只要抬腳射門就有爭得世界第一的可能。
這不是一般的技術合作,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斥資問題。聯邦制藥董事長蔡金樂先生透露,“此舉厲害”。據說一旦成功,將意味著人類可以獲得由氨基酸合成的某種抗原,從而對新一代疾病譜中最為關注的現代病起到免疫及預防作用。
當然,這是一項極具冒險性的嘗試。要把實驗室的成果進行市場轉化,后果未卜,卻耗資巨大。據說,蔡先生將用買斷UBI公司股權的方式,獲得此項技術的控制權。之后,中美雙方將在各自的制藥企業之間進行同步的產品試驗、開發。這位躊躇滿志的中國藥界成功人士,不諱言其中的“氣魄”和“膽量”。他甚至說到頗沉重的字眼——“拼!”
“我們民族的制藥工業怎么發展?怎么競爭?怎么站起來?出路在哪里?是繼續做普通藥還是向高科技沖刺?”蔡先生坦言,這樣的問題在自己的頭腦中想了很久。因此,一旦有機會,他是不會輕易讓它跑掉的。
論規模,“聯邦”算不上中國制藥企業的“大阿哥”;論時間,不過8年的經歷。挑頭的事按理輪不到他。
企業家的思維方式決定一個企業的運勢。蔡先生考慮問題的出發點總是離不開國家、民族——“國力的競爭在于企業,我們不去做,哪有國家的強盛?”于是,他的事業一次又一次從這種激昂情緒中走過來。“激昂”鍛造出聯邦制藥不可抵擋的核心能量。
故事二
1994年,“聯邦”在中國珠海一片撂荒地上破土。當年,蔡先生一擲數億港幣。說實話,連第一口淡水井都是自己打的。基礎設施幾乎是零。對國家,他沒有一絲抱怨,這份苦他吃得心甘。
當年,他回敬給這片撂荒地的是一座國際化的醫藥公司和一座占地36000平方米的現代化藥品制劑廠。
蔡先生性格執拗,“咬定青山”,風來雨去,不為所動。“必須是世界最前衛的設計和最精當的設備。”他說。事實上,從第一塊磚頭開始,他就把未來的企業設定在GMP標準上(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
多么不諳時務!當時國內的行情是,“要想當縣長,首先辦藥廠”。“低水平、廣覆蓋”在制藥行業尤為突出。在有利可圖的驅動下,中國大地,家家點火。更重要的是,國家法規以及行政管理部門,還沒有把這種國際通行的GMP標準擺在桌面上。這種“空子”對于中國的制藥企業,無疑是“難得的商機”。但是,大勢之下,聯邦制藥為了廣大消費者用藥的絕對安全,居然自覺地為自己設置了這道相當高的門檻。
“如果只是建個藥廠,賺點錢走人,那不是我要做的事情”。蔡先生把“為自己的國家建一個現代化的、符合GMP標準的、世代相傳的制藥企業”,稱之為“投資建廠的目的”。理由很簡單,“外國人能做到的事,我們應該可以做到”。這種不甘示弱的民族氣節,恰恰決定了一個企業的發展前景。
事隨人愿。1997年,聯邦制藥成為中國境內第一個全方位通過GMP認證的企業(包括粉針、片劑、口服液、膠囊劑、凍干共5大劑型)。自此,中國藥業的新生代在混沌中脫穎。
上個月,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安全司司長白慧良先生證實,國家已經開始對7000多家制藥企業進行GMP強制認證。達不到標準的,沒商量,關門。試想一下,一個沒有生產規范和質量標準的制藥企業,它的命數能有多久?而它對于患者生命的責任又體現在哪里?
蔡先生明智。他深諳制藥工作者的立身之本。因此他能把握住崇高之中的縝密和嚴謹。當然,企業日后與國際對接、走向世界的基礎必須是從腳跟鑄起。于是,在自己的國土上,他甘愿扮演“先驅”的角色。
故事三
1996年,聯邦制藥還是襁褓之中,卻已經早熟。或許是印證了“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蔡先生一直把自己的國家看成“并不富裕的母親”,而自己俯首甘為孝順孩子——
“為什么中國的百姓依然停留在落后的用藥狀態?”整個世界的基礎抗生素已經從青霉素走到半合成青霉素時代(氨芐、羥氨芐、頭孢菌素等);“為什么十余億人,尤其是孩子們,無奈地忍受青霉素試驗的疼痛、恐懼,而我們的制藥企業竟可以聞而未聞,視而不見?”“為什么直到90年代中,半合成青霉素還只能依賴進口?”而其中昂貴的價格又有多少國人可以受用得起……“我們這么多大型的原料藥廠都干什么去了?這種并不高明的制藥工藝竟能卡住這么一個泱泱大國的脖子?難道我們不能用自己的產品將它們抵制在國門之外?”
一連串的想不通。這種置疑不知更應該屬于哪部分人的職能范疇?反正當時,如此耿耿于懷者在諾大個中國,似乎莫過于蔡先生。“真的很氣!”一氣之下,“唉,我來試一把。”真要改變依靠進口的被動,不妨先建一座月產量100噸的氨芐、羥氨芐原料藥大廠。
于是蔡先生二擲數億港幣。建原料藥廠的氣魄更大——200000平方米。按常理,等待“國企”挑大梁是最穩妥的選擇。原本這種基礎原料應該是國家的職責范圍。
商海歷練,蔡先生明白此舉將是驚險迭起:一個稚嫩的民營企業要和龐大的“國有”叫勁兒;更重要的是,他還要和老牌的“國際”在價格上抗爭。很顯然,與單純生產制劑相比,他可能失去獲取最大利潤的機會。但是,他懂得放棄“利潤第一”的口號。這并非純屬于高尚的動機。因為他不同于常人。在一般人的眼里,企業的目的就是賺錢。但在他看來,民族的榮譽、人民的利益更重要。
其實,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往往不是踩著地雷,而是占盡先機。但是,這種“冒險”最起碼的本錢是激情和熱血。聯邦制藥的“使命感”勢如破竹。原料藥廠一動手,當年過關。更讓蔡先生欣慰的是,緊跟著,大“國有”們也陸續告罄。兩年的工夫,到1998年,中國原料藥的局面徹底改變。半合成青霉素進口終于畫上歷史的句號。
之后,聯邦制藥引發了一場青霉素劑型的革命。這是建立在新一代原料藥基礎上的新產品——口服劑型。于是,青霉素最古老的針劑和皮試,在中國這個最廣闊的市場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隨即中國百姓用藥的觀念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因為口服的方便和帶有絲絲甜味,孩子們不再談“藥”色變。
“不,不能說我做得最早。”對于做原料藥的“一氣之下”,蔡先生稱之為“只是拋磚引玉”。這么一激將,讓大“國有”們一拖數年的改造項目進程大大加快。這似乎更是他的目的。
故事四
“愛國”不是一句空話。企業家最大的“愛國”是敢于承擔起社會的責任。
21世紀社會對于成功人士的標準,已經不僅僅是以財富論英雄,而是對人的素質提出“整和藝術”的概念。一位明智的企業家,越來越多考慮的不應該是利潤,而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他們會主動地肩負起對消費者、對客戶、對員工特殊的責任。
“平民風格”是聯邦制藥基于國民經濟狀況實施的“為人民服務”戰略。他們在投資成本很高的前提下,承諾“讓并不富裕的人同樣享用高質量的藥品”。這本身是一道難題。但讓人驚奇的是,他們竟能在銷售手段上創出奇跡——“賣半包,甚至幾粒”。如此,云南大山里的農民們,挑擔柴火到集市,變賣之后,可以買幾粒“聯邦”的“阿莫仙”帶回家;湖南的鄉村教師;新疆的牧民……總之,最基層的消費者都能接受“聯邦”。
蔡先生屬于大徹大悟的企業家。他深諳發展與平衡的關系。遵循取之于社會,回報于社會的道理。比如,他會把目光放到很遠,為國家后續的醫藥人才建立3800萬的“聯邦獎學金”。又比如,他有感于中國的醫學專家們醫術高超,辛苦有加。于是,出資請人,為他們樹碑立傳。當然,抗洪救災,他覺得責無旁貸;西部大開發,他積極響應。據說與“四川抗生素廠”合作,一投就是3000多萬……
蔡先生的責任感更表現在對精神啟迪的貢獻。“物質不是中國下一代的最缺”。為此,他已經連續4年,年年親臨設立“聯邦獎學金”的38所大學,用親身經歷為年輕人講述“貧窮無過”、“愛心傳遞”、鼓動“成功屬于每一個人”……他會把父輩用手和用馬達軋甘蔗,完全不同的初始體味,講給孩子們聽。美好生活需要動力馬達去替代愚昧落后……就這樣,他把和年輕人的溝通看得非常重要,哪怕是晚上,甚至疲憊不堪,也不放棄這種溝通。他說:“一見到他們,我覺得自己立刻變得年輕。”
其實真正成功人士,自己未必清楚并在意個人的成果價值。在公眾場合,蔡先生習慣稱自己是“一個制藥工作者”。而且非常自然,不帶有一點沽名釣譽。他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寫到,“制藥業本身是為人類帶來健康和幸福的事業”,這樣的事業是人生最高的榮耀。
結果
聯邦制藥,扛著愛國旗幟,一路高歌猛進走過來。
近年,適逢藥品價格調整。制藥企業隨即出現利潤縮水。跌宕之時,更顯英雄本色。從企業年度財政報告國內市場顯示:1995年完成銷售收入2.6億,1996年5.6億,1997年8億,1998年10億,1999年13億,2000年15億,2001年18億。
2001年,聯邦制藥一座現代化的科技大樓崛起。企業的技術儲備因此更上一層樓。為什么“信心倍增”?蔡先生欣慰,“8年,證明我們的路子是正確的”。如果說當初他對中國市場百舸爭流,勝數難測,那么現在,一覽眾山小。
今天,聯邦制藥已經構筑起向世界科技前沿沖刺的基礎平臺——自行研制開發生物類制品;向一類藥品進發。這些即將成為他們下一輪的主攻方向。顯然,他們正欲擺脫蕓蕓眾生,浮上更高層面。
“這是一條不歸路”。蔡先生會有更宏偉的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