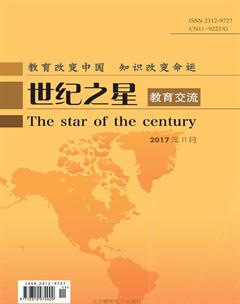淺議在《道德與法治》教學中滲透德育教育
董應兵
作為一門對學生進行道德與法治教育的專設課程,它與日常德育以及學校黨團組織教育成為并駕齊驅的三條德育工作路徑。
它是以初中學生生活經驗為依據,以青春生命在與他人、與集體、與社會、與國家以及全球關系中的自我發展為線索,以培養社會主義合格公民為中心,遵循生活邏輯,整合道德、心理、法律及國情方面的知識領域,因此,在《道德與法治》的教學工作是與日常的德育教育密不可分的。
一、在《道德與法治》的教學中應注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
將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些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有機滲透其中。如在“少年有夢”中體現了愛國主義教育;在“感受生命的意義”中從敬業的角度引導學生認識在平凡中閃耀的偉大;在“網上交友新時空”中隱含著對誠信及其復雜性的探討。而愛國主義教育、敬業、誠信這些問題都是日常德育中的重要課題。因此,在教學中為學生提供更多貼近生活的情景,讓學生在這種情景中主動地把學習當做自己的一種需要。而創設情景的一個目的,就是讓學生了解自己、了解家人、了解社會、了解世界,參與公共生活,具有公共意識,達到思想的升華和品德的內化。
二、在教學中努力滲透優秀傳統文化教育
所選擇的課例盡可能引入傳統文化經典,增強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讓學生感受到身上流淌著民族文化的血脈,以民族精神豐富和提升自身的精神世界。從學生的生活經驗出發,關注學生的內心世界,通過活動,把學生的德認識與學生的體驗、感受結合起來,讓學生從心里感受傳統文化給我們帶來的沖擊。
三、努力創新教學方法,把教育滲透到家校互動中去
針對家庭對學生成長過程的影響教師應當重視法制教育對家庭的滲透作用。讓法制教育內容滲透到家庭中,學生用課堂所學法律知識來幫助家長,再使家長以良好的家教去影響學生,就能達到家長、學生共同學習、共同提高的目的。為此,可針對法制教育方面的內容,布置一些家長、學生共做的作業,目的在于讓家長同時了解法制知識,督促學生完成所布置的作業,達到學生的知行統一。同時,學校還可通過家訪、開家長座談會等方式來加強學校與家庭的聯系,對家長進行適度的法制教育,有效地發揮學校法制教育對家庭的滲透作用。
法制教育滲透的前提是強化教師的滲透意識,形成堅定、明確、一貫和持久的滲透意識。只有教師本身具有比較高的法律意識和比較全面的法制知識,才能在學校各項工作和活動中自覺地進行法制教育的滲透,才能在實踐中逐步探索到滲透的具體途徑和形式,也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隨著普法的不斷深入,滲透性的法制教育必將受到更大的重視,并有可能成為普法教育的主渠道。
四、結合學生實際,加強德育教育
關注社會問題,應該讓學生走向廣闊社會,充分挖掘和利用社會資源,讓學生從自身實際出發,以實踐為載體,積極倡導學生自主學習、探究學習。如讓學生在學雷鋒月的時候,發現身邊的弱勢群體,從而培養學生對社會的關懷。要在實踐中體驗、在體驗中感悟、在感悟中樹立法制意識,促進自我發展,它需要我們積極利用好各種教育資源,尋找好適合學校實際和學生特點的現場感、實用性強的各種活動作為法制體驗教育的載體。例如,與公安司法機關的先進集體和模范人物進行座談,成立法制學習興趣小組,開展法制演講比賽、辯論賽,舉辦法制作文競賽,調動起學生學法用法的積極性。
學生是法制教育活動的主體,如果一味被動地接受教育,缺少過程性的參與積極性,教育效果肯定不會好。法制體驗教育實際上就是強調抓住主體體驗的關鍵環節,通過中小學生的踐行、體驗和感悟,引導學生在實踐中用“心”去體驗,自覺來感悟,使廣大學生能夠在參加豐富多彩、富有意義的法制教育活動過程中真正掌握基礎的法律知識,形成基本的法律意識。現實生活中我們可以有意識地抓住中小學生的主體體驗環節,如學生可以自行組織起來,對發生在自己身上和校園內的案例進行法律剖析,從而教育自己,警示他人法制教育活動一旦新穎、有趣,對學生有了吸引力,其預期的效果就會體現出來。
總之,將學科教育滲透于德育之中,可以走進學生的心靈,幫助學生形成一定的道德結構,自主解決對客觀世界的態度問題,從而也達成我們的學科的德育目標。